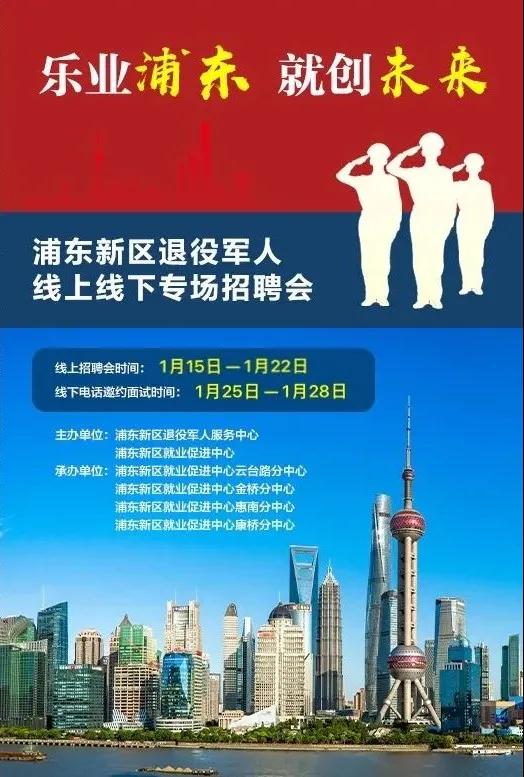最近我走访了深圳、东莞郊区的几个镇,都是3C电子轻工制造业的重镇。虽然之前报纸上已经有很多消息,但深入前线才能更好地理解肉眼可见的压抑。然而,萧条背后也存在一些有趣的现象,它们就像更大经济环境的缩影。以下是总结并与宏观趋势进行对比。
与外部需求相关的工厂,比如处理海外品牌需求的组装厂、零部件厂,就像沙漠中的泉水,成为最大的活力源泉。许多工厂甚至逆势投资增加设备。我遇到的相关老板几乎都在前十分钟内表示,千万不要相信海外市场陷入困境的报道。海外需求依然非常旺盛。还有人特别提到,即使在欧洲,媒体似乎也已经被我们这个行业彻底超越,濒临破产。可以感觉到需求的复苏,人们对新事物有强烈的渴望和兴趣。
研讨会上的眼见为实。从低价移动电源,到中价家用储能、户外储能,再到高价家用影音娱乐设备,装配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熙熙攘攘,大部分货物正在滚滚待运。 。一个仓库。
但盛况虽大,却仍暗藏隐忧。几乎所有老板都提到了在泰国和越南建厂的计划,有的已经开始实施。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尽管目前的生产成本仍比国内高出20%,但这种微弱的差距一旦加上25%的关税,就变得难以区分。
与蓬勃发展的出口相比,过去处理内需的工厂正在不断撤退和萎缩。他们要么搬迁到大陆,要么倒闭。这不仅与国内需求萎缩有关,还与国内品牌过度竞争、降价适得其反有关。极度内卷化的后果就是工厂再也赚不到钱了。以前我总是声称自己年年赚不到钱,但我离开游戏时的身体是最诚实、最可信的。
过去,很多工厂为了维持现金流,愿意在盈亏边缘生产,但现在,随着最低社保金额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老板想开门干脆关门。
我们的供应链文化中没有涨价的概念。除了年年降价之外,我们还会想尽办法降价。终端消费者也在降级。层层传导,增加了员工工资上涨的难度。
不只是老板要开放,员工也要开放。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之一是,对于维持生产的工厂来说,即使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招人的难度也比往年更大。因为大量员工离开沿海省份,返回内陆。
老板们的反馈是,年轻员工普遍不想再工作,回去找简单的工作,工作成本低,生活轻松。
这和我之前在宏观数据中观察到的趋势是一致的(详见详情)。
尽管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至18%以上,尽管国家仍然鼓励制造业,但愿意进入该行业的青年工人数量却断崖式下降。
我完全能够理解年轻人的想法。疫情过后,人们似乎从一场大梦中惊醒,意识到继续这样做是没有未来的。他们只活一次(国外也有YOLO风潮),所以还是对自己宽松一点比较好。这是普遍心态的变化。


从经济金融角度看,东莞附近工厂普工的平均工资为每月6000至7000元,每年上涨100元左右。加上年终红包,一年的工资总额大概在8万到9万元左右。从国民收入来看,已经属于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以前,一个人吃饱,一家人无忧。
但即使有了技术经验的积累,工资涨到1万到1.2万元也太高了。这个水平不允许他们在海岸定居,更不用说组建家庭了。
八点八点的工厂生活对年轻人的身心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折磨。现代人在短视频中看到的多彩世界与流水线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人心无法抑制。
上述收入中,底薪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来自加班。因此,工人必须加班。如果他们不加班,他们就赚不到钱。这进一步让生活变得无趣。

相比之下,如果回到省内从事服务业,工资低,生活成本也低,可以住在家里,领取父母的补贴,在身体和健康方面显然要好一些。精神上的幸福。
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作,也依然可以幸福地生活。请观看哔哩哔哩视频《交朋友的精灵》。但这也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
由于大部分收入来自加班,企业需求与工人供给之间存在棘手的矛盾。当订单不稳定甚至下降时,许多工厂无法填补工人的饱和水平,工人就会离开。招聘和培训成本大幅上升,企业招人变得更加困难。当很多工厂都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任何一个工厂的工人都会吃不饱,都会选择离开。
订单减少后,出现了工厂招不到工人、工人吃不饱的双输局面。即使外需强劲,工厂也宁愿增加自动化设备或实行两班倒,对增加工人也极为谨慎,因为外需也有淡季和旺季,害怕人员流动率高。毕竟,内需仍然主导着劳动力市场。
这也是制造业的致命弱点。生产线一旦启动,对饱和生产的要求太高。

整合困难,并购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资金支持。
很多人会抱怨,为什么不给工人加薪呢?欧美制造业工人为何能享受完整福利?轻松的时间,我们不能吗?我也问过各位老板。
本质上,当地制造业大部分处于低附加值状态。你赚的是组织生产线的钱。更重要的是让一大群人沿着流水线走,跟着设备走,把事情交给管理能力指挥。组装起来。这里的价值大部分沉积在设备上,其次是组织管理,最后很少落在工人身上。但这就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宿命,因为工人必须随时可替换、可替换、可流动、可补充,所以必须避免对工人技能的深度投入和依赖。
高端制造、新生产力可以提高附加值,但不能改变分配。大部分利润仍将流向设备、专利和品牌。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人类在整个生产中的价值会变得更小。这种情况将进一步加剧工资占总收入比重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
设备国产化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例如,在我参观的工厂中,除了SMT机等设备仍然使用日本产品以保持精度以满足欧美消费者的要求外,其他大部分设备基本上都是国产化的。但这种本地化不会让工人受益。连设备的生产都需要工人,整个产业链对工人的需求出现了净减少。

新生产力越发展,价值在人口中的分配就越不均匀。相反,会造成大量的劳动力冗余。
这或许就是所有高收入国家最终都必须大力提高服务业比重的原因,因为只有服务业才能增加人的价值,是主要的生产资料。
人们回流内陆省份,可以看作是经济的自发斗争,寻找自己的出路。因为当大部分人口回去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人们互相服务并满足需求。比如像杨哥这样的主播赚什么?是服务业的利润,但只是高度集中了线下门店导购的情感服务。
当物质产出过剩时,物质的边际成本被推向无限低的水平,人们对服务的需求显着增加。这时,服务业的比重会逐渐提高。因此,降低制造业比重,导致产业空心化是有风险的,但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也是不可避免的。理论上,整体蛋糕应该做大,服务业比重应该提高。即使在德国,服务业也占经济的70%。
但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最佳时机是总体需求上升的时候。一旦总需求下降,收入端就需要外部支持,才能形成正循环。
服务业的提高,归根结底是人的技能的提高和教育投入的提高。不仅是尖端顶尖人才的培养,泛服务业也需要更多具有可转移技能、自学能力和沟通能力的灵活人才。
但我们的教育体系能培养出这样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