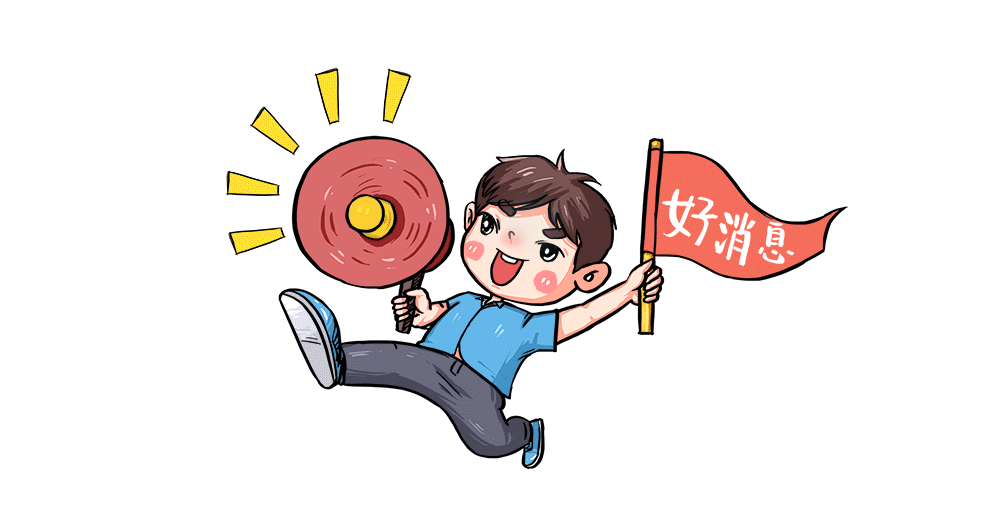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搜索“投资圈求职”,你就会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鬼故事摆在你的面前。有人表示,投资机构发布HC,不一定是真的“找人”,而是想通过“不断采访”了解各大机构最近推出了哪些项目、投资了哪些项目;有人说,“清北哈佛‘剑桥本科’已经是投资圈最低学历要求了,最新版本是‘QS50学士硕士1995年’”;有人贴出自己的职业经历,称自己是清北毕业的,被奠定了30岁就离职,在获得第一份工作之前提交了1000多份简历。
但如果加上“国有资产”这个关键词,评论区就会瞬间塌陷成三个很简单的句子——“dd”“私有”“请拉”。
这种对比具体地展现了当代风险投资从业者的生存现状:可供选择的职业机会越来越少,有限的机会慢慢向“国有”一方倾斜。近两年,不少行业争议由此引发。有人认为,这带来了一批投资方法论的失败,也有人抱怨“风险投资”越来越像一种投资工具。
经过多次讨论,大家最终会达成一个理解的态度,认为有工作比失业好,跳槽比转行好。至少,国资的积极态度表明社会对“风险投资”的价值有了基本认识。变得更好只是时间问题。而作为一个内陆城市的居民,我的看法就更加积极了,因为这种情况的另一面就是“人才回流”,而过去一直被诟病的创投氛围似乎终于有了机会变得专业。
但最近在和投资者朋友聊天时,我发现这个共识联盟似乎在松动,人们似乎又开始变得焦虑起来。一位呼声最高的朋友认为,“拥抱国有资本”可能是一条死路。尤其是那些不幸才入行近两年的年轻人,可能已经集体“功能性失业”了。
“功能性失业”
功能性失业,改编自生物学术语“功能性灭绝”,原指某个物种虽然仍然存在,但其数量已不足以支撑该物种原有的生态功能(如授粉、食物链中的天敌等)。 )并且不足以支撑种群的持续繁衍,它在生态系统中基本上已经“灭绝”了。这个词是我和老袁一起想出来的。
老袁是一位深耕某一技术领域的硬科技投资人。他是一位硬核技术人,知识图谱扎实。几个月前,他决定转行,带着多年来学到的知识加入公司负责战略,社交圈因此成倍扩大。他出差时我们约了个咖啡厅。那天早上他刚刚参观了一家连锁企业,并把晚餐时间留给了当地的一位风险投资家。
在他看来,不少一级市场从业者面临着这样的情况:他们可以通过“拥抱国资”获得工作经验,但这种工作经验是否来自“传统创投环境”,就失去了能否转移到市场的可能。面向风险投资的工作仍是未知数。
比如,他发现一些国有平台的高管全部集中在中后台,没有人负责投资或募资线路。这种设计对应了与市场化组织完全不同的“项目属性”,进而对应了完全不同的工作内容和完全不同的工作技能。
这当然没有好也没有坏。不同的社会分工需要不同的功能。但根据老袁的观察,市场化的制度(尤其是硬科技领域)已经逐渐开始呈现出明显的“工字型”结构。 “合伙人加几个MD,带一群分析师、投资经理,排名上升到高端投资”——这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这是创投行业经过多次试错后的“修正结果”,大家开始认识到“规模是回报的敌人”。
具体到一个普通从业者来说,这意味着想要在事业上更进一步,需要积累丰富的产业和人力资源。他很难想象那些“投资国有资本”的朋友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从理论上讲,那些“全面拥抱国有资产”的市场化机构很难提供太多个人积累的机会。
“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在同一个机构里,投资经理和合伙人表现出不同的工作情绪。”老袁拿出手机,给我看了几个可以作为例子的朋友圈。 “即使是普通人的搭档,他的体感也可能与核心团队不同。”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我曾经拜访过一家专注于“下沉市场”的投资机构。他们筹集的资金很多来自“地市州”,包括内蒙古和广西,这些在传统风险投资环境中属于边缘地区。该机构的领导多次向我描述“县城资金筹集量很大”。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他们在选拔和推介过程中经常会看到“红杉高瓴级别的大牌”。
套用老袁提出的话题,即使是大牌人物,也难免会接触到类似“县招”这样的业务。这一代从业者或许确实缺乏“市场化培训”的机会。
同样,我看到大量的研究报告都一致认为“规模是回报的敌人”。 《哈佛商业周刊》一篇题为《风险投资家的六大误区》的文章引用了一份未透露数据来源的“行业和学术研究报告”,称当基金规模超过2.5亿美元时,基金业绩必然会衰落。
美国著名LP考夫曼基金也曾发表题为《我们遇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的分析文章,声称在其投资的近百只风险投资基金中,规模超过4亿美元 几乎所有基金都没有提供有吸引力的预期回报。在未能战胜股市的 62 只基金中,有 30 只的规模超过 4 亿美元。
此外,2024年12月,以红杉合伙人Matt Miller、A16z合伙人Michelle Waltz、Two Sigma合伙人Willy Ilcev为代表的一波“高管辞职设立个人基金”的趋势。Pitchbook的分析师团队进行了大规模采访与LP试图了解投资偏好的变化,最终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即使AI趋势的出现也有可能为LP带来比以前更多的投资机会。有限合伙人普遍认识到“越大并不意味着越好”。
这些数据和热点事件共同描述了从业者之间“脱节”的可能性。在所有相关讨论中,心情最严肃的就是李刚强老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非常直白地指出:我们的股权投资行业已经完全畸形了。
《蔑视链逻辑》
老袁和李刚强老师虽然说得很严厉,但在我看来他们其实都是乐观主义者,因为他们的讨论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隐性条件,那就是“为市场主导时代的回归做好准备”。如果他们是标准的保守派,他们很可能会看到“国资独大的时代可能刚刚走到一半”。
中国投资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3年国有资产平台分析报告》显示,近五年来,国有机构直接投资总规模逐年增长,2019年达到4322.07亿元。 2023年,并已获得全部创业资金。投资市场份额超过40%。如果从直接投资数量来看,2023年国有机构已经超过非国有机构,达到3676家。最直观、最有影响力的描述之一是,在过去五年获得投资的企业中,三分之一的企业获得了国有机构的直接投资。
考虑到股权投资基金的平均久期,这意味着“全面拥抱国资”的行业主题将持续至少五年。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时间跨度足以定义一个投资者的职业道路,“功能性失业”早已不再是“隐忧”。在此前提下,国有机构的“市场化”、“专业化”改革成为当代实践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例如,7月25日,成都高新区发布全生命周期投资基金运营制度,明确提出从80个以上提高种子、天使、创投、产业投资、并购基金等政策性基金的损失容忍度。 % 至 30%。设置。大批学员自发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转发这一消息,“极其大规模的宽容”成为最常见的形容词。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国务院办公厅1月7日发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要求“不得以吸引投资为目的设立政府投资基金”、“鼓励取消政府投资基金和管理人注册地限制”、“鼓励减少或取消返程投资”在“建立基金退出管理制度并制定退出方案”一项中,特别提到了“二级市场基金(S基金)”和“并购基金”两种退出机制。
主流解读认为,这一系列举措是试图在“风险投资的独特价值”和“国有资产的特殊社会分工”之间尽可能找到平衡点。这是国有资产快速发展后总结经验教训的必要修正。
彭哥不幸经历了以上这一切。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在省会城市的一家国资平台工作。他总是皱着眉头带着同行业的朋友喝咖啡,问有没有机会一起做点什么。去年,他感到压力很大,申请调岗,到集团其他业务部门工作。在他的回忆中,如果选择跳槽的同事还打算“留在投资行业”,基本上只能“在国资平台工作”。
至于原因,彭革的总结与老袁的观察类似。国有资产结构的投资并不需要太多的个人“洞察力”。系统中的很多人就像游戏中的NPC一样,等待着“来料加工”。久而久之,“知识”水平与市场化机构培养的投资者相差甚远。 “即使民企想要你,他们看重的也不是你的项目经验,而是你能有一些人脉。”
但如果要谈“事业”,鹏哥很容易举出反例。 “如果你是做PE/VC,特别是创投业务,在国资体系内,(功能性失业)可能会比较明显,但如果你是在战略、产业投资部门,那就不一定了。”他认为话题应该分开讨论,“这些部门给你提供的专业接触和专业经验非常复杂和多样,包括业务运营和(了解)国资系统……从事这一领域的兄弟应该去被投公司当战略总监,当董事会秘书没问题。”
小刘也持同样的观点。去年年初,小刘离开一家投行,加入一家国资平台。他还认为,国资对投资者职业生涯的塑造应该分开看待:如果是投前投资职位,那么“国资系统确实很难培养出所需的技能和简历”。金融投资”;但如果是中后台岗位,那么“国资系统反而可以让你更有竞争力”,因为目前的情况是国资所接触到的项目质量一般来说,比市场化资金资助的项目要低。“如果你看到的东西多了,处理的也多了,你的体验就会更好。强大的。”
即使纯粹从技术层面分析利益,国资体制仍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财政投资的基本动作是“判断行业前景、寻找项目、以合理价格投资”,而国资的行动则包括“判断当地产业培育的需求,寻找符合标准的项目,协调说服项目方、地方国资部门及一把手、内部资金负责人”等。不一定比金融投资更容易。”
李亚认为,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典型的“鄙视链逻辑”,“市场化更血腥、技术化”是一定程度的偏见。两年前,他通过各种面试进入了省会城市的一家国企。随后他迅速“卷起”,开始了“尽职调查、汇报、开会”的循环。加班的强度让他感觉“我还没离开北京”,业余时间又如此有限,“只能保证不缺睡眠”。
“我以前对市场化机构也有这样的刻板印象,但实际进来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很多国资内部要求非常高,启动和启动都非常困难。”结尾。”
与之前的工作相比,李亚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更符合他对“好工作”的定义——在他的职业观中,“好工作”有两种定义。第一个是组织足够丰富。晋升、加薪有空间、有明确的路径。二是工作内容和领导力比较强,能够给人明显的成长和学习机会,在整个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不断增强。
“市场化机构太多,良莠不齐,或者市场上不专业的机构很多。”他表示,“(在监管压力下)很多国资的投研能力已经强于市场化(机构)了。”
“要自洽,不要在灯下黑暗”
过去一周我和很多人谈论了“功能性失业”。有老袁这样“几经周折一直在国资身边”的人,有小刘、李亚这样“从市场来到国资”的人,还有彭这样的人葛先生“离开了国资第一线”。获得的见解五花八门,有人会质疑这个命题是否属实,原因是从风险偏好的角度来看,“国资平台”和“市场化机构”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就实际而言求职经历中,尝试以“国资”为跳板,打开市场化大门。案例几乎闻所未闻。
李刚强老师甚至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我们今天所抱怨的“变形”,本质上是过去绝大多数中国投资基金不给LP赚钱的结果。
一个从未真正表现出令人信服表现的职业被“边缘化”,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当然,我的每一次谈话都很顺利,因为大家也看到了“焦虑”的存在,然后共同提到了“自洽”的重要性。最令人不安的观点来自小刘,他说:“投资经理也需要判断自己行业的兴衰,不能总是判断别人(行业的兴衰)而对自己视而不见。” ”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风险投资史》一书中为风险投资家列出的三个“最重要”的能力:第一,风险投资家必须努力与冷酷的创始人建立联系;必须要有一颗坚强的心,才能熬过投资归零这一不可避免的黑暗时期;最后,风险投资家必须依靠高情商来鼓励和引导有才华但不守规矩的创始人。
——作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由此得出结论,伟大的风险投资家可以把自己变成调节企业家情绪波动的“工具”。我想我们也可以换个说法:正是通过一次次成功地挑战人性中难以逾越的情感波动,风险投资才有机会摆脱人们对“商业文明”的偏见,成为一个有机会成为一个职业的人。 “伟大的”。职业。
(文中老袁、鹏革、小刘、李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