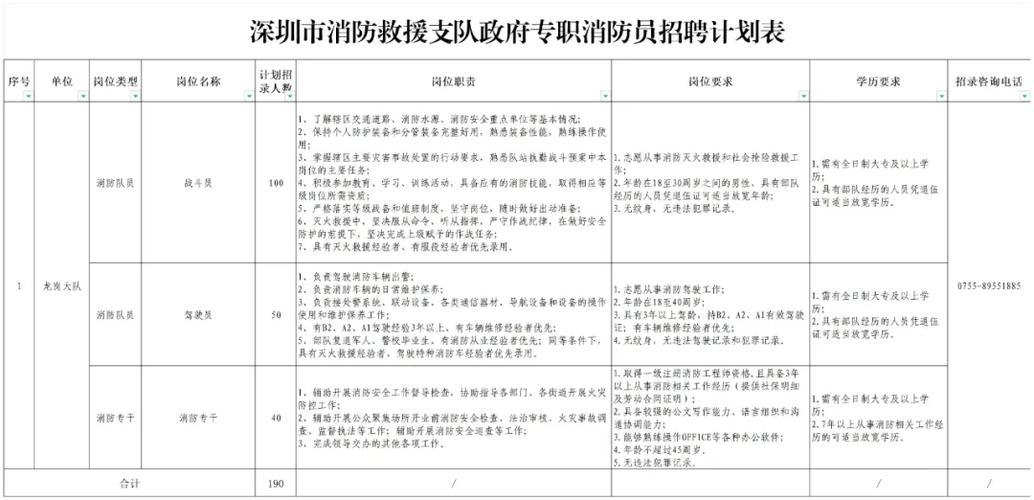天启五年至七年,也就是1625年到1627年,明廷对故宫“三殿”,即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进行了明代最后一次且规模最大的集中重建,此次重建是因为万历二十五年,也就是1597年,“三殿”受灾 。这场大火的详细情况,官方记录相当简洁:“三殿发生火灾……火从归极门燃起,蔓延到皇极等殿,文昭、武成二阁,以及周围廊房同时全部被烧毁……宫殿都遭受火灾,这是本朝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此后,经过万历、泰昌两朝长达二十多年的长时间准备,才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中修建。这场火灾被视作明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它对明朝中央的政治心理影响极其严重,对制度运行影响极其严重,对宫廷生活影响也极其严重,然而相关研究却十分匮乏。
笔者在阅读“明代档案”时,发现了三份与这次修建直接相关的兵部档案,这三份档案从一个侧面详细记载了三殿重修的过程,以及其存在的问题,以这三份档案为线索去探寻明末这次重修三殿的若干历史史实,会发现天启年间对故宫三大殿的重修,对晚明政局的走向有很深刻的揭示,其中包括皇权运行、宦官专制、晚明的财政运作等方面。

明代朱邦绘有此画作。画轴所描绘的是北京的皇宫紫禁城。它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图中左立者是明代紫禁城的设计者蒯祥。蒯祥是苏州人。他出身于木工世家。官至工部左侍郎。当时人称他为“蒯鲁班” 。画中的蒯祥下朝后,手里拿着笏板,站在承天门(也就是清代的天安门)金水桥西侧,午门、奉天门(即清代太和门)、奉天殿(即清代太和殿)在他身后,大明门、正阳门在他前面,身着明朝官服的官员们弯腰站在正阳门外,这幅画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院,是绢本设色 。
三份档案与三殿重修
有三份兵部档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第一份档案是“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皇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这份档案尾缺),时间是天启六年(1626)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二份档案是“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建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时间为天启七年七月十六日;第三份档案是“兵部为举劾皇工本卫指挥姚应爵等侵克军粮事行稿”,时间是天启七年八月初五日。原档被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它已被影印收录在《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三册)里,其档案编号分别是第260号、第286号、第294号。
第一份档案,编号为第260号,内容是“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皇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这份档案尾缺,时间是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份档案记录的是,兵部根据职方清吏司主事官员的奏请,给参与皇极殿做工的山东都司、河南都司第一、二、三、四拨的做工班军发放“赏银”这件事。奏疏表明,按照规定,参与修工的军人,每人每班应发赏银八分,其中五分由户部负责发放,三分由兵部负责。奏疏详细开列了,山东、河南二都司班军参与皇极殿修工的情况,这里分三拨,说明了每拨的起止时间,做工日期,领工官员姓名,做工人数,还提到了兵部应负责的银两数等 。
皇极殿原名为奉天殿,嘉靖时重修后改了名,其正式重修的时间是在天启帝即位之初。泰昌元年是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1620年,八月的时候,熹宗刚刚即位,就下诏说要传起建皇极门殿,选择日子开工,原因是文华殿狭窄矮小,百官朝贺列班不方便。当时辽饷越来越紧急,大规模工程开始建设,有关部门没有办法。于是工部请求发放内帑二百万,马上开工。“百官朝贺列班不便”这种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皇极等殿没有修建,这严重影响到国家典礼的举行,也影响到宫廷仪制的举行。万历末年的时候,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缵在向神宗上疏请求“修省”时也曾说过,“自从圣上英明统治天下以来,火灾示警的情况已经多次出现了。第一次出现在乾清宫,使得帝王居住的地方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第二次出现在皇极殿,导致没有了上朝理政的场所”。“视朝无所”,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从天启三年开始,皇极门进行了修复,皇极殿也在修建(尚未最终完工),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礼仪,比如朝贺、南郊、婚礼、岁贺、颁历等,已在皇极门或者皇极殿内象征性地举行了。
皇极殿完工时间比其他二殿早,赵翼称“天启六年九月,皇极殿成。七年八月,中极、建极殿成”,这里说的是主体建筑完成时间,《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六年四月,“内官监恭进‘皇极殿’牌额。得旨。所进三字,端严堪用。着即颁刻,择吉悬安”,六月时,熹宗说“皇极殿工已八九” 。到当年九月,礼部进天启七年祀册,当时皇帝在皇极门内殿。次年十月初一日,熹宗御皇极殿颁历,这表明皇极殿已投入使用。另外,信王朱由校(即后来的崇祯皇帝)的婚礼,时间在天启六年底至七年初,其仪式安排在皇极殿内举行。这既说明皇极殿已完成,功能也已恢复,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皇极殿的政治地位此前确实受到了很大影响。
第一份兵部“行稿”指出,河南、山东二都司班军参与皇极殿做工,时间起始于天启六年七月初一日,每拨时长为15天,每拨人数在700人至1100人之间,人数不固定。每拨有3批军人同时进行做工,连续至少有4拨人马参与(结合第二份档案可知,同时用工达八九拨),此时有数千名班军在皇极殿等地做工,工程量颇为巨大。从工程进度看,这拨班军负责的应该是这次大修的扫尾工作。

第二份档案,编号为第286号,内容是“兵部为开列依遵拨给建极殿做工班军赏银事行稿”,时间是天启七年七月十六日。
其内容是兵部职方清吏司上疏奏明,按照规定给参与建极殿做工的中都等三都司的班军发放赏银,这三都司是中都留守司、山东都司、河南都司,发放的是第柒、捌、玖等三拨赏银。按照第一份奏议的相同规定,参加修工的都司班军,每人每班应发赏银八分,其中五分由户部负责发放,三分由兵部负责。参与做工的有中都、山东、河南三都司的班军,每拨时间同样是15天(或以实际15天计算),每拨各有领工官的名字,还有兵部应当负责的银两数等,不同的是,这份完整奏疏所列人数比修皇极殿的人数更多,做工时间是天启七年四月十八日至六月初八日 。
建极殿,其原名谨身殿,在嘉靖年间重修后更名;中极殿,其原名华盖殿,于嘉靖时期改名,二者是同时修建的,竣工时间为天启七年八月,这也标志着“三殿”重修工程最终完成。
熹宗本人喜欢土木建筑、工程制造,他对中极、建极二殿的修建颇为关注,《明熹宗实录》简洁地记载了两大殿重修的主要环节,还记载了熹宗亲自过问的主要仪式。
天启六年十一月庚辰日,建极殿竖立金柱,朝廷派遣尚书薛凤翔行礼,赏赐辅臣黄立极等人不同数量的银币。天启七年二月己亥日,迎接建极殿金梁,赏赐辅臣黄立极等人茶叶。同月辛丑日,建极殿升梁,赏赐辅臣黄立极等人茶叶。乙巳日,因为建极殿升梁,赏赐辅臣黄立极等人每人五十两银子。三月丙申日,因为建极殿安装吻兽,赏赐辅臣黄立极等人每人五十两银子。
中极殿的金梁安装稍稍晚于建极殿约两月,据载:
迎接中极殿的金梁,皇上命令举行升梁祭告仪式,派遣工部尚书薛凤翔去迎接梁,神木厂尚书杨梦衮、广渠门尚书孙杰、正阳门尚书崔呈秀、大明门尚书王之臣、午门尚书郭允厚、皇极门尚书周应秋,各自进行行礼。……己卯这天,中极殿举行升梁仪式,赏赐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木普】每人白银五十两,中书官张承爵等人每人五两。
中极殿举行升梁仪式,这是三大殿工程浩大且隆重的仪式,崔呈秀等“阉党”成员纷纷出来迎接,其中蕴含的政治深意有待分析。
到了天启七年八月乙未这一天,中极殿、建极殿插剑悬牌仪式举行,三大殿重建工作基本完成。十天之后,也就是甲寅日,司礼监王体乾传达熹宗的意思,宣布“殿工告成”,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随即奉命题请皇上向天下宣告此事。第二天,“皇上在乾清宫驾崩”。三殿完工,熹宗就去世了。可以这么讲,熹宗在位的这一朝,也是三大殿进行重建的时期,三殿的修建,从始至终,贯穿了他在位的七年时间。
第二份档案记载了三都司的做工时间,开始于四月十八日,截止到六月初八日,这时金梁已经升起,距离完工还有一个多月,不过也进入了大殿修建的最后收尾阶段,没有延续到三大殿建成之后的扫尾,大概是因为熹宗病重(并且很快去世),宣布殿工告成,这样更有政治意义。
第三份是三都司班军参与大殿修建的兵部档案,编号为第294号,题名是“兵部为举劾皇工本卫指挥姚应爵等侵克军粮事行稿”,日期是天启七年八月初五日,此为中都司所领参与三殿修筑官军举报军粮被侵占一事的行稿。滁州卫班军林春芳称,他们于天启七年正月十六日“接替皇工”,应当分得的军饷被卫指挥“侵冒”,数量达300两之多。

这份档案没有明确指出滁州卫班军参与的“皇工”是三殿的修建,不过,从班军到京参与做工的规定来看,从班军参加做工的时间来看,从班军军饷的数量来看,林春芳等班军参加的必定是三殿大修。
第一份档案已不完整,它记载的班军做工分为四拨,分别编为一、二、三、四等,时间是天启六年的七、八月间;第二份档案是完整的,其记载的班军做工编号为七、八、九等,共三拨,时间在天启七年的四、五、六这三个月。这里恰恰缺少了天启六年下半年到七年年初这段时间,这大概就是第五、六等拨上班做工的时间。
三殿重修费用与晚明财政状况
三份档案共同的议题是,参与修筑三大殿的班军,其赏银和粮饷的问题。领班官和做工军人在一线工作,非常辛苦。然而,他们获得的奖赏或补助相当有限。与那些仅象征性地参与巡视、阅视的内官、阁臣、六部尚书和主管的高级武官所受封赏相比,他们得到的辛苦钱少得可怜。即便这样,他们还常常被官员克扣或侵冒。
班军参与工程修筑,除了正常发放粮饷,也就是月粮和行粮之外,按惯例还有“补助”费,其中包括“工价犒赏恤银”,还有“工价银”,以及“盐菜银”,另外还有“赏赐银”等,这些都被纳入了正常预算编制。从嘉靖朝开始,历经隆庆朝、万历朝、天启朝,一直到崇祯朝,这些做工补助在班军成为主要的建筑力量后就已经存在了,它们的名称不完全一样,含义也不完全一样,数量有高有低,不过其补贴的性质是一样的。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户部提出请求,称京操班军在修工时,既有行粮,又有赏赐,因此请求减汰,具体内容为:减赏粮以节省不必要的开支。还表示各省班军已有行月口粮,在免操后前往工所服役时,仍额外加支赏粮四斗,这显得过多,应减半……班军赴工劳作比操练更为辛苦,所以不应减赏 。
隆、万年间,明中央大规模修建边墙,将边地军兵和京操班军全部派遣去参与修筑 。工程紧急,修筑工作非常辛苦 ,同时为保证边墙质量 ,政府按照惯例给参与修工者发放“工价犒恤银” 。发放标准是依据修筑边墙的数量和质量来核算发放 ,即“计台墙之丈尺而给工价焉。工完则每军犒恤银七分” 。工价银在修筑过程中发放,用来补充班军日常生活所需的资金,犒恤银通常是在修完工程、等待验收完毕之后发放,发放依据是工程完成的数量和质量,如果发现有质量问题,不仅领班官军会受到降职革任的处罚,已经发放的犒恤银也要收回用作重新修筑的费用。
明末时,参加修筑的军兵有劳动补贴,这补贴被称作“盐菜银”,实际上它就是此前一直施行的工犒银,只是标准稍微高一点。给上班修造官军发放盐菜补助,在崇祯朝以前就存在,比如天启四年以前,南直隶东、西二海所上班官军“有安家费,有大粮,还有月米盐菜等项目”。军人在京做工,其做工补助标准大致按照上述标准执行。
国家进行重大工程修建时,会动用全国的力量。除了工部之外,礼部、户部和兵部也会参与其中。礼部从典制方面参与,户部从财务方面参与,兵部从用工等方面参与,并且这三个部门都要分摊费用。做工劳务和修筑费用大多按照“户七兵三”的比例来担负。到了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说:“近日蓟门三年小修的规则中,其中用于工程犒劳的银两,是按照户七兵三的比例分担的。兵部的三分出自冏寺,户部的七分出自太仓。这是一直以来的旧例。”
三份档案中提到修建三殿班军,“(每拨)每军赏劳银捌分,内户部五分,兵部三分”,意思是每名工作每参加一拨(15天),就能一次性获得赏劳银8分。其中5分来自户部,由云南清吏司兑付。3分来自兵部,由太仆寺负责兑付。
太仆寺(行太仆寺)负责管辖全国的官牧和民牧马政,它隶属于兵部。依据《明史·职官志》,太仆寺的职责主要如下:

太仆寺设有卿一人,官阶为从三品,还设有少卿二人,官阶是正四品,正德十一年又增设一人……卿负责掌管牧马的政令,要听从兵部的安排。少卿一人协助处理寺内事务,一人监督营马,一人监督畿马……对于已经开垦成田的草场,每年收取其租金,遇到灾害时就拿出这些租金来辅助购买马匹。对于赔偿折纳的情况,就征收马金并输送给兵部。主簿负责掌管检查文书往来。大使负责掌管储存库马金。
官牧主要是各都司卫所养的马匹,民牧是司府州县分别养马,太仆寺设老库贮存马价银,用来调剂用马。至迟在嘉靖年间,马匹以及草场等相关收入一直有专供军政事务的特性。此后,因为官牧逐渐荒废,而民牧陪补让百姓受累,隆庆年间就采纳了太仆少卿武金的建议,把民牧种马出售一半,折算成银子入库。到万历九年(1581)五月,民间种马被尽数卖掉,种马以折价形式进入太仆寺冏库收贮。但从万历中期开始,军兵催饷之急如同星火,政府只能动用仅有的太仆寺银来救急。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司卿称,“今春若不是承蒙皇上允许借寺银百万,几乎无法支撑。目前九边的饷银、三大营军马草料布花的费用,又变得紧迫了” 。他觉得,太仓银和太仆寺马价银都是皇上的钱财,而且按照时节使用,应该先重视数额巨大的,总之都是皇上要用的,并且在当时能起到帮助,正好可以灵活变通,等等。这次借支受到了太仆寺署事少卿李恩孝的反驳,李恩孝说户部已经从太仆寺借用了高达990万两的马价银。很明显,明朝后期,太仆寺银库成了解决军饷不够的重要办法。天启年间,崇祯年间,太仆寺是兵部下设机构,太仆寺负担兵部的费用支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三份档案的主要内容是班军粮饷被侵冒,侵冒军兵钱粮这种情况,在有明一代的军队里普遍存在。为避免班军粮钱(包含月粮、行粮、盐菜、犒赏银等)在发放时被侵冒,明中央想尽各种办法,还形成了较为严格的制度,用来防止官员作弊。如官员唱名、班军亲领、附以监察等,规定有:“凡发放班军钱粮,一以督工二衙门号领为据,职立一定规则,凡有领银,俱于先日投领,次日发放,一刻不爽,必不稍有参差错乱,以滋军士守候之苦,开吏胥需索之端。”放银的时候,要与官军一起打开鞘进行称兑,务必保证毫厘不差,官军自行查验,核对数目足够后再发放,所有打点使用、克扣短少等陋规,都已消除干净。关领本色也和折色一样,提前一天申请领取,第二天在仓库发放,我仍会时常稽查,委派官员监督查看,并且在各军下次领粮时,当面核实上次领粮的数量,务必保证一升一合都不短缺。实际上,发放时克扣现象极为常见。
重建三殿总的花费,明朝官方公布,仅白银将近六百万两。
工部上奏,三殿大工程于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开始动工,到七年八月初二宣告竣工,总计发放钱粮并给予领状的,共有五百七十八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两八钱三分八厘二毫二丝八忽六微,应当找补的共计三十万零一百三十三两八钱九分四厘七毫五微,透支的为一十三万零七百四十九两九钱四分四厘二毫二丝,对外兑换的总共一十三万九千一百五十三两三钱八分一厘六毫九丝,所花费的银子总计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一十九两七钱六分八厘四毫一丝六忽一微。虽前朝册籍无可稽考,而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也。
得到圣旨,阅览奏章“三殿鼎建,历经两年告成,工程浩大但费用节省,全依赖厂臣精心谋划,尽力筹措,因此顶石的运输,楠杉的采伐,节省金钱数百万,而且禁止苛刻体恤民力,百姓欣然前来,功劳特别高”。说得对。这核算钱粮,从开工到竣工,总计五百九十五万七千五百两有余,可见稽核详细严谨,还应将册案交付史馆,用以彰显实录。其丈夫从事匠铺车等劳役,所给银子未交完的,必须从外地解送补还,要行文各省直严厉催促,已上报的助工银两,迅速向内解送,以便完成工程局事务。
三殿被毁坏的时候,明朝中央的财政已经出现了颇为严重的问题,皇室的费用、官员俸禄的开支、军费年例等日常开支已经相当庞大,而且战争支出也不是一个小数目。三殿二宫全都被毁坏,这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大灾之后,神宗君臣们惊魂稍微安定下来,就开始谋划修复作为国家权力运行象征的三大殿,并且想办法筹措巨额的修建费用。
《明史·食货五》记载,等到两宫三殿遭遇火灾,营建费用极其高昂,这才开始开矿增加赋税……宦官遍布天下,不是负责征税就是负责开矿,逼迫威胁官吏,致力于搜刮民脂民膏。致使万历中后期民怨沸腾的“矿监税使”开征的托辞是重修三殿。两宫三殿对大明王朝的重要性非常明显,好像没办法反对修建,然而中使到处都是、矿监税使遍地的危害也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进言“时事可痛哭者八事”,批评了借“三殿之名”致使矿监税使遍布天下的现象,称“榷税之使遍布天下,导致灾异屡屡出现,又以三殿为名,搜刮聚敛没有一日停歇,正如诗中所说:‘小东大东,杼轴其空’,此为可痛哭者七”。此后神宗因身体原因,曾一度打算停止监税之派,然而身体康复后,却更加变本加厉 。万历四十三年(1615),江西抚臣王佐反映,湖口税役对地方造成横扰,希望等三殿工程有一定进展后,奏请停止,这既揭露了矿监税使的恶果,又体现出对三殿修工的无奈,官员们这种态度在明末时更为突出 。
湖广巡抚梁见孟上奏疏建议,斟酌催促大木来接济宫殿工程。他说三大殿开始动工,全国共同欢庆。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愿意像子女为父母尽力一样,湖广原本分派大木二万四千六百根,后来因为受灾百姓疲惫而减少分派十分之三,分五次运送并起程,查督运木道路涉及四川、贵州、湖广三省,新运送的几乎达到七分之数,第一次运送已经交付工厂,第二次运送正在上报解送的途中。如今部里咨复派金柱三百八十根,每根长六丈四尺,围一丈五尺,明梁等一百六十余根,每根长五丈五尺,高三尺五寸,这些都是异常巨大的木材,而且要求在一年之内完成。私下考虑,楚地并非产木的地区,向来是从黔蜀求取木材,而巨大的木材生长在深山绝壑、人迹罕至的地方,要经过千百年才能成材,商民冒着毒瘴,踏着蛇虺,众人齐声呼喊,排开岩石,劈开荆棘,历经很长时间才到达江河 。然而这样的特殊木材,从嘉靖年间开始就已经难以获取了,如今树木被采伐得凋零残败,山势险峻路途遥远,即便搜寻获取一两根都很困难,更何况要三百多根呢。所以数量要求太奢侈,应该商议减少摊派;获取材料非常特殊,应该商议给予补贴;限定的期限非常紧迫,应该商议放宽期限 。请求下令复查或者酌情减少株数,依照嘉靖年间题准的帮折之例,若是长度足够但周长不足,周长合适但长度不足,以及长度和周长虽合适但根部与梢部不相称,还有木材没有瑕疵但长度和周长稍差的,都准许起运,仍然稍微放宽期限,以便购买获取,那么大工程不会受到影响,地方也不会导致严重困难了。
这里很能体现当时官员对三殿大工程的态度,没人明确表示反对,由于三殿是国家典礼政务处理的重要地方,重修的缘由是合理的,三殿遭受灾害,影响非常大。万历帝甚至把此当作不朝见大臣、不出席典礼、不举行仪式的原因。不过针对大殿修建过程中的诸多问题,许多大臣提出疑问,期望宽缓民力,多些通融。实际上,矿监税使给整个明王朝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一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许多学者认为,矿监税使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

矿监税使最终停罢,是在神宗去世之后。
废除天下矿税的诏令旨意。先前开矿抽税,是因为三殿两宫尚未修建,国库空虚,才权且采用这种办法。近来由于辽东奴酋叛逆,户部已经加派了地亩钱粮,如今将矿税全部停止,通湾等地的税监张烨、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人,都要召回,那些正在征收且在官府的税银要解送进京。从万历乙未年起,大规模工程开始营建,武弁和市井狡猾之徒以开矿为由上奏,众多宦官在其中主持,矿事于是兴起,榷税也随之产生,朝廷派遣宦官四处出动,而首先挑起事端的武弁和狡猾之徒成为其爪牙,那些奸邪谋利之徒凭借差遣的机会,称之为奏带。宦官所到之处都引发骚乱,驿站遭受极大痛苦,普通百姓有向内输送财物却得不偿失的情况,甚至到了设店征税,连鸡和猪都要计算在内,税收以万计,官员仅得到其中十分之一。在神宗晚年的时候,也曾商议停止、商议减半来资助经费,然而残余的弊端仍未消除。到这时,遵照遗命,全部免除。后来又有各内使接到要把被征缴以及拖欠的等税银,都亲自押解进献的旨意。兵部尚书黄嘉善又奏请所押解进献的,应该以本年七月前已经征收到的为准,不要再因为拖欠而使百姓受扰。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关卡、集市、山林、湖泽等一切不合理的征敛,都因此被全部清除。
这里特别提到,因为辽东用兵,户部已在田亩加派。言下之意或许有两点,其一,修筑之费的问题能够通过别的途径加以解决;其二,如果继续开矿抽税,百姓负担会更加沉重。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矿监税使给广大百姓带来了祸害。以修建三殿为名派出的矿监税使,对明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使得社会矛盾激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开矿抽税所获收入,明显无法满足三大殿的修筑费用,况且这笔经费也做不到专款专用,熹宗即位后,便宣布要重建三殿,除了神宗已有的积蓄,还包含从西南地区大量采征的木材等建筑材料,另外还向内外臣工、士农工商进行广泛的劝捐。首先是内外大小文武百官都要通行捐款一年,据天启六年督察工程的崔呈秀说,各官要捐出俸禄并催缴外面解送的积欠,得到旨意,大工程费用繁多,物力耗费巨大,内外大小文武百官都要通行捐俸,这原本是会典的旧例,要等三殿建成后才允许开支,只有庶常教职以及行人、京卫指挥、千百户不在此例,各省直历年拖欠等项银两,要派御史前去催促查问解送,并酌情商议后饬令执行。后宫群体响应了号召,参与了捐款 ,“今中宫等官员,诸王、公主,以及司礼监等衙门、各监局司库掌印管事牌子,还有内外私家闲住太监等官员,恭敬地进献了助工银共四十万两,都发到公所贮存收纳” 。
熹宗赞扬其“大费省皆赖厂臣心计经营”,工部也觉得“虽前朝册籍无可稽考,而工倍费省,未有如斯举者也”,这样的结语自是官样文章 ,笔者未查到这些经费的花销情况 。
回到三份档案中记载的参与做工班军的“赏银”,这可看作是整个三殿大作工程开销的一部分。在明朝多数时间,只要参与做工,工人都会得到相应津贴。三殿完工后,作为劳动者的他们,从兵部、户部分别得到了3分、5分,共计8分银的赏赐。他们每组1000人,一共获得80两银子,其中兵部给30两,户部给50两。
明廷为庆祝三殿完工,对参与重建的几位重要大臣予以奖赏,奖赏环节包括参与立金柱、迎金梁和升梁等,赏赐不过赐茶,或者赏银50两、20两,赏赐范围远远不如同期因“宁锦大捷”的赏赐范围广,后者赏赐总额多得多,从官、军获得的“赏赐”数量来看,晚明财政状况非常困窘。
不过,重修三大殿的时候,正值宦官魏忠贤权势极大、在朝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宦官群体,还有依附于有权势的宦官的王公大臣,他们在修三大殿时所起的作用值得关注。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内臣权势很重,利用修建和完工三大殿的时机,极力彰显自己的地位 。
天启七年八月己亥这一天,礼部上奏说三殿已经建成,请求选择吉日皇帝前往视察。于是,各个部门都纷纷呈上奏表表示祝贺,这些表文的言辞中透露出了当时宦官专权的政治局势状态。工部尚书薛凤翔呈上奏章陈述殿宇工程情况,得到圣旨:
三朝旷典,长久以来需要适逢其会,才过去两年,就恢复了旧有的规矩,这实在依赖厂臣魏忠贤,他生来符合名世的标准,禀赋来自天地间的正气,真的怀有与国家同甘共苦的心意,卓越地肩负起天下安危的期望。他平定危局救济弱小,就如同炼石补天,揭露隐藏的奸邪,就像铸鼎刻画事物。他清扫反复无常的世界,使之回归太平,振奋怠惰的人情,使之归于整肃。他的法令如金科玉律,让盘踞一方的恶势力心寒,他的恩泽如湛露甘霖,使市井百姓都感受到滋润。河水干涸,鸡犬安宁,三藩之地彩船频繁往来,边塞之地的勇猛之士径直出使,多年的风声鹤唳都已平定,巨鳌之足稳固于地轴,彗星陨落于天街,伟大的功业,岂是容易一一列举的?
这段材料,对魏忠贤进行了极力吹捧,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赞誉之词对于权臣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由此可以看出宦官擅权所带来的灾祸 。

同时,吏科右给事中陈尔翼也奏表称贺:
臣恭敬地看到三殿建成,盛大的典礼开始举行,天下各处都安宁平静。……因为能协助完成大典并节省费用,地方百姓因此受益,这都是厂臣为国的宏大谋划、匡正时世的伟大谋略才达到这样的局面。而且皇上能得到得力的辅佐之人,也由此可见一斑了。如果厂臣把独自承担的责任当作众人分担的责任,那么依臣看来……
文中所说的“厂臣”,从字面意思看是指“东厂、西厂的主官”,实际上专门指宦官魏忠贤。根据《明史·魏忠贤传》记载,“所有的奏疏,都称‘厂臣’而不直呼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拟写圣旨时,也必定说‘朕与厂臣’,没有人敢直呼‘忠贤’的名字”。魏忠贤权势极大,外廷官员谄媚的丑态暴露无遗。当然,魏忠贤的党羽崔呈秀、杨梦衮等人也因此各自得到了丰厚的封赏。
对于天启年间三殿的重新修建,明末刘若愚针对熹宗、魏忠贤在修筑过程中的心态以及其政治目的,有着自己的分析,他的分析虽然不是很全面,不过也并非没有道理:
圣性喜好盖房,只要是自己操持斧锯凿削,就算是巧工也比不上。……太阿之柄下移,南乐、蓟州、东光这类人以及在京的徐大化等人,是一条线索,就像鼓槌击鼓一样迅速响应。先帝每次营造得意,就会忘记膳饮,感觉不到寒暑,可惜玉体的心思精力,都耗费在这里了。然而皇极等三殿在天启年间落成,继承父业,先帝喜好土木之事,难道也是天启年间就有预兆了吗?抑制贤能之士的干练济世才智,刻意留下督促催办的迹象,或许是想借此难以消除吧?考察万历中年,乾清、坤宁两宫建成,神宗皇帝命令正一真人张国祥率领数十名道士在宫中举行黄箓大醮,圣上的德行感动上天,曾出现群鹤飞鸣环绕的祥瑞。到皇极等三殿建成,魏忠贤等人只贪图庇荫赏赐作为自己的荣耀罢了!
这段史料常被后世史家引据,它将熹宗因喜好匠作致使阉人乱政贻误大明江山作为内容,把天启年间重修三殿与晚明政局结合在一起思考,这是值得深思的。
晚明时期,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开始,神宗以修建三殿为借口,肆意派遣矿监税使,搜刮百姓钱财。即便遭遇重大天灾和人祸,出现边民叛乱,发生征倭之战,也只会让统治者的贪欲加剧,然而始终没有启动三殿大工程。到了万历末年,努尔哈赤起兵,辽东地区为之震动。天启即位后停止了监使之派,然而却迅速启动了三殿重修工程,整个天启一朝,出现了朝野东林与阉党之祸,令人惊讶的是,耗资巨大的三殿居然顺利竣工。到了工程完成的时候,熹宗驾崩,辽东战局变得更加紧张,陕西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起。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历史发展,在提醒我们要重新思考明末的政局。
万历年间,三殿不修,原因在于他长期怠政,还在于他对把控晚明政局充满自信。天启喜好土木工程,当时大家普遍觉得财政困难,宦官专权、文恬武嬉的政局是实情,班军制度早就遭人唾骂,然而修筑三殿的人力却能得到充分保障,三都司班军几乎以完整队伍、近两万人的规模照常上班,按期完工,明代后期军事动员的效率不可小看。即便存在天灾,即便有人祸,即便有民灾,即便有辽东战事,似乎晚明财政已濒临破产,然而六百万两白银的大工支出,居然能够顺利筹措,这表明晚明国家财政能力同样不可被过度低估。
明中央对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能进行有效控制,这种控制在三殿大修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所以,绝对不能过度低估明清交替之际明朝的综合国力。决定明清交替进程的偶然因素,远比必然因素要多,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本文选摘自彭勇所著的《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该书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25年4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进行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