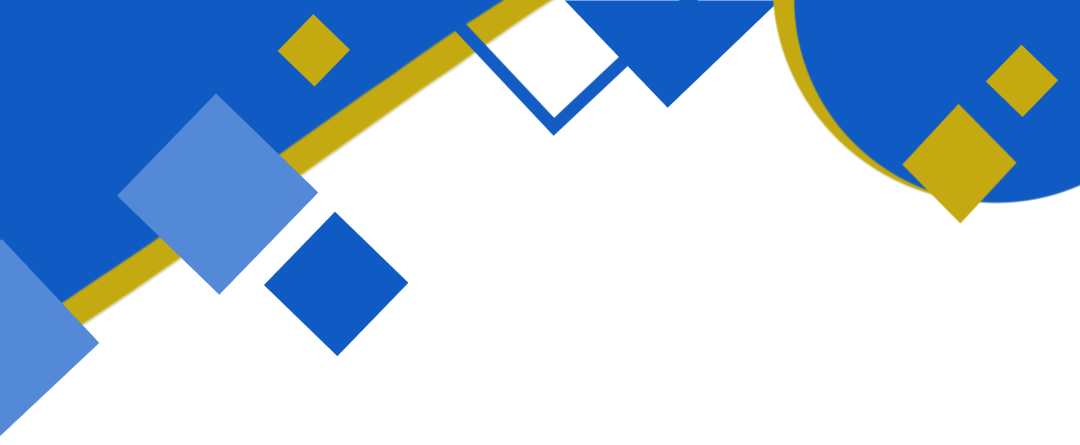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看·见殷商”展览最新增加了展品,其中四件新展品里,有三件源自河南安阳妇好墓的陪葬物,这让人们对这位商代多才多艺的杰出女性产生了关注。

鸟之崇尚
妇好墓出土玉器共七百五十五件,是商代所有墓葬中发现的玉器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一个。这些玉器涵盖了所有种类,装饰品数量最为突出,其次是礼器、工具、仪仗器,而生活用器则相对稀少。在众多玉器造型中,动物形状的玉器是妇好墓出土玉器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无论是片雕、圆雕,还是饰件、摆件,如此大规模集中出土的现象,在商代所有已发掘的墓葬中尚未找到第二个实例。
出土的玉器里,有一件白色玉鸟,上面带有少量黑点,它的形状像刻刀,做工非常精致。刀刃两面打磨光滑,看起来像一只长尾小鸟,正保持着站立的姿势。鸟的头上有两个大圆眼,是用阴刻的方式雕刻出来的,尖尖的嘴巴向前突出,尾巴自然下垂,翅膀收拢,整体呈现出一种沉稳安静的神态。
这件玉鸟刻刀的形态是写实的,并不是凤凰类的夸张变形样式。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双爪位置有微小的孔洞,这些孔洞应该用来穿线,以便能够挂在身上。

玉鸟刻刀
妇好墓出土玉器,以绿色最为普遍,具体包括墨绿、茶绿、黄绿、淡绿等品种;黄褐色和棕褐色玉器数量相对较少;白色、灰色、黄色玉器则十分罕见;仅有四件黑色玉器。其中,通体呈现白色的玉鸟刻刀,因其稀有而显得格外珍贵。
鸟类,自古时候起,就是人类寄托心绪的象征物。在远古的捕鱼打猎生涯里,人们对于山林水泽间居住的飞行动物怀有深深的崇敬,它们既能展翅高飞于云霄,也能随时停歇在草野,人们视这种无拘无束为神赐的非凡本领,对鸟类的敬仰因此产生。
殷商年代,凤鸟作为玄鸟,为商朝的象征,被视为“上苍旨意归于商”的吉兆,在商朝民众眼中备受尊崇。妇好墓发掘出诸多玉器,其中包括代表尊贵身份的“玉凤”,其造型简练而雄浑,形态逼真且透出神秘气息,似乎凝聚了商朝持续六百年的壮阔气象。
妇好鸮尊
妇好墓主对鸟类有着特别的喜爱,生前和死后都收藏了不少与鸟有关的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青铜鸮尊这件作品。这件妇好鸮尊也是这次殷商展览中最受观众瞩目的两件展品之一。
猫头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鸮,它那与众不同的样貌和只在夜晚活动的特点,激发了商代人的想象力,让他们认为这是一只能在黑暗中看透一切的神奇鸟类,它的聪慧和非凡甚至超过了勇猛的老虎、凶恶的熊,乃至传说中的龙。
1976年,在妇好墓中发现的一对鸮尊,其形象十分独特传神。这些鸮尊的头颅微微抬起,头上竖立的双角,仿佛正专注地侦听四周的潜在威胁,随时准备猛地腾空,展开搏斗。这种孤高的神态,鸮尊的全身布满了华丽的装饰,图案复杂多样,主要纹样之上又叠加了用阴刻方式制作的云形纹饰等,被后人称为“三层花”,这是商朝晚期逐渐形成的一种青铜装饰“新风格”,也是商朝后期青铜铸造技术达到顶峰的象征之一。
这两件制作精良的鸮形器分别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由于展览安排的缘故,它们已经各自被送回原处,不过最近从妇好墓出土的三件文物,继续传递着它们所蕴含的历史情感。
国之大事
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几乎包括了殷墟所有青铜器的种类和样式,共计468件,其中祭祀用的器具210件,兵器134件。展厅入口处陈列的蛇纹铜铲就是这些器物中的一个。它整体上粗下细,铲口两端向内翻卷,带有平整的刃口;铲身中部两侧微微向内收敛;手柄部位和两端装饰着菱形图案,转折处略微圆润,手柄是直的。安装手柄的孔洞为椭圆形,里面残留着腐朽的木头,证明原先安装过一个木制的手柄在里面。蛇纹铜铲是商代人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用工具上升为礼器的代表。

蛇纹铜铲
另一种青铜兵器是古代礼仪和战争场合的代表作品。这件兵器竖立起来形似头盔,顶部雕刻着龙纹,龙眼呈圆形,独角向上,嘴唇向下,身躯短小且尾部卷曲。龙纹下方连接着扁平的长条形柄,柄的底部较宽,边缘厚重且没有锋刃,顶部装饰着云形图案和三角形图案。

戈形器
国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祭祀和军事行动,在青铜器方面,这主要表现在钺和戈上,钺是举行仪式用的器具,属于祭祀范畴,戈是用于战斗的兵器,属于军事行动的范畴。
遇见妇好
这次展览中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创新展示方式,考古专家们参照安阳殷墟遗址数十年来积累的大量考古成果,在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研究之后,力求重现了妇好的外貌和穿着。
研究人员最初检测了与妇好同代商朝遗骸的基因,确认墓主属于中原古老类型。这类商朝人的相貌特征,在出土的石像、玉像及青铜像中都有相似表现:鼻梁突出,颧骨高耸,眼型偏长。这些发现构成了最可靠的考古证据,为塑造王后形象提供了确凿依据。最终创作出妇好墓主人的三个具体样貌,这些形象陈列在本展览与妇好墓出土文物旁边,为观众提供立体且直接的视觉感受。
展墙上的屏幕里,妇好身著三种服饰,分别象征她的三种身份:王后身份,母亲身份,以及女将身份。作为一国之后,这是这位杰出女性的社会定位,作为母亲,这是她的家庭定位,作为巾帼英雄,这是她的历史定位。展览用白色袍子,棕黄色袍子,和战袍来区分这三种形象。
手持斧钺、披挂铠甲的妇好,正是统率军队出征时的威严模样,白色战袍是商朝权贵阶层的通用服饰,这种色彩的选择并非偶然。
司马迁于《史记·殷本纪》亦载有“殷尚白”之记述,其言曰:“汤遂更定历法,变换衣物色彩,尊崇白色,于日间举行朝堂集会。”商汤登基执政,对历法进行更革,对器具衣饰的色调予以更换,以白色为尊,在白昼时分开展朝见聚会。
画中妇好所佩戴的饰物,也展示了商朝权贵所用饰品的情况和穿戴习惯,许多出土的商朝权贵遗骸中,都发现了陪葬的饰品作为证据。所以,这次展览首次呈现的妇好穿白色衣裳的样貌,更像是她真实历史上的装扮。这样的处理方式,让这位三千年前的人物,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了。
“妇好”这两个字,在古代文字记录里频繁出现,次数达到数百回。经过郭沫若和唐兰的研究分析,确认妇好是商朝时期盘庚迁都到殷地之后,武丁的第二个君主所娶的皇后。根据占卜的刻辞文献所载,她擅长主持宗教仪式,同时具备军事才能,身份非常尊贵,和武丁的感情十分要好。在武丁使国家重新兴盛的这段历史里,妇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妇好离世之后,获得“辛”的谥号,武丁对她怀念不已,不仅为她举办过三次阴间婚礼,还破格将她的安葬之地设置在宫室附近,这样他就能经常前往探望。
最令人惊叹的是,这位声名显赫的古代女性,其陵墓由一位当代卓越的女性学者率领团队发掘。1975年,妇好墓所在的河南安阳小屯村计划将附近一座高地进行整治。该区域属于殷墟的宫殿庙宇地带,处在殷墟遗址的守护范围之内,尚未进行发掘。殷墟的墓穴大多设置在洹河的南岸,宫殿区则没有这类遗迹,而且妇好墓的藏匿地点非常隐秘,极不容易被找到。1976年春天,根据现场考察的结果,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郑振香确信宫殿区某处夯土之下必定有重要建筑,她便带领工作人员用探测工具从夯土的侧面向下挖掘。
那是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是个阳光明媚的周日,连续数日的搜寻后,队员们大多显露沮丧和劳累的样子,郑振香却愈发充满干劲,她激励众人今天的使命就是要挖到深处。尽管反复使用探测工具均无结果,她还是凭借自身的考古学识和直觉,认定必须继续挖掘下去。技工潜入8米深时,探铲中见到明亮的红漆碎片、青绿色的玉饰,一座沉寂三千余年的商代古墓因此显露原貌。我们这般方式,与妇好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