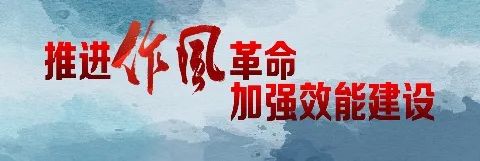旧金山那里,有个中国项目在运作,外界普遍认为,这是硅谷最讳莫如深的内幕之一。
一接触帕迪·科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他就一边演示刚才在DeepSeek上查询的内容,一边说明,那些完全不搞AI的企业,都在推进DeepSeek的本地化实施。“既然有了这个,还有谁愿意花钱使用OpenAI或Anthropic呢?”
帕迪·科斯格雷夫
帕迪·科斯格雷夫担任Web Summit的负责人,同时是该组织的发起人,Web Summit是欧洲首屈一指的科技论坛,也是全球规模宏大的科技盛事之一,至今已经举办了十六届,亲历了数轮科技领域的风起云涌。现在,这个国际性科技论坛已经吸引了一百多万参与者,包括特斯拉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斯克,OpenAI的创始人山姆·奥尔特曼,知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加拿大前国家领导人特鲁多,美国前副国家元首戈尔,黑石公司的共同建立者苏世民,以及美国顶尖风险投资机构之一凯鹏华盈的合伙人Mood Rowghani,他们这些人都曾是这个论坛的发言嘉宾。
Web Summit现场
我们在张江科学城对面的希尔顿酒店有过短暂的碰面,他刚刚在浦江创新论坛上完成了发言。帕迪·科斯格雷夫的中国访问日程安排得非常满,上周他到了北京、广州、深圳,这周抵达上海,后面还要去杭州,他似乎想把中国最有创新活力的城市都走一遍。
帕迪·科斯格雷夫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将在人工智能科技竞争中超越美国,这个判断依据核心期刊的高引用数据,也参考了硅谷众多企业中中国员工的比例。就连美国国内,一些新兴的AI企业本质上也带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帕迪·科斯格雷夫如此指出。
当时,全球风险投资和资本大量涌入人工智能领域,催生出接连不断的十亿乃至百亿级独角兽企业,它们在短时间内便实现了数千万或上亿的年营收规模,这种景象此前从未出现过。这被视为AI时代的特殊机遇,不少投资者指出,只要产品面世便有用户接纳,就能带来收益。
我们谈论到Lovable——这家发展迅猛的欧洲人工智能独角兽,仅用八个月就实现了每年一亿美元的经常性收入,这一速度甚至快过美国的Cursor独角兽,后者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独角兽的,在这次WebSummit上,Lovable的联合创始人Anton Osika也将作为演讲嘉宾之一。帕迪·科斯格雷夫谈到,即便是Lovable这样的欧洲企业,其内部氛围是“997”——他们觉得,要想超越中国人,就必须比中国人更加努力。
帕迪·科斯格雷夫表示,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文化影响力,并非人工智能。他兴致勃勃地举例,提到在深圳目睹的一家特色店铺,该店专门制作中国的传统香料。
这次到访中国,帕迪·科斯格雷夫另有要事在身,需要购买Labubu产品,他最近与Scale AI的创始人Alexandr Wang进行过交流,该数据标注公司刚刚获得了美国科技巨头Meta高达143亿美元的资金注入,Alexandr Wang本人也加入了Meta的行列帕迪·科斯格雷夫在和Wang交谈时表示,双方除了谈论各自日常,Alex还透露了自己收藏了多少个Labubu的盲盒。帕迪·科斯格雷夫补充说,自己不能不带任何东西回爱尔兰。
去中国走一趟吧,那里正在各个技术领域不断拓展新的高度。这是帕迪·科斯格雷夫在浦江论坛讲话时提到的内容。
DeepSeek刚问世时,旧金山地区几乎所有公司都在使用它
虎嗅询问,生成式人工智能至今,哪些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让你记忆犹新,又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如此印象深刻,请分享你的看法。
帕迪·科斯格雷夫:DeepSeek,这个完全不要钱,你知道吗?他们居然真的靠它搞出了模型,而且费用只是西方模型的零头。性能比它们好,价格比它们便宜,简直太厉害了。没错,它在各方面都动摇了西方的基础。哇,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Deep Seek刚问世时,整个2月和3月期间,几乎旧金山的所有公司都在使用它,连那些与AI无关的企业,也都在部署Deep Seek的定制化版本。既然有了这个选择,还有谁愿意付费使用OpenAI或Anthropic的服务呢?这或许就是硅谷最大的一桩隐秘内情。
他们秘密在本地上架了一套,天衣无缝——服务人员、管理系统,全部依托 DeepSeek 运行。既然开销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又何必再向其他公司支付费用?
虎嗅问你是否每天使用它,我猜想你更频繁地运用GPT或Claude。
帕迪·科斯格雷夫表示,在他看来DeepSeek更为出色,他更倾向于使用DeepSeek,因为至少能从中获得某种程度上的“隐蔽性保障”。
虎嗅表示,之前曾经提及,中国在这场人工智能竞赛中将会取得领先,这一看法的依据是什么?
帕迪·科斯格雷夫谈到,他回想起来,在2017年前后,彭博进行过一次访谈,询问他预计哪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能够最后脱颖而出——当时几乎没有哪一家公司显得特别突出,他回应称,人工智能行业中的成功者,要看一些尚未在中国出现的公司,对方听后表示难以置信。
缘由十分清晰。浏览顶尖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学术刊物的参考文献列表,可知我国学者备受推崇的论著数量持续大幅攀升,而西方国家的相关成果却几乎停滞不前。科研活动是产业发展的先导;当前哪方贡献了更多一流研究,未来便更有机会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商业领域的创新实践。
现在看来,剧情正依照页数推进。即便在美国,新出现的 AI 企业内部也带有明显的东方色彩——翻阅硅谷企业的人员名单,最为普遍的那一项国别,登记的不是 American,而是中国。
AI 终将像电一样,以近乎零的边际成本普及。
最赚钱的是那些运营“电力网”的企业——涉及计算能力、传输容量、数据保管以及能源供给。即便模型再出色,其核心功能也仅相当于一个数学过滤器:将信息输入其中,凭借概率法则得出预测结果。数学方法不分地域,也无法申请专利保护;只要计算资源充足,任何组织都能够复制、优化、提炼,将竞争对手的“核心算法”转变为自身的“基础技术”。因此随着发展,竞争将更多地体现在资源规模、成本控制和用户体验上,技术门槛会持续下降。
全球范围内时常有企业获取部分收益,然而长远来看,具备数百亿乃至数千亿规模价值的公司数量相当有限。美国和欧洲在人工智能产业显现出显著虚高现象,预计接下来数年,众多财富精英会承受巨大损失。
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半导体及相关部件出口限制,甚至迫使全球厂商配合,导致众多中国新创企业在与西方人工智能企业对抗时,仿佛缺少一只手。即便如此,诸如DeepSeek这样的中国公司依然突破硬件获取的障碍,实现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这样的案例并非孤例。
一旦中国新兴公司能够全面获取国际一流的半导体、首屈一指的图形处理器,形势将更加激动人心;而这一时刻即将来临,由于这些芯片将来也会在中国境内生产。

“想跑赢中国人就得比中国人更拼”
虎嗅问,你见识过众多创业公司,包括欧洲的、美国的和中国的初创企业,它们彼此之间有何差异?在AI领域这场浪潮中,欧洲也涌现出相当出色的公司,例如Lovable。
帕迪·科斯格雷夫谈到Lovable的企业文化特点,称其为“997”。这种文化认为,要超越中国同行就必须更加努力工作。因此公司实行997工作制,他猜测中国团队随后会采用“998”模式,额外增加一天工作时间。
如果论及不同,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所有人都在最尖端奋力前进。不过近几个月以来,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逐渐认识到 LLM 和 Transformer 的局限。学术界中,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发出过警示,例如那位将人工智能企业出售给优步的纽约大学学者,四年前在Web Summit论坛上,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曾明确指出,“不断增加计算能力、图形处理器和数据”所带来的额外效益终将逐步降低,当时多数人并未重视,甚至认为他在进行负面预测,然而上周《纽约时报》上他直接发表文章表明,“我早已预见到这一结果”。
中国或许也会走过相似的发展阶段:起初发展迅猛,人们每半年就期待新版本问世,感觉离通用人工智能更近了,但后来发现升级效果仅属一般,并非重大突破。因此,虽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或许最终会领先,但我并不觉得我们离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有什么实质进展——目前多数只是有趣的应用,与通用人工智能目标相比,仍停滞不前。
虎嗅问:自 2009 年发起 Web Summit 以来,你见证了移动互联的技术浪潮,也目睹了AlphaGo引发的变革,过去的科技浪潮与当前的AI浪潮之间,有哪些差异?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帕迪·科斯格雷夫:首要的是速度和资金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西方初创企业获得的估值、融资数额、年度经常性收入都刷新了历史记录。1亿元、2亿元、8亿元——由于进展迅猛,其能力显得极为惊人。
不过最近,OpenAI 发布的信息表明:公司层面的每日活跃用户好像在减少,而个人使用GPT的频率却在不断提高。起初企业纷纷追求“拥抱AI”,现在逐渐意识到这类工具的局限性。因此,尽管我认为个人付费订阅会持续增加,但公司投资的前景却值得商榷。机构内部部署的大型模型方案,实际效果远非预期般理想。
人类向来对自身局限性和最终结局充满好奇,科幻作品中机器战胜并替代人类的毁灭性情节屡见不鲜。自行车速度超过人类,拖拉机早已取代农田劳力——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引发人们惊呼“机器将主宰世界”,这种担忧几乎演变成一种普遍的恐慌。只是这次,这股浪潮的规模确实要大得多。
“(中国AI公司)先走出去,气氛远比你想象的宽松“
虎嗅:中国很多AI公司都在出海,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帕迪·科斯格雷夫提醒我们,美国新兴企业前往欧洲时会感到陌生,仿佛到了外星球;而欧洲企业进入美国时,同样觉得环境差异巨大。即便在欧盟内部,各国之间也并非统一市场:文化习俗、法律体系、监管规定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区别,瑞士这样的非欧盟成员国更是增添了复杂因素。因此,对于中国企业,他给出的忠告是:不妨先尝试出海,其他问题之后再逐步解决。
DeepSeek、华为、比亚迪给西方年轻人带来的震动是毋庸置疑的。民意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群体中,将“中国”视为未来的趋势日益明显。
年轻人原本就是新兴科技的早期采用者,现在又正值对中国免签的时期,纷纷前往成都、深圳等地,晚上拿出手机拍照后,社交平台上充斥着疑问“这是哪个城市?”——“是成都。”——“成都位于何处?”这种即时的互动效果,远胜过任何宣传材料。大疆就是典型,西方市场缺乏能与之匹敌的无人机,消费者普遍认为“除了大疆没有其他选择”。
二十岁的大学生观看的是TikTok平台上的重庆夜景画面,他们脑海中的中国形象完全是另一种形态。
因此,我国相关机构仅专注于拓展海外市场,整体氛围远超预想中的开放。三月份在旧金山举办活动期间,众多明星创业公司的领导者几乎都配备了本地化的DeepSeek系统——通过部署开源模型,客服及后台功能已全部实现。该方案既便利又无需付费,何必还要向OpenAI支付使用费用呢?
虎嗅表示,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潮时期,涌现出大量年轻的创业者,其中不乏中途退学创办企业的案例,对此他们持何种观点呢?
帕迪·科斯格雷夫坦言,他不认同所谓“年少有为”的流行说法,相关数据表明,初次创业最有可能成功的年龄段是42岁,这个年龄恰好也是他目前的岁数。尽管媒体热衷于报道19岁大学中途辍学、迅速实现公司价值暴涨的传奇故事,并且受众对此类情节颇为着迷,但整体数据不会误导人。更可靠的策略是:先进入一家优秀的企业,深入理解所在领域,提升自身成为值得信赖的负责人,随后独立创业——这样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很多。
虎嗅:你见过一些年轻创业者吗?和他们聊过吗?
帕迪·科斯格雷夫表示,Alexandr Wang是Scale AI的建立者,他是个鲜明的例子,早先曾是白手创建企业而获得亿万财富的最年轻人士之一。
虎嗅:你们聊了什么话题?
帕迪·科斯格雷夫谈到,他询问了对方收藏了多少个Labubu的盲盒,数量之多令人惊讶。
虎嗅:今年webSummit你最想邀请谁?
帕迪·科斯格雷夫是Labubu的建立者。中国的后续重要发展将集中于软实力方面,包括影视作品、动画创作、玩具制造以及文化传播。观察日本就能发现,该国起初主要输出技术,到了七十年代则着力提升设计水平,并将设计打造为国家的象征性标志。
我家那个八岁的孩子一听说我要去中国,首先就说:“真棒,别忘了给我带个Labubu回来。”——他才仅仅八岁而已!我接着问他,中国还有其他什么牌子是他喜欢的?他琢磨了挺久,最后回答:“没有了,就想要Labubu。”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向海外的转折点已经来临了。
我最近在深圳偶然拍下一家店铺,那里专门制作香水,那个包装盒的精美程度让我惊叹不已——它的工艺水准和审美价值,放眼全世界都属于顶尖行列,他们是如何实现这种境界的?文化虽然属于无形资产,但一旦发展成流行趋势,其影响力会超过有形资源。Labubu并非首创者,将来也不会是终结者,紧接着将涌现大量中国品牌,年轻人会感叹“中国真是魅力无限”,主动选择前往体验——当年日本正是这样吸引粉丝的。
文章标题:DeepSeek成了硅谷最大的“不能说的秘密”
这篇文章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涵盖了多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深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