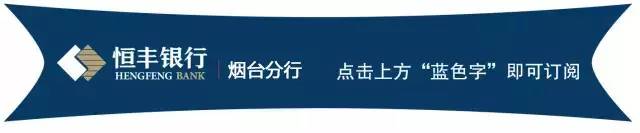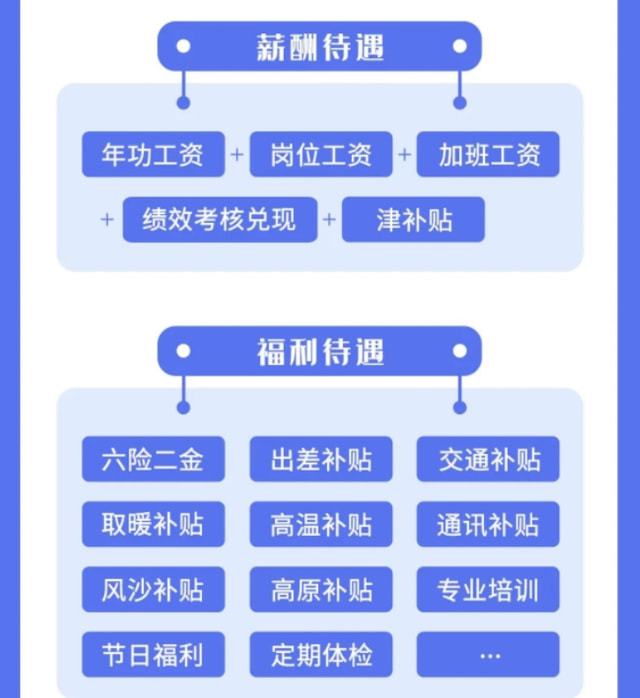1. 一个荒谬的错误预测
1969年,有媒体请多位经济学家对50年内世界各国的GDP进行预测,排名前10位的是:日本、美国、西德、苏联、巴西、菲律宾、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法国。
2019年实际排名前10位的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10~20个分别是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西班牙、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荷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瑞士)。
这个预测并不能预测中国的崛起是可以理解的,毕竟1969年的中国还在十年的动荡中挣扎,不预测苏联解体和德国合并是正常的,但其最大的问题是,它明显高估了亚洲国家的增长潜力,低估了经济转型后欧洲经济体的韧性。
这个预测在某些地方大错特错,但在我看来“非常合理”,为什么?
二、误入异次元的日本和老板级玩家中国
1969年,日本和韩国的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2.48%和14.56%,当时亚洲有许多国家,经济增长刚刚上升,人口众多,工业基础良好,如印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这让世界对亚洲经济统治的未来深信不疑, 而在前10名的预测中,亚洲国家占了5个席位,与实际情况差异最大的是日本和菲律宾,预测值分别是实际值的4.2倍和7.8倍。
GDP是增量的,那么GDP增长就是增量的增量,相当于加速。如果一辆车现在在20码处,很容易连续加速,但是如果车现在在200码处,以后速度肯定会下降,如果前几百公里没有加油站,迟早会变成0。
这种物理现象很容易理解,但一个国家的快速增长往往持续几十年,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一半,以至于许多人忘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不仅不能无限期地加速,而且很难保持增长。
很多人喜欢把现在的中国和30多年前的日本进行比较,以为中国也会经历“失去的30年”,但这种比较忘记了,泡沫经济巅峰时期的日本,GDP是美国的70%,到1995年人均GDP是美国的1.54倍, 可以说,日本是当时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前十名中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因此日本可能是第一个挑战人口大国人均GDP极限的国家。
在我的文章《阅读,重新思考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之谜》中,我通过解读这部小说的社会背景,分析了日本为何会经历三十年的停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日本文化特有的现象,更多的是由于政府在应对日本遇到的困难时缺乏远见和经验,缺乏先例。
从那时起,日本GDP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就像一个运动员跑得太快,跑到时间停止的另一个维度,努力寻找30年,尝试各种方式回来,也为后来许多国家遇到类似困难提供了经验
事实上,日本这个经济庞大、停滞不前几十年的大国,现在能否走出长期通货紧缩,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全球配置中,我最困惑的是日元和日本股市。
此外,这份名单上五个亚洲国家的集体疲软与“中国经济奇迹”有关。
亚洲的崛起反映了自由贸易全球化下制造业产业链的转移,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后者的发展路径几乎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赚取外汇利润,然后逐步建立重工业体系, 最终实现产业升级。
在预测中,日本之所以战胜朝鲜,是因为日本先崛起,而四只虎后来又遭受了日本的产业转移,而在90年代,还有所谓的“四只虎”,即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希望继续承接“四只虎”的产业转移。
只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这种转移的进程,危机过后,中国加入了WTO,整个博弈中突然出现了一个老板级的参与者,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市场规模和制度优势,直接承担了全部转移的产能。这个游戏在战后玩了五十年,在中国地图上“卡”了30年。而在2019年,正是这种大停滞的顶峰,直到特朗普引发的去全球化和拜登领导的再全球化,产能才继续向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转移。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抓住这种“全球化的珍贵”,在预测名单上,有一个亚洲国家比日本更失败。那就是菲律宾,如果说日本式的衰退难以避免,那么菲律宾式的失败就真的是“亚洲的耻辱”了。
3.被历史抛弃的菲律宾和东南亚
今天的人们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这个预测将菲律宾排在世界第六大GDP中如此之高。
事实上,菲律宾在1969年是亚洲第二强国,其人均GDP仅次于日本,因为菲律宾在长期殖民时期被美国建立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亚洲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首都马尼拉,许多东亚人习惯于移居菲律宾寻找就业机会。
由于政治腐败和不稳定,菲律宾经济成为一个令人震惊的国家,在大独裁者马科斯的 20 年统治下,其中 10 年是军事控制,他的妻子伊梅尔达被非正式指定为总统职位继承人,他的儿子、侄子、兄弟和亲信都担任要职。马科斯有“10%先生”的绰号,在菲律宾的任何商业、投资、生意都必须给马家族回扣,而在马科斯下台之前,他的家族超过100亿美元,相当于菲律宾外债的40%,是年度预算的三倍多。
在60~80年代的亚洲国家,有许多专制政府和独裁政府,如朴正熙、李光耀、萧蒋等,但至少经济表现不错,大部分起飞都是在这个时候,但历史选择了一个既无能又腐败又独裁的马科斯,执政20年。
直到1982年,菲律宾的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左右,不仅低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低于同样位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1983年,当独裁统治结束时,反对派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在马尼拉机场被暗杀,引发了该国汹涌澎湃的民众抗议运动,1986年,马科斯以欺诈手段再次当选,引发了数百万次抗议、示威和集会。国防部长哗变,马科斯逃往美国。

1983~1987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滑,后台政局仍不稳定,到2022年,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第39位,人均GDP位居世界第125位。
GDP预测中最难的是政治动荡,一个国家政治稳定与否往往是一门形而上学。在亚洲,有日本这样的“超级马厩”,日本在战后长期保持稳定,即使在收入增长30年后也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有叙利亚、缅甸等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例如,在经历了极端的“十年动荡”之后,中国奇迹般地稳定了近50年。
当然,菲律宾的失败不仅仅是马科斯的独裁统治,韩国在整个80年代都处于类似的“人民反对独裁”的社会环境中,但并没有影响到韩国10%左右的GDP增长率。
它要求劳动者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吃苦耐劳的意志和精益求精的精神,而东亚文化显然比东南亚文化更适合制造业。华人比例最高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也是人均GDP最高的三个东南亚国家。
相比之下,印度尼西亚是预测榜上排名前10位的国家,1968年的GDP增长率为10.9%,是迄今为止最高的一年,线性外推的效果也很明显。

当然,印尼的人口也是预测的原因之一,人口增长是最容易估计GDP增长的因素,总体经济水平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慢,很多国家的GDP增长拐点与人口增长的拐点一致,只要人口基数大, 生长速度高,盲测有50%的正确率。
在预测榜上排名第六的巴西也出于类似的原因,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人口。
四、旧资本主义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力
这些预测不仅高估了亚洲国家的增长潜力,也高估了欧洲经济转型后的弹性,这也是线性外推的结果。
以英国为例,英国虽然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但就GDP而言,英国从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这一地位在1890年之前是中国,此后一直是美国。除去统计不一致的苏联,英国在1960~1962年仅短暂位居世界第二,1963年后被法国、日本超越,1969年排名第四。根据这一预测,按照这一趋势,英国不太可能在50年内保持在前10名。
事实上,英国虽然在70年代经历了两次危机,分别是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其全球GDP排名一直稳定在4~6之间,而其他欧洲国家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则上下稳定。
为什么当时被认为是“不好”(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这么认为)的欧洲“大国”几十年来一直位居前十,尽管它们的GDP增长很低但很稳定?
如果我们看一下其形成的原因,增长经济学认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是“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和创业人才”,所以一些经济学家用以下公式来表达:
GDP = 资本投入 * 劳动投入 * 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这样写:
Y = K^α * L^β * A
通过这个公式可以看出,短期内最容易改变的是K(资本投资),它可以超发货币并引入外资,这与M2或社会金融的增长率相对应,是过去20年来对中国GDP的最大贡献。
但是,K(资本投入)的产出不是无限的,并且受到α(资本产出弹性)的限制,可以看出,2015年之后,M2和社会金融仍在大幅上升,但GDP的增长率却在下降,说明这个α已经开始从之前的极限水平下降, 中国的融资和外资驱动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高层决定不做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决定,原因是没有资本弹性,再多的刺激也不会奏效。
另一个重要项目是L(劳动力)和β(劳动产出弹性),前者是数量,后者是工作时间、效率等,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L在2010年之前是主要的增长因素,然后主要依靠β,但随着劳动法越来越规范,年轻人“躺平”, 它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当这些资源的潜力耗尽时,唯一能维持增长的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GDP中无法用人口和资本来解释的东西,我前面提到的自然资源禀赋就是其中之一,但自然资源禀赋是有保障的项目,更重要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科技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系统成本、 以及其他相对难以量化的因素,这些因素难以在短时间内盈利,需要多年的积累。
以高等教育水平为例,从表面上看,我国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在60%以上,但这是近十年快速发展的结果,如果从整个人口来看,我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只有15%,而英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上。
因此,欧洲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似乎已经完全城市化,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少,工人贪婪地追求舒适,制造业的损失,人口老龄化,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但是,真正使它们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保持竞争力的是过去一个世纪积累的“全要素生产率”。
例如,在英国,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期间,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数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在GDP中的份额从1979年的10%下降到1997年的不到1%。摆脱这些负担后,以金融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迅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从1950年的46.3%上升到2015年国民经济的79%左右。从1992~2007年的15年间,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是最快的,在人均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在七国集团中名列前茅。
中国的GDP能赶上美国吗?
高盛(Goldman Sachs)预测,到2075年,GDP排名前10位的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埃及、巴西、德国和英国。
从这份榜单和本文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个预测的逻辑是“人口+当前经济规模和增速的线性外推”,其中悬念的预测是中国和印度都将超过美国。
这个预测可靠吗?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1969~2019年这50年的变化:
1969年,GDP排名前11位的是美国、苏联、日本、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加拿大、印度和巴西(不同的统计来源略有不同);
2019年GDP排名前11位的国家是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和俄罗斯。
事实上,这两份榜单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和5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排名也是一样的。这50年真正的变化只有两个半:中国的崛起和苏联的衰落,而“一半”就是印度的成长。
即使是这“两个半”也只是历史的“均值回归”,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从公元0年到1000年,GDP世界第一的位置被中国和印度交替占据,从公元1000年到1890年,中国一直位居第一;而苏联只是一个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国家,目前的排名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国力。
因此,国家的国运不能勉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国家命运的起伏与普通人的命运相去甚远。在几千年来全球经济强国的历史中,始终是“富,民苦,民死,民苦”。
无论50年后是GDP第一还是第二,只有自己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