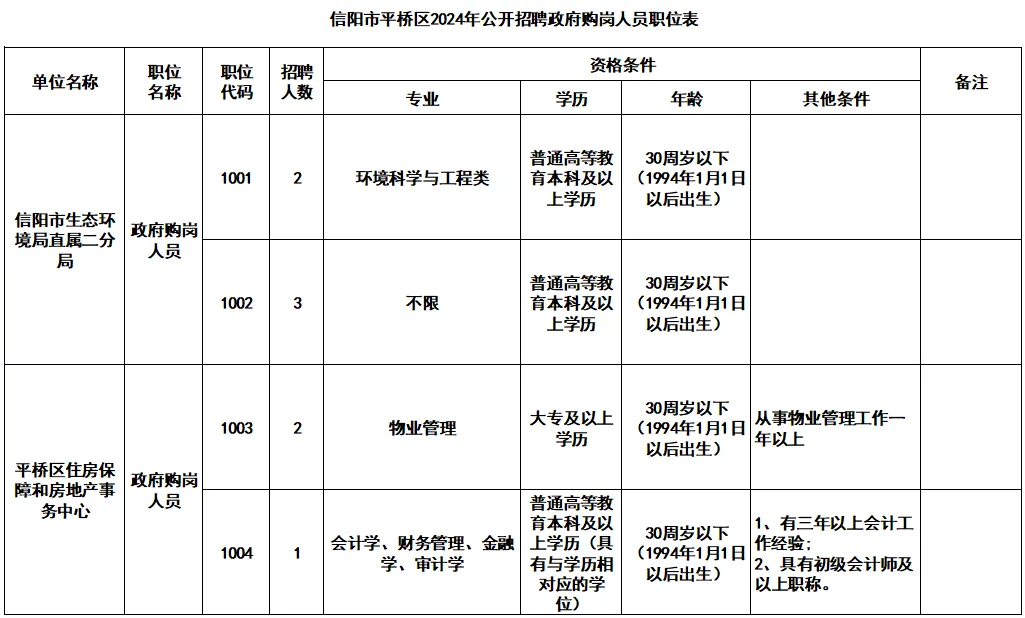一
1958年1月6日晚,上海大场机场。一架专机正在等待某人。
上海统战部干部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人。起初我只知道他可能住在虹口。当我找到他的工作单位时,晚上没有人值班,只好向人力资源部门查询,得知他住在溧阳路瑞康里92号。
夜深人静时,统战部工作人员用手电筒在深巷里挨家挨户地读门牌号,终于找到了他——新民晚报社长赵超构。
已经上床睡觉的赵超构从床上醒来,赶紧洗漱换衣服。一行人赶往位于南京西路的统战部办公室。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和谭家桢已经在这里等候。当他们开车到机场,登上专机时,才发现这是毛泽东主席的专机,要带他们去杭州。毛泽东想和他们三人谈谈。飞往杭州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从机场到达西湖刘庄时已经快十二点了。
上述颇为生动的描述,引自张琳兰所著的《赵超构传》。
1978年9月11日,赵超构写文章回忆毛泽东的几次接见。写作就简单多了:
“1958年初,我记得是1月6日,主席在杭州再次会见我。我是晚上接到通知的,飞到杭州时已经是深夜了。周谷城、谭家桢同志也来了。”去的时候是西湖边的水木名色花园,那天晚上,主席没有休息,就接待了我,直到凌晨三四点。”

赵超构(左)与张琳兰合影。摄于1986年10月。作者提供。
二
1946年5月1日,《新民日报》上海版创刊,赵超构任主编; 7月1日,《新民晚报》报头首次亮相。从此,上海街头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夜报、夜报、新民夜报》的卖报声。
同年9月,赵超构迁入瑞康里。
这套房子是报社经理邓继兴给他租的。当时,赵超构因抗战与妻儿离散八年,一家人终于团聚。这段停留持续了42年。因此,《虹口区志》和《虹口文化志》都有“赵超构”的条目。
据《上海地名》记载,瑞康里位于虹口区中东部,溧阳路、海伦路、哈尔滨路、嘉兴东路、新嘉路之间。建于1931年,这里巷弄多,四通八达,共有建筑183间,建筑面积约12600平方米,居民约3000人。难怪市委统战部的人深夜苦苦寻找赵某。
溧阳路上有48栋花园洋房,是虹口区一条比较洋气的道路。文化名人鲁大南就住在其中一所房子里。但瑞康里是一条石库门胡同,比较普通。
《赵超构传》说,这是一栋房子,一层有亭子,有地下室,赵超构的卧室和书房只占前层的一半,大约十平方米。有一次,陈望道来拜访,上楼一看,大吃一惊:“邱关太大了!你们的楼梯又窄又陡,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赵超构的司机小崔也在赵超构去世后告诉新民晚报记者钱勤发:“老总统的家在溧阳路瑞康里,是一栋石库门老房子,楼梯又黑又陡,再次令人心寒。当我到达前楼,更让我惊讶的是,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一张三尺半的铁床,一张书桌,一张旧藤椅,三个矮书柜,这。都是老总统的家当。”
不久前,笔者在赵超构家乡文成见到了85岁的退休教师徐世槐。 1970年,他来到瑞康里,对赵超构家庭的淳朴印象深刻。他还笑着告诉我:“赵超总是用他家乡的方言跟我说话。”
三
1958年的那个夜晚,西子湖畔,博学的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对于赵超构,毛泽东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分清九指和一指的关系;第二,要经常跑到下面去,多与工农兵接触,接受教育。毛泽东和三人一直聊到凌晨。临走时,他高兴地说,这样的聚会也算是一个“西湖故事”。
第二天,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设宴招待周、谭、赵。席间,毛泽东请赵超构回家乡探望。
5月、6月,赵超构回到家乡温州,历时两个月,各地走访采访。返回上海后,他于7月20日至8月2日写下了近三万字的长文通讯《我来自家乡》,在《新民晚报》连载。市委领导肯定并发来消息说:“主席已经看到你的文章了。”当年,赵超构辞去主编职务,成为唯一的社长。主编由舒仁秋接替。
《我从家乡来》是赵超构自1944年写下《延安一个月》以来的第一部长篇通讯作品。
1944年也是赵超构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一年。

第一版《延安一月》。上海图书馆藏。
赵超构作为西北中外记者代表团成员访问延安。记者团于1944年5月17日出发,在陕西、山西各地考察了半个多月后,于6月9日抵达延安。6月12日,赵超构首次会见毛泽东。
这一天,毛泽东设宴招待中外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一个月》中记录了他对中共领导人的第一印象:
”毛先生得意地走进来,身材修长,但并不起眼,一身毛料制服明显有些破旧,领子纽扣一如往常地解开,衬衫裸露在外,就像他的照片一样,眼睛盯着介绍。人们似乎都在尽力听对方说话,他说话的时候仍然带着湖南口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比较紧张,但他看上去很疲惫,整个过程中他几乎没有笑。不过说话的态度却很优雅,他的音节清晰,词汇安排得体、有序。”
吃完晚饭,又到了看戏的时间。工作人员让大家从第二排坐起来。耳朵聋的赵超构没有听到,直接坐在了第一排的中央。不久,他发现毛泽东坐在他的右边。看剧时,毛泽东“不断戒茶戒烟,像朋友一样和我们说话”。这是赵超构第一次与毛泽东进行一对一的深入交谈。
也正是在1944年的西北之行中,赵超构结识了22岁的张琳兰,两人后来成为了终生的同事和朋友。 1944年5月20日,西安记协为来访的中外记者团举行欢迎招待会。张琳兰当时在西安一家名为《华北报》的报社工作。他的老板赵自强命令他代表报社出席,而他恰好与赵超构坐在同桌。张琳兰写道:“赵超构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他身材瘦小,中等个子,肤色不太健康,只有戴着金丝眼镜的眼睛还有些精神。”
四
张琳兰后来随赵超构从重庆来到上海,创办了《新民日报》上海版。 1982年《新民晚报》创刊时,领导班子里只有赵、张是《重庆新民报》的元老。
事实上,赵超构早就有机会搬出瑞康里,住进更好的花园洋房了。那是1956年。
张琳兰在《赵超构传》中说:“说到住房,我一直忐忑不安。”当时,市里把建国西路的一套房子划给了新民晚报。第一选择当然是赵超构。 “他连看都没看,就把它给了我,并告诉我‘在事情发生变化之前赶紧搬进来’。”
对于赵超构坚持住在瑞康里、不愿意搬家,最常见的解读是,他想了解石库门巷的民情民意,这对办新民晚报有利。然而继承了低调朴素家风的赵超构的长子赵东侃却另有解释。
他告诉邻居金洪元:“我父亲生前不同意这个说法,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父亲听说建国西路房子的租金占了他收入的一半以上,所以他放弃了去看看的想法,因为那是住宅的月租,绝对不是我们家能负担得起的。”
五
1982年元旦,《新民晚报》创刊第一天,赵超构就向老朋友张琳兰发脾气。
张琳兰主笔的《飞进寻常百姓家:新民日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中写道:“复牌讲话是报纸创刊前一天赵超构向编辑部发表的讲话。该报正式发稿的第二天上午,副总经理张林兰在看大样时,觉得原来文章里说的“为老百姓”,省心又享受。 “老百姓”两个字感觉重复,于是把其中一个“老百姓”字改成了“国”,成了“与老百姓共忧,共乐”。到了报社,他看了报纸,非常生气,批评了他的老下属和小弟。”
张琳兰在《赵超构传》和他的自传《拉侯过春节前》中对此事有更形象的描述:“他急忙站起来,大怒,把报纸扔在桌上。” “他发脾气后,默默地看了复刊前一天的报纸,觉得没意思,就沮丧地下楼了。”
张琳兰道:“我认识他四十五十年了,老兄弟们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不好的话。”此后多年,张琳兰一直在反思此事,“我深感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不明白他的用意和言辞的意义”。 “他处处与老百姓即‘老百姓’站在一起,为老百姓说话;老百姓也忧,老百姓也高兴,这就是他的民粹主义思想的体现。”
六
今年9月是赵超构奉献一生的《新民晚报》创刊95周年,11月是赵超构的代表作《延安一月》创刊80周年。新民晚报与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联合举办“林放不老——赵超构手迹暨《延安一月》80周年纪念展”。展品中有1944年出版的《延安一月》第一版,以及赵超构的手迹。 1991年《韦晚谈》手稿,以及台历。
“上午政协代表团参拜,下午我去报社吃了晚饭。” 1992年元旦,赵超构将这件事记录在他的台历上。

很简单的记录,发人深省。赵超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天,他参加政协集体参观,没有在政协餐厅用餐。相反,他“去了报社吃了一顿饭”。本月9日、10日、14日,他三次来到报社。 24日上午,他“与于刚一起去拜访巴老,并向他赠送了一本厚厚的《真理之书》。于刚,新民晚报原副总编辑沈玉刚,和巴金是赵超构生前拜访的最后一位朋友。四天后,28日,赵超构因病住院。1992年2月12日,赵超构去世。

32年后,新民晚报的老读者仍然对赵超构充满感情。 《林放千古》展览两个月期间,每天都有老读者前来参观,缅怀“与民同忧、与民同乐”的赵超构。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公民。”
这是《赵超构传》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来看看瑞康里老邻居金洪元的回忆:
“每年夏天的傍晚,赵大爷都喜欢坐在门口的小竹椅上,方凳上放着茶壶,手里拿着一把蒲扇轻轻晃动着纳凉。经常有邻居和他聊天,说关于家庭的缺点。”巷子口胡一达粮油店里,经常看到他拎着几瓶绍兴酒。 ”
赵超构(1910-1992)
笔名林芳,著名记者、专栏作家。长期主持《新民晚报》工作,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着有《延安一月》、《维万谈》、《林放选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