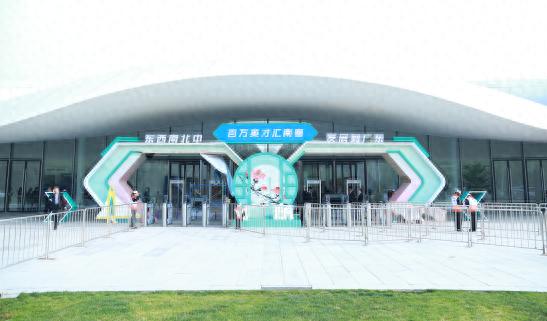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诵习一个字,要认识它的形、音、义。口中诵读它的音,耳朵听到它的音,眼睛观察它的形,内心理解它的义,这三种认识同时运用,一个字的功效才算完备。接着,他举例说:在文章中,写山就用“崚嶒嵯峨”,描绘水就用“汪洋澎湃”,形容草木茂盛就用“蔽芾葱茏”,仿佛遇到了茂盛的树木,提到“鳟鲂鳗鲤”,就如同看到了很多鱼。究其原因,汉字具有三美。其一,意美能够感人心;其二,音美能够感人耳;其三,形美能够感人目。
在意美境界,观“仁”字能看到礼乐教化,睹“和”字能领悟中庸大道,每个字符都是先民智慧凝结的文化符号。汉字书写的文明有此三美融为一体,犹如一幅幅流动的画卷,历经千年时光,依然能够熠熠生辉。
汉字之美 美在形体
汉字的形体美首先是源于它的“图画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书画同源”这种说法,这是因为汉字在开始造字的时候就遵循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说文解字·叙》里提到:“仓颉刚开始创造文字的时候,大概是依照事物的类别来描绘它们的形状,所以把这些叫做文;在那之后,形声相互增益,就叫做字。”
汉字的构形是对词义进行记录的象形化过程。以“泉”字为例,从甲骨文(见图 1)来看,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在山石之间有一眼清泉正在汩汩流动,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汉字的象形图画具有一种通过形状来体现意义的美感。《说文解字》中提到,“泉,就是水的源头。它的字形像水流出形成川的样子。”这是先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用笔墨表达出来的,绝不是随意创作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样的意境之美似乎从一个“泉”字就能领悟到。“泉流岩窦本来就很清,更何况还有松风逼近座位而产生”,那种清幽之感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图1
书法艺术将汉字的形体图画美发挥到极致。汉字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线条章法和形体结构,这些结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且布局完满。每一幅书法作品都像一幅精美的图画,与作者的内在精神融为一体。例如,“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其飘逸潇洒的风骨,充分展现了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
汉字在不断发展演变过程中,其形体从初创时的“图画美”逐步形成了由笔画向右、向下运动构成的二维方块平面文字,从而展现出独特的“对称美”。现代汉字的合体字占总字数的 96%,经《汉字信息字典》统计,在 7785 个汉字里,左右结构的字有 5055 个,占比 64.93%;上下结构的字有 1643 个,占比 21.11%。这种汉字具有对应结构,它能带来匀称的视觉美感,也能带来协调的视觉美感,体现了中华文化中对称和谐的审美观念。
汉字的形体美体现在其有广阔的再造空间。它既包含工艺美术美,又涵盖工程技术美。汉字笔形多样且排版灵活,使现代汉字成为人类视觉认知、工艺技术与悠久历史相结合的产物。比如,中国邮政的鸿雁徽标,其设计灵感是源于西周青铜器何尊内底铭文中的“中”字,这是最早关于“中国”二字的文字记载。徽标巧妙地对“中”字进行了再加工,它由横与直的平行线构成,形状像翅膀,这象征着秩序与四通八达。字体略微向右倾斜,展现出方向和速度感,让人能联想到中国古代的“鸿雁传书”。这种对取自重器铭文的字形进行再加工的方式,既具有艺术美感,又能传递出深邃的文化底蕴。
汉字之美 美在音韵
汉字的音韵之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为声调的韵律性;其二是同音字的谐音性;其三是叠音词的回声性;其四是联绵词的和谐性。
声调是汉语重要的韵律特征之一。古人最初借用音乐的五声音阶,将声调称为“宫商角徵羽”,这反映了声调与音乐之间存在共性。然而,音阶的音高变化是跳动的,声调的音高变化却是滑动的。并且,声调还涉及发声态和时长等要素。南朝学者周颙在《四声切韵》里首次给出“平上去入”的声调名称;唐朝的《元和韵谱》有这样的描述:平声听起来哀伤且安稳;上声听起来严厉且高扬;去声听起来清越且悠远;入声听起来直接且急促;清朝江永在《音学辨微》中也提到,平声通常而空灵,就像敲击钟鼓;上去入则短促而实在,如同敲击木石。古贤们用这些生动的比喻,为我们直观地描绘了声调的音韵美。平声悠扬安详,上声高亢激昂,去声清脆回荡,入声短促有力。古代的四声说、平仄说、舒促说等,都是从语音的听感角度对声调进行分类的。平仄的运用成功地融入到了韵文的格律之中,造就了汉语诗词独特的音韵之美。
汉字有 1200 多个音节,音节是有限的,而字义却很丰富,这就导致了大量同音字的出现。同音字通过一些手法,比如谐音双关、押韵和谐、叠音重复、谐音隐喻等。这些手法不仅让语言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得到增强,还使表达变得更加生动、含蓄且富有艺术性。例如,古诗《子夜歌》里有这样的诗句:“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其中,“丝”和“思”是谐音的关系,“匹”这个字有同音多义的特点。它既指代了织布的那个过程,又巧妙地把情感给暗指了出来,让诗句的内涵变得含蓄且深刻。
人离去后,显得隐隐迢迢。仅用七个不同的字以及六组叠词,就把那人从山水隐约处离去之后,作者内心的那种不舍以及酸楚展现得极为充分。
联绵词由两个音节构成,在语音方面大多关系紧密,有的是双声,有的是叠韵。《诗经》和《楚辞》里双声或叠韵的联绵词大概占总数的 72%。两个音节让语句文章具备了更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美。《楚辞·卜居》中记载道:“是宁愿超然出众、特立独行以保持纯真呢?还是会阿谀奉承、卑躬屈膝地去侍奉妇人呢?是宁愿廉洁正直以保持自身清白呢?还是会圆滑世故、如脂如韦地去迎合他人呢?”其中“哫訾”是连绵词,“栗斯”是连绵词,“喔咿”是连绵词,“儒儿”是连绵词,“突梯”是连绵词,“滑稽”也是连绵词。这五个连绵词,有的是双声,有的是叠韵。连续使用这些连绵词,提升了文章的气势,赋予了文章抑扬顿挫的韵律感,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
汉字之美 美在意境
鲁迅先生提及的“意美”,是汉字在文章运用中所具有的独特审美体验。它以“字本身的意义”为根基,将人们的主观直觉融合其中,这些主观直觉包含与字义相关的情感、暗示以及深层次的文化信息。汉字构形最大的特点是“据意绘形”,其形体始终蕴含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这些信息是由最初造字者的主观意图所产生的,它体现出了主体的认知以及思维方面的特点。汉字从古文字向今文字进行演变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先从具象开始,接着到意象,而后再到抽象符号的创造过程。
汉字呈现为感性的象形符号时,它源于客观事物。同时,它又经过人的心灵雕琢。并且融入了华夏先民对宇宙人生的独特见解,还有在生活中的真切感受与深刻体悟。正因如此,它蕴含了丰富的生命意蕴。汉字化作抽象文化符号时,每一个汉字似乎都肩负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等内容,还承载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沉淀下来的对自然、社会、精神世界的独特态度和深邃智慧,其中包括价值取向、道德准则等。
汉字从甲骨文时代开始,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表意体系。比如表示四季的“春”“夏”“秋”“冬”这四个字。“春”的甲骨文(见图 2)如同种子刚刚开始萌芽,这象征着春季种子破土长叶的过程,展现出了蓬勃的生命之美,也寓意着“春草生长、万物萌出”。“夏”的甲骨文(见图 3),所描绘的是在烈日之下进行思考的人。其本义是中原的农人抓紧进行耕种生产的那个太阳回归的季节。对于远古时代依靠天来获取食物的中原先祖而言,在秋冬季节进行农耕难以有所作为。所以,一年一度太阳回归到北方的那个季节显得格外宝贵。金文增加了一些部件,比如(见图 4)所代表的双手,(见图 5)所代表的脚,(见图 6)所代表的卜(指观测天象),(见图 7)所代表的耒(指翻地的农具)等,这些部件进一步体现了农耕的特点。“秋”的甲骨文,如(见图 8)所示,描绘的是蟋蟀。《诗经》里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样的诗句。人们通过观察蟋蟀的生活习性,以此来暗示天气渐渐变得寒冷,从而表现出季节的转变,富有自然规律的美感。之后,字形从籀文(见图 9)演变成了篆文(见图 10)。《说文解字》解释“秌”为“禾穀孰也”,这体现了植物的生长规律。“冬”的甲骨文(见图 11),其本义是终结。《说文解字》提到“冬,四时尽也”,因为冬季是一年四季的最后一个季节,所以人们就借用“冬”来表示。篆文的(见图 12),增添了“仌”(冰),从而突出了年终下霜结冰的季候特征。古人依据四季的特征与规律,提炼出了一种养生理念,这种理念是天人合一且顺其自然的,具体表现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图2
图3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图12
汉字具有形美,这是它的视觉架构;汉字具有音美,这是它的口头表达;汉字具有意美,这是它的精神内核。这三美紧密结合,如同青铜鼎的三足一般:形美如同器具,承载着文明的重量;音美如同韵律,延续着诗礼的声音;意美如同灵魂,照亮着精神的深渊。国家领导人在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中国的汉文字极为卓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汉字凭借“形、音、意”三美,在二维平面空间内展现出了文字最大的表现力。同时,汉字还通过鼎铭建筑、典籍工艺等文物和文化遗产等三维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智慧经验。即便时代发生更迭,汉字依然以三美兼具的姿态,在数字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全球化语境下彰显出东方智慧的永恒魅力。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16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