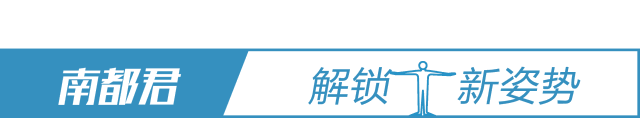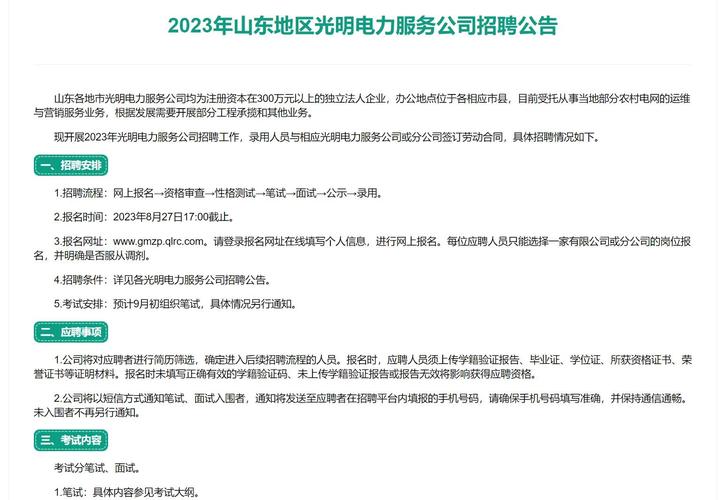绍圣四年四月十七日,即1097年5月30日,苏轼收到了一份将他贬谪至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诏令。(根据孔凡礼所著《苏轼年谱》卷三十六,中华书局出版,第1261页记载)该诏命是在四月初四发布的,经过将近两个月的旅途,他终于到达了贬居地惠州。苏轼未能与近在咫尺的弟弟苏辙告别,心中充满了困惑,于是将心中的不解与不公倾泻于给苏辙的诗篇中,诗中写道:“胡为适南海,复驾垂天雄”。他为何被贬往天涯海角?
苏轼像
开宝四年三月,太祖将岭南的儋州、崖州、振州、万安州这四个州划归琼州管辖,该地现今即为海南省;熙宁六年十一月,儋州被废除,改为昌化军,崖州改为朱崖军,万安州则更名为万安军。在宋初时期,琼州隶属于广州,而昌化军正是由原儋州演变而来。“别驾”这一职位属于“流外官”,其地位相当于胥吏。
宋代在流放地中区分了“近里”与“远恶”的州军,而在宋朝的政治文化里,被贬至岭表之地具有特殊含义,“过海”则达到了极致的境地。据记载,宋代第一个被贬至海南的人是卢多逊。在开宝六年九月十九日,卢多逊担任参知政事;九年十月二十日,太宗登基;紧接着的二十七日,卢多逊被封为宰相。到了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十七日,赵普再次成为宰相;而到了七年四月七日,卢多逊则被罢免了宰相职务。太宗与秦王廷美之间兄弟不和,赵普趁机揭露了秦王廷美与普廉交往的诸多不正当行为,借此机会将卢多逊拉下马,以报复卢多逊过去在太宗面前多次对他进行贬低。
卢多逊事件之后,到了八年四月,枢密副使弭德超对枢密使曹彬进行诬陷,意图取代其位,然而最终却导致自己被流放到琼州;乾兴元年七月,章献皇后以“春秋无将,汉法不道”为由,将丁谓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根据史料记载,卢、弭、丁三人之后,只有盛梁、齐化基二人官位不高,而且他们的任职时间都在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之前。
元祐年间,“车盖亭诗案”爆发,那年的五月丁亥日,前任宰相蔡确被“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新州位于现今的广东省新兴县,属于中国大陆地区。然而,右宰相范纯仁却坚持认为,这样的先例不能再继续下去,“这条道路已经布满了荆棘,长达七八十年,为何还要继续开辟呢?”
自真宗朝起,岭南地区未曾再遭贬谪,更别提“渡海”之举。因此,苏轼穿越过大庾岭时,不禁感慨:“今日我行岭上,此生与此地永别。”(《苏轼诗集》卷三十八,《过大庾岭》,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一版,第2056页)此外,那些曾前后被贬至岭表,且官至宰执、侍从以上级别的文臣,无不与宫廷政治有所牵连,或直接卷入皇权争夺的漩涡之中。
绍圣年间,陈衍内侍先于苏轼被“配往朱崖军”,随后,已故宰相吕公著、司马光、王珪亦因与宫廷政治紧密相连的罪名,被贬至海南。这四位官员的罪行,无一不与宫廷政治紧密相关。具体来说,他们都涉嫌“宣仁之诬”,且被认为有“逆党”之嫌。
“宣仁之诬”标志着“徐邸案”的开端。苏轼被贬至海南,或许是由于他与“徐邸官”关系过于亲密。陈衍源自“徐邸”,而苏辙则被指控“暗中勾结宦官陈衍,意图窃取宫中机密”,(见苏辙《栾城集》附录二,《苏颖滨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8月第一版,第1401页)“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于雷州”,苏轼为此作诗,诗中有“莫怪琼州与雷州相隔云海,圣上恩典仍允许我们遥相守望”之句,琼州险些成为苏辙在雷州之后的下一处安置地。(《苏轼诗集》,卷四十一,第2243页)
一
赵颢,原名仲糺,乃英宗皇帝与宣仁皇后的次子,同时也是神宗皇帝的同胞弟弟,哲宗皇帝的叔父。神宗皇帝登基后,赵颢最初被封为昌王、岐王、雍王;而哲宗皇帝继位后,赵颢先是晋升为徐王,后来又封为冀王、楚王。
绍圣四年闰二月十九日,苏轼被任命为琼州别驾;四月十八日,吕公著被特别降职为昌化军司户参军,司马光亦被特别降职为朱崖军司户参军;二十四日,王珪被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
元丰末期,《资治通鉴》得以编纂完成,司马光推荐了共同编纂的范祖禹,授予他秘书省正字的职位。范祖禹前往朝廷任职,司马光设宴为他送行。在交谈中,司马光将太皇太后比作北齐的娄太后,并提及“娄太后曾废除她的孙子少主殷,转而立她的儿子常山王演为王”。邢恕据此推断,司马光对太皇太后意图废除哲宗、另立赵颢的举动表示怀疑,并指出“雍王赵颢存有野心”,而宰相章惇更是进一步对司马光进行诬陷,指责他怂恿太皇太后效仿娄太后的做法。
王化雨学者提出,章惇与邢恕所策划的“司马光案”实际上是一场“陷害”,其意图在于向哲宗表示忠诚,以此稳固自身在政治上的地位。(出自王化雨:《北宋绍圣“逆案”新考》,《历史研究》2024年第6期)然而,相较于“宣仁之诬”或“司马光案”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探究赵颢是否有过篡位之心或行为,以及哲宗是如何判断赵颢的动机与行径的。
金中枢同样坚信,皇太后在支持哲宗登基一事上,态度坚定,毫无私心,“皇太后立孙之心愿,愈发显得真挚”。然而,宰相王珪在赵颢与哲宗之间摇摆不定,“留下了模棱两可的迹象”。因此,哲宗亲政后,便断定王珪“心怀叵测”,“在两派之间徘徊”,且其“怀奸”、“二心”的意图明显,不仅有动机,更有实际行动。
赵颢未能如愿以偿,哲宗顺利继承了皇位,将年号改为元祐,并将皇太后尊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亲自处理政务,赵颢被封为徐王,赵覠则被封为荆王。赵覠是赵颢的亲弟弟,在太子被立的过程中,赵覠给予了哲宗极大的支持,他的作用尤为突出。
元祐三年七月四日,赵覠突然患病,最终不幸去世,当时口鼻出血不止。在薨逝的前两天,殿前都指挥使燕达也去世了。金中枢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两位都是辅助立哲宗的重要人物,却如此巧合地遭遇不幸,实在令人疑窦丛生。赵覠和燕达的相继离世,令人怀疑其中必有隐情,赵颢的行为嫌疑极大。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赵颢有觊觎之心”的说法,而且他的行为嚣张狠辣,对母弟也毫不留情。国立编译馆担任主编的《宋史研究集》第二十辑,于2000年9月首次出版,内容涵盖了第189至194页。
元祐年间,哲宗皇帝沉默寡言,九年如一日地端坐朝堂,太皇太后亲自临朝处理国事,赵颢却表现得越来越跃跃欲试。赵颢王府的官员被称为“徐邸官”,于志霖和铁爱花认为,“在元祐年间,‘徐邸官’接连被任命为重要职务,这在北宋的历史上实属罕见”,“高氏、赵颢以及当时的宰执在王府属官的晋升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志霖与铁爱花在《宋史研究论丛》2017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中,探讨了赵颢的属官及其在元祐年间的政治影响。
二
除“高氏、赵颢及当时的宰执”外,苏轼兄弟扮演了重要角色。
铁文章所整理的“徐邸官”名单中涵盖了郑雍、孙觉、郑穆、陈轩、乔执中、盛侨、王汾、龚原、崔公度等人,然而龚原与崔公度二人却主动与朝廷及宫廷政治保持距离。徐邸官成员多属旧党派系,龚原既是王安石的亲外甥也是其弟子,(参见刘成国所著《荆公新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增订本,第186页)他们主张各异,或许难以达成共识。至于崔公度,由于史料不足,此处便不再详述。
在“乌台诗案”事件中,由于他们的诗作与苏轼的意境相吻合,却与朝廷的新法及当时的时政相悖,因此受到了处罚的官员包括孙觉、陈襄、盛侨和王纷等人。孙觉与盛均被称作“徐邸官”,而另一位“徐邸官”郑穆则是陈襄的妹婿。陈襄曾举荐孙觉与苏轼相识,孙觉亦曾为陈襄撰写《墓志铭》,并自称“门生”,想来苏轼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陈襄,别字述古,出自福州侯官。在熙宁四年六月,苏轼担任杭州通判;翌年秋季,陈襄接任杭州知府,成为苏轼的直接上司。到了十年之后,陈襄身兼侍讲之职,向神宗皇帝推荐了苏轼、孙觉以及胡宗愈三人,并对苏轼的评价是“具备文学才华,堪为词臣之选”,对孙觉的评价则是“学识、品行、器识俱佳,足以担任侍从之职”。
彼时,苏轼担任河中府的代理知府。在九年十月,苏轼本应从密州调任河中府,但他并未前往;转至十年二月十二日,他转任徐州知府。此外,在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陈绎落担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一职,陈襄填补了他的职位空缺;而在十年正月二十五日,陆经再次被任命为河中府知府,苏轼则被调任徐州知府。因此,陈襄推荐苏轼的时间必定是在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这段时间内。由此可知,陈襄在刚刚兼任侍讲官职后,便急切地推荐苏轼和孙觉。
元丰二年七月四日,“乌台诗案”初露端倪;到了十二月二十六日,此事终于尘埃落定,苏轼被贬至黄州;不到半年,陈襄在京城去世。苏轼被贬至黄州后,“与往日交往皆断绝”,然而陈襄的弟弟陈章却始终牵挂着他,“从远方寄来药物以激励我改正过失”。苏轼的诗文集中并未记载他们与郑穆之间的交往记录,然而,根据苏轼与陈氏兄弟间的深厚关系来看,可以推断苏轼对郑穆并不陌生。
“乌台诗案”之名常被提及,然而,关于“王纷”的记载,在流传下来的文献中却鲜有提及。而同一文献又称之为“曾祖禹偁”,在《东坡乌台诗案》一书中,以及明清时期的多种版本中,也均写作“王纷”。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王纷”实际上可能是“王汾”的误写。王汾,字彦祖,在皇祐五年考取进士甲科,司马光便尊称他为王禹偁的“后裔”。(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三,中华书局1989年9月首次出版,第50页)在宋人笔记中,普遍以“王汾”称呼,这也足以证明“王纷”实为“王汾”之名。(《宋人轶事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首版,第1344-1345页)
自熙宁二年八月起,苏轼便与王汾、胡宗愈在景德寺一同应试,两人交情颇深。到了元祐五年,苏轼在赠予王汾的诗篇中,不禁回忆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心中感慨万分。(《苏轼诗集》卷三十二,《次韵林子中、王彦祖唱酬》第1683页)
郑雍和孙觉是当时官阶最高的“徐邸官”。孙觉,字莘老,曾官至御史中丞,他与“徐邸官”中的崔公度、乔执中、秦观同是江苏高邮人。孙觉还与黄庭坚结为姻亲,他的岳父是黄庭坚的母亲之兄李常。孙觉和李常都是皇祐元年的进士,而苏辙曾是李常的部下。苏轼与孙觉、李常的交往,比他与黄庭坚、秦观的相识还要早,他们之间的诗文往还更是多达数十篇,堪称亲密无间的好友。
综合来看,在熙宁年间,孙觉、盛侨、王汾成为所谓的“徐邸官”之前,苏轼与他们交往甚笃,他们三人占据了“徐邸官”职位的三分之一。然而,并未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实孙、盛、王三人与苏轼兄弟在政治上相互支持或协助。尽管如此,苏轼家族与“徐邸官”中的郑雍、乔执中翁婿以及陈轩等人关系复杂,他们同样占据了“徐邸官”职位的三分之一。
三
郑雍,字公肃,籍贯襄邑,现今属于河南睢县,于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这一天,由御史中丞一职晋升为尚书右丞。在《宋史》和《东都事略》中的《郑雍传》记载,他曾经(或曾经)被任命为尚书左丞,这一说法似乎来源于官方编纂的国史。然而,查阅《宋史·宰辅表》、《宋宰辅编年录》以及《郑公行状》这些文献,却并未发现有关他担任尚书左丞的记载。
郑雍身为唯一的“徐邸官”执政者,若时间允许,他或许能晋升为宰相。然而,这样的好景并未持续太久。在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太皇太后驾崩,哲宗皇帝亲理朝政。此时,御史周秩揭露了郑雍“因与徐王私交过密,而得以攀附权臣而得官”的事实。绍圣二年十月甲子,郑雍被免去尚书右丞的职务。在这场风波中,唯一为郑雍辩护的是钱勰,他与苏轼一同被誉为“元祐四友”。陆游所著《老学庵笔记》之第十卷,于1979年11月首次出版,其中第138页载有相关内容。
周、郑二人因苏轼而结下梁子。在元祐三年年底,郓州州学的教授周穜上呈了一封奏章,内容是“恳请将已故的宰相王安石供奉于神宗皇帝的庙宇之中”。学者刘成国等人经过考证发现,周穜与他的兄弟周秩都是王安石的表侄和弟子,他们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新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周穜的提议显得格外不协调。
周穜被任命为郓州州学教授,这一职位是由苏轼推荐的。面对舆论的压力,苏轼选择了自我弹劾,以等待处罚,并强烈要求对周穜进行严厉的惩罚。他还将幕后主使指向了吕惠卿,并暗指“吕惠卿之流”利用周穜试探太皇太后和朝廷的底线。最终,周穜被罢免了官职,回到了吏部,而苏轼则被特别赦免了罪行,尽管他犯了“妄举之罪”,但朝廷采取了宽容的态度,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依照文书处理流程,周穜的处理决定首先需经“三省共同呈递以取旨意”,从而确立“词头”,随后由中书舍人着手起草,之后交由事中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作为正式文件,由尚书省负责执行。郑雍作为“权给事中”,临时代替履行给事中职责,对处理结果予以驳回。(綦崇礼:《北海集》,卷三十四,《郑公行状》)
郑雍坚信,朝廷对苏轼对周穜行为性质(即“擅议宗庙”)的判断(即“以轼言为然”)应予以严厉处罚(如“弃市”),而仅仅“罢归吏部”的做法显得过于宽容。郑雍与苏轼之间保持着一种默契,他期望借此机会对周穜及其背后的势力进行清算,特别是以吕惠卿为首的“熙丰臣僚”,而吕惠卿兄弟更是苏轼兄弟的宿敌。他维宏在《史林》2023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中,探讨了元祐年间的一次“调停”事件,以及熙丰时期臣僚周穜向王安石献议配享神宗的事迹,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这应是郑、苏二人初识的起点。在元祐六年二月癸巳这一天,苏辙从御史中丞的职位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紧接着的三月辛酉,中书舍人郑雍则被提升为左谏议大夫;与此同时,徐王府的翊善陈轩和侍讲乔执中同时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这是按照惯例所请的结果;(详见《长编》卷四百五十六)到了八月辛丑,左谏议大夫郑雍进一步晋升为御史中丞,这一晋升成为了他开始执政的关键转折点。
欧阳修起初用“蹊田夺牛”这一成语讽刺包拯的不光彩升迁手段,主要是指通过陷害他人,将权高位重的大臣拉下台,自己取而代之的恶劣行为。后来,蔡确运用此手法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郑雍担任御史中丞时,也涉嫌“蹊田夺牛”。
赵君锡与贾易联名弹劾苏辙,郑雍挺身而出,为苏辙解了围,转而攻击贾易和赵君锡。结果,贾易被外放,赵君锡被调离原职,郑雍则取而代之,担任了御史中丞一职。苏辙的提拔对郑雍至关重要。《王岩叟系年录》中记载:“赵君锡、贾易对苏辙的攻击违背了众意,郑雍随后反击,有人议论说:‘他这是要篡位。’不久之后,事情果然如此发展。”(见《长编》第四百六十四卷)
元祐年间,贾易与苏轼结下梁子。由于贾易等人营造的舆论压力,元祐四年,苏轼不得不前往杭州担任知州。此次风波再次掀起,起因还是贾易,他指责秦观担任秘书省正字不合适,并批评苏轼过分渲染了两浙地区的灾情。苏辙身为宰辅成员,他私下将贾易弹劾的内容告知苏轼,苏轼便安排了自己的亲戚王遹(其弟王适是苏辙的女婿)去游说赵君锡;同时,他还通知了自己的弟子秦观,秦观随后也去见了赵君锡。苏轼著述,孔凡礼负责校对:《苏轼文集》第三十三卷,《关于贾易弹奏待罪奏章的辨析》,首次出版于1986年3月,位于第九百三十五页。
赵君锡与苏轼交往基于道义,秦观得以担任正字,全赖赵君锡的推荐。然而,王遹与秦观拜访赵君锡,却违背了台谏官的“谒禁”,也就是职务回避的规定。此外,苏辙被指控泄露机密,即便苏轼辩解称这些并非国家机密,贾易仍以此为由,强迫赵君锡一同弹劾苏轼兄弟。
贾易反复提及旧事,先是针对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对颜章、颜益的特殊处置提出质疑;接着又对苏轼的题诗行为进行深究,称之为“对苏轼题诗的诽谤”。在此过程中,给事中范祖禹、右正言姚勔、谏议大夫郑雍纷纷为苏轼辩护,并对赵君锡的言论进行批判,认为其观点相似且偏颇。苏轼对郑雍、范祖禹、姚勔的相助心怀感激。(《苏轼文集》,卷三十三,《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第934页)
郑雍与苏轼兄弟同年同榜高中嘉祐二年进士。宣徽使王公拱辰见到苏轼十分赏识,并将自己的侄子许配给他。王拱辰,字君贶,本名拱寿,是天圣八年的状元,仁宗皇帝赐名拱辰,他是三苏的伯乐,也是姻亲欧阳修的连襟。元丰五年之初,文彦博和富弼共同创立了“洛阳耆英会”,王拱辰也希望能加入其中。与此同时,赵颢迎娶了冯拯的曾孙,而冯拯之子冯行己也是“耆英会”的成员之一。司马光在《司马光集》卷六五的《洛阳耆英会序》中,于2010年2月出版的第一版,第1354页明确指出。
郑雍是王拱辰的侄女婿,而苏辙则是王拱辰的旧部。《栾城集》卷十四中,《王君贶宣徽挽词三首》一文中提及。郑雍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胡奕修,胡奕修的父亲胡宗愈与苏轼关系亲密。元祐初年,胡宗愈与苏轼、孔文仲彼此以亲信身份相互结盟,竭力排斥不支持自己的人。因此,郑雍首先协助苏轼兄弟清除政敌,随后苏辙推荐郑雍担任御史中丞,直至升至执政之位,这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
四
元祐七年六月辛酉日,苏辙由尚书右丞之职擢升为门下侍郎;与此同时,郑雍接替苏辙,担任尚书右丞一职。在元丰八年,左仆射王珪不幸去世,右仆射蔡确则升任左仆射。太皇太后询问谁可填补右仆射的空缺,蔡确回答道:“若依祖宗旧例而言,那么东厅参政最为合适。”这里的“东厅参政”指的是门下侍郎。一旦宰相职位出现空缺,苏辙将依次填补右仆射之位,而郑雍也将紧随其后,逐步晋升。
元祐年间,吕大防担任左仆射,地位稳固,苏轼兄弟亦受宠爱,未曾减弱;而右仆射之位,却如同走马灯般,频繁更换人选。苏辙除了静候时机之外,还指使台谏势力对右仆射进行弹劾,以此主动制造职位空缺,杨畏与郑雍则成为了苏辙的得力助手。
苏轼与辙同属蜀地人士,他曾先后对刘挚和苏颂发起攻击,实则暗中为辙铺路。在元祐六年二月辛卯日,刘挚晋升为门下侍郎并兼任右仆射和中书侍郎,然而不到一年,于十一月乙酉日,刘挚被免去郓州知州的职务,这主要是由于郑、杨的弹劾和陷害所致。
起初,王巩品行不端,却得以“堂除”担任密州知州,刘挚很可能对其进行了庇护。鉴于“刘挚之子为王巩之婿”,郑雍趁机对刘挚发起攻击,最终王巩得以罢免密州知州职务而侥幸逃脱。然而,郑、杨二人迅速截获了刘挚回复章惇诸子的私信,其中含有“自爱以俟休复”之语,他们添油加醋后,上报给了太皇太后。蔡确、章惇、邢恕声称自己有制定决策的功绩,指责太皇太后有废除或立新的意图,而“以俟休复”这一表述,透露出他们意图在太皇太后归政之后,重新崛起,扭转局势,清算旧怨,这无疑会触及太皇太后的禁忌。
郑雍与杨畏指责章惇之子弟私吞财物,意图谋取未来福祉,“上疏奏报,皇帝开始有了驱逐刘挚的念头”,这便是刘挚被罢相的经过。(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第十卷,中华书局,第597页)《宋史·刘挚传》记载,“休复”一词出自刘挚致邢恕的复信,这一记载或许源自《邵氏闻见录》,最初由李焘引用。《长编》记载,卷四百六十七;《宋史》中,卷三百四十,《刘挚传》部分,具体内容见第10849页。
刘挚被免去相位,然而苏辙并未能实现接替的愿望,反被苏颂所阻拦。在元祐七年六月辛酉这一天,苏颂从尚书左丞晋升为尚书右仆射并兼任中书侍郎;与此同时,苏辙也从尚书右丞一职被提拔为门下侍郎,达到了权力的顶峰;郑雍则从御史中丞升任尚书右丞,成为朝廷的辅政大臣。
杨畏对刘相的攻击意在指向苏辙,朝廷重新任命苏颂为右仆射,杨畏与邵言再次借机诘难,指责苏颂在处理贾易贬谪事宜上故意拖延。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御史中丞李之纯与苏颂的姻亲关系,试图将李之纯拉入战局,共同对苏颂进行抨击。
绍圣元年六月甲戌日,右正言上官均上呈弹劾文书,将吕、苏二人视为同一阵营。(出自《苏颖滨年表》)于是,左仆射吕大防未能出席讨论贾易贬谪事宜的御前会议,其行为显得颇为可疑。在剩下的三省长官中,门下侍郎苏辙、中书侍郎范百禄以及尚书右丞郑雍均倾向于同一立场,他们必然与苏辙保持立场一致。总之,若苏辙、范百禄、郑雍在贾易被贬之事上犹豫不决,苏颂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最终黯然离场,这样的结果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郑雍、杨畏、来之邵相继使刘挚、苏颂两位宰相失势,而苏辙却未能与右仆射一职结缘。邵伯温指出,“太皇太后看穿了杨畏等人的私心,于是从外部召回范纯仁担任右仆射”。王铚亦认为,“太皇太后察觉到言官们对吕大防、苏辙的态度有所保留,他们屡次攻击罢免宰相和执政,鉴于范纯仁的旧有德行,因此被召回并任用,直至国门才下达任命制”。
太皇太后看穿了苏辙及其同党的手段,毅然决然地摒弃了苏辙,并且打破常规,将前宰相范纯仁直接任命为右仆射。然而,杨畏、来之邵以及苏辙本人仍旧心怀不满,“杨畏等人暗中接受暗示”,“一致认为范纯仁不适合担任宰相”,苏辙的党羽杨畏和来之邵持续对范纯仁进行弹劾。(《长编》,卷四百八十二、第四百八十四)
五
元祐八年三月,御史董敦逸在奏章中直言“川人势力过盛”,并对苏轼、苏辙、范百禄等人涉嫌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提出批评,其中苏轼的行为尤为突出。(《长编》卷四百八十二)苏轼所引用的“亲信及同乡”名单中,便包括了一位名叫陈轩的“徐邸官”——他后来被苏轼推荐,官至中书舍人。(《范太史集》卷五十四)
范祖禹,字纯甫,出自成都华阳,是范百禄的侄子,同时也是吕公著的女婿。他为儿子范温迎娶了秦观的女儿,而苏轼则为其第三子苏过娶了范百嘉的女儿。正如晁说之在《景迂生集》卷二十《眉山苏叔党墓志铭》中所记载,华阳范氏与眉山苏氏之间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密。范祖禹还向朝廷推荐了“徐邸官”郑穆和郑雍,并认为这两位郑氏兄弟适合担任讲读之职。(详见《长编》卷四百三十七。)
另一位名为乔执中的“徐邸官”官至给事中,他与郑雍结为姻亲。(见《郑公行状》)苏轼所写的《答乔舍人启》一文,正是面向乔执中而作。元祐七年十月辛酉日,孔武仲担任中书舍人并兼直学士院职务,乔执中则被任命为起居郎,姚勔接替起居舍人的职位,吕陶被提升为起居舍人,高士英则由考功员外郎转任为右司员外郎,吴安诗则由直集贤院兼侍讲一职调任天章阁侍讲。
杨畏与来之邵所掌控的台谏势力之外,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等两制官员,以及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左右史官,均在历次权力角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这批被重点提拔的官员中,除了高士英之外,其余均与苏轼、苏辙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吕陶及孔氏兄弟则被明确归为“蜀党”。当时,中书侍郎范百禄负责官员差除的提名,而门下侍郎苏辙则主管审核工作,他们的职位提升与苏辙、范百禄的推荐和扶持密切相关。
因此,董敦逸对苏轼兄弟及范百禄的指责并非无中生有,上官均更是直言不讳地指责道,“范祖禹、乔执中、吴安诗、吕希纯这四位,均因吕大防、苏辙的喜好与厌恶而结党营私”。其中,吕希纯是范祖禹的妻子的哥哥,而吴安诗则是范祖禹的姑父。
御史黄庆基与董敦逸激愤地上奏,指责苏辙等人专权,然而李之纯、杨畏、来之邵希附和苏辙等人,反而指责黄庆基和董敦逸诬陷忠良。最终,黄庆基和董敦逸被贬谪至军垒守卫,这充分显示了“二苏”势力的强大,并且他们与徐邸官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
高士英与高士敦,均为太皇太后的亲侄,亦即赵颢的舅舅。高士英在高氏家族中颇为罕见,他成功进入了文官行列。在元丰八年九月己酉日和元祐元年八月己亥日,高士敦分别担任范百禄和苏轼出使辽国的副使,尽管最终未能成行,却因此结识了他们。三年后的四月初二,高士敦被任命为成都钤辖,《苏轼年谱》卷二十七第826页有载。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均作诗为其送行。《苏轼诗集》卷三十中收录了《次许冲元韵送成都高士敦钤辖》一文,位于第1582页;《栾城集》卷十五则有《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钤》一篇,见第303页;黄庭坚所著的《山谷诗集注》与《山谷外集诗注》的第十六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3年12月首次出版,书中第1019页同样收录了相关内容。
五年十二月,高士敦任期届满,转任邢州知州。太后亦为弟弟向宗良谋求相同职位。当时担任御史中丞的苏辙,对“二人同为外戚,却一得一失,于礼不合”的观点表示认同,认为朝廷不应有偏有向,因此他积极为高士敦辩护。由此可见,苏轼兄弟与高士敦之间的交往未曾间断。在《长编》卷四百五十三中记载,元丰末年,高士英及其弟高士充与王珪、赵颢关系模糊,三人皆牵涉到“废立”的阴谋之中。与此同时,高士英被提升为都司郎官,而苏辙、范百禄对他伸出援手。此情此景,或许导致苏轼兄弟与赵颢之间有了秘密的联系。
苏轼与赵颢的姐/妹夫王诜关系密切,他们还是莫逆之交,同时苏轼也与王克臣结为好友。(出自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十一,《王郑州挽词》第1637页)王克臣,字子南,他的儿子王师约则是赵颢的另一位姐/妹婿。
绍圣三年九月,赵颢去世,哲宗亲掌朝政,以章惇、蔡卞为首的新党派成员纷纷入朝,他们力图整顿旧党势力。哲宗对太皇太后及“徐邸”心生猜疑与厌恶,这为章、蔡二人清除异己提供了借口和机会。在此背景下,苏轼、陈衍被贬至海南,而司马光、吕公著、王珪等人也相继被贬至海南。
绍圣四年的尾声,“同文馆狱”事件突然爆发。当时担任枢密院事的曾布,将梁焘与苏轼兄弟并提,这完全可以被视为解读苏轼遭遇的一个缩影或参照。梁焘,字况之,来自现今的山东东平,他是“朔党”的领袖;而苏轼则是“蜀党”的领袖,两人政见相左,成为政敌。在苏辙的党羽攻讦苏颂之际,梁焘是宰辅中唯一挺身而出为苏颂辩护的人。
自“同文馆狱”事件爆发,刘挚与梁焘被疑与“徐邸”有所勾结。关于梁焘的处理办法,曾布曾这样表示:“梁焘罪行虽重,但最终也不过是流放到海外。”曾布与哲宗之间心有灵犀,他们都知道“流放到海外”是惩治那些与“徐邸”有染者的最终手段。随后,朝廷计划派遣吕升卿和董必前往岭南,对涉嫌同文馆狱的人进行惩处,而梁焘,这位已被贬至雷州别驾的人,自然成为了首要打击目标。所幸的是,“是日晚,闻梁焘卒”,而未能成行。
苏轼及其兄长与所谓的“同文馆狱”并无瓜葛,然而曾布曾上奏劝阻在岭南处决众人,却多次提及二苏,言道:“苏轼、苏辙听闻此事后,怎能不感到震惊恐惧?”这一点亦反映出,吕升卿、董必所诛杀的对象虽以涉嫌“同文馆狱”的“朔党”成员为主,但苏轼、苏辙同样未能幸免,或许正因为他们也与“徐邸”有所牵连。
元符元年三月,蔡京与安惇共同对“同文馆狱”案作出结论,将司马光、刘挚、吕大防等人案件合并处理。其中,“王府”作为关键因素,指的是徐邸,这表明哲宗对皇叔赵颢的成见极深。
司马光和吕大防均与“同文馆狱”无关,而“等”字所指的“诸人”中亦包含苏轼和苏辙,然而在提及曾任宰相的司马光、刘挚、吕大防时,却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此外,上官均将吕大防与苏辙并列,朝廷曾初步商议让吕大防流放到海外,然而哲宗认为吕大防为人所欺,此事便作罢。而那些可能出卖吕大防的人,很可能就是苏辙。同理,苏轼的影响力更为显著,因此,在“过海”这一过程中,成功的是苏轼而非苏辙,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恐怕也与与“徐邸”的交往密切相关。
王正伦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