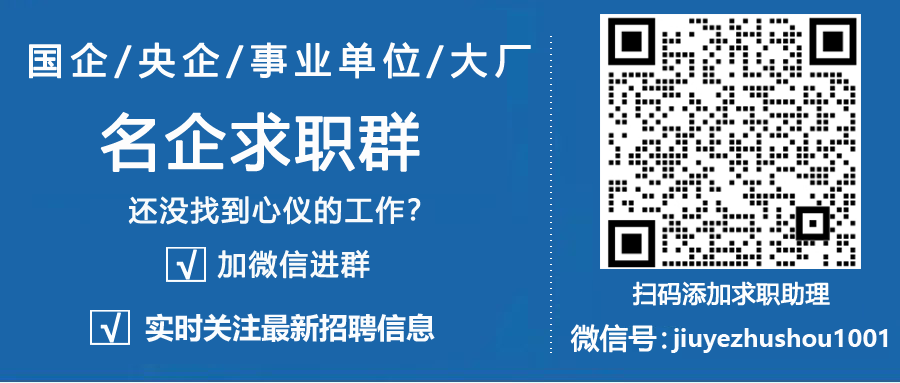中新社香港7月3日电 题:手工毛笔传人张宏霓:做毛笔就像做人,所有毛都齐心协力
中新社记者 韩兴桐
关于毛笔的起源,一说是“虞舜发明毛笔,用漆在方简上书写”,一说是“蒙恬首创”。现年77岁的香港毛笔博物馆馆长张红妮,对毛笔的一切记忆,都从她八岁那年的暑假开始。
在漫长的日子里,除了捉青蛙、蟋蟀、泥鳅之外,他还帮助忙着做笔的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比如晒兔毛、羊毛、鸡毛,拉直竹竿,或者穿过北京的胡同,把做好的笔送到买家手中。

香港书法毛笔博物馆创始人张宏霓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新社记者韩星彤摄
看到奶奶和姑姑坐在炕上的小矮桌上,端着一盆水,一堆兽毛,一坐就是半天,张宏妮对家族历史开始有了一些模糊的概念。据奶奶说,张宏妮的高祖母张杨是满族人,9岁被选入沈阳故宫学习制笔。聪明的她很快发现用卷烟做成的笔头更精致、方便,于是张杨亲手做了一支“大清一统”铜菊花笔头,受到清道光皇帝的嘉奖,被当做红笔御用。
正是在这样一个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年纪,张宏妮央求奶奶教他这项只传给女孩子、不传给男孩子的家传技艺。奶奶说,你一个男孩子,坐在炕上,对着野生动物的皮毛、羽毛,一坐就是几天,但几个月几年,你就坐不住了。
没想到,他竟然接下了第五代传人的位置,还随他一起来到香港。“我七岁开始接触毛笔,十三岁开始制笔,如今已经七十多岁了,依然对毛笔乐此不疲。”
1969年,张红妮一家移居香港,日子过得并不顺利。她们以为可以靠着家里的手艺谋生,但母亲跑上环各店铺打听,才知道香港的制刷技艺早已失传,需求量不大,大多依赖进口。张红妮无奈之下,只能在一家鞋厂当学徒,“工资一个月280港币”。张红妮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这个数字,因为当初老板生孩子时,拿不出礼金,就做了一把金蛇皮“龙袍蟒袍”胎毛笔作为礼物。
正是这一举动,让张宏霓这颗尘封的珍珠熠熠生辉。在老板的安排下,他为一名意大利人制作了一对“一挥而千须动”的毛笔。此后,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名声大噪。
采访当天,天空下着大雨,中新社记者在九龙土瓜湾的高楼大厦中迷失了方向。白发白须的张红妮撑着伞站在不远处,看上去颇为独立。她领着记者穿过商场,拐进一条窄巷,推开门,“香港毛笔博物馆”的金色招牌格外醒目。
在像给记者讲述自己的珍宝一样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的同时,张红妮频频站起来,兴奋地向记者展示馆内丰富的藏品:“清一统”铜菊花笔尖、“情侣扎笔”、“清代郎世宁笔”……这些背后,是王朝的兴衰,承载着传统的文化遗产,延续着“笔家”的家族传承。
该博物馆由张宏霓创办,作为他宣布退休后的一个慰藉,他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儿子。博物馆不仅展出不同时代、不同材质的毛笔,还举办各种毛笔文化教育和推广活动,如毛笔书法讲座、毛笔工作坊等,以增进公众对毛笔制作技艺的了解,弘扬中国毛笔文化。

张红妮紧跟时代步伐,会根据顾客的喜好,把刷子做成圣诞装饰品等物品。中新社记者 韩星彤 摄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眼中始终萦绕着那个八岁的男孩。张红妮记得,有一次,顾客不喜欢她送出去的毛笔,一气之下把试毛笔用的宣纸揉成一团,连同毛笔一起扔掉。张红妮因为没收到钱,不敢回家,在外面待到天黑,蹲在院门外睡着了。
后来奶奶告诉他,不要怕“烂笔头”,下次记得把纸和笔拿上。这样,他就能根据对方的握笔方法、墨迹深浅等细节,改进笔尖的软硬、粗细,把“烂笔头”变成“好笔头”。人生也是如此,机会总是等待那些永不放弃的人。
“做好笔,就是做好人。”张红妮喃喃地念着奶奶的这句老话。屋外,雨已停,天色放晴。转眼间,又是盛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