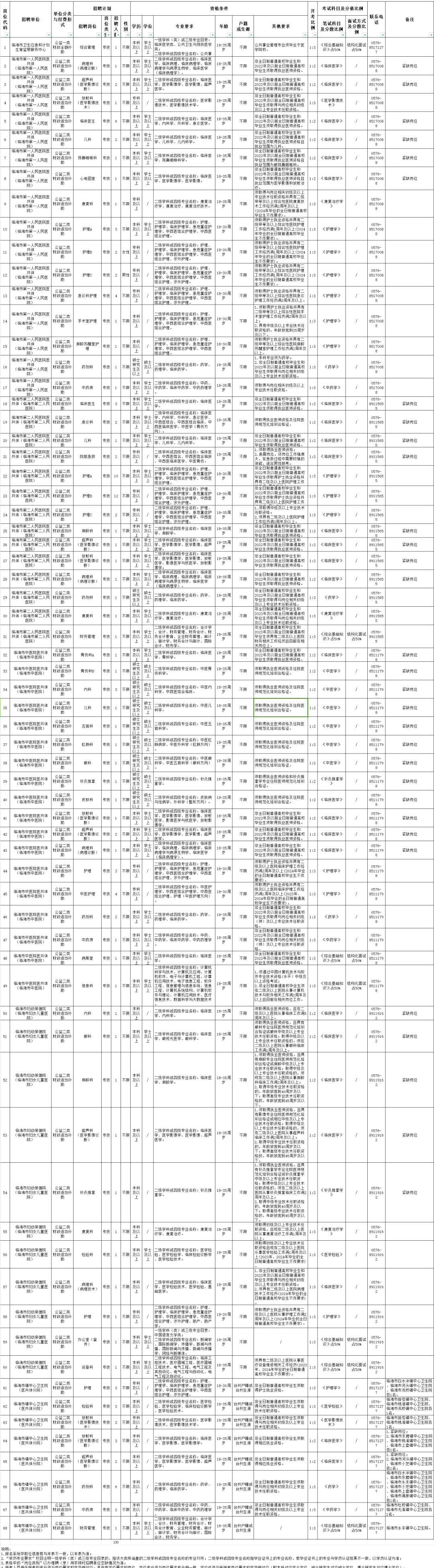当地时间7月24日晚8点,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演讲,首次解释自己突然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的原因,并称赞副总统哈里斯的经验、毅力和能力。
拜登说:“我相信前进的最好方式是将火炬传递给新一代。这是团结我们国家的最佳方式。”
自6月27日首场总统大选电视辩论开始,“换人”风波迅速发酵,民主党内部谣言四起,悲观情绪不断加剧,逼宫压力与日俱增。拜登是否应竞选连任成为民主党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焦点问题。拜登虽然多次力挽狂澜,但最终未能东山再起,与特朗普的第二次“终极PK”戛然而止。至此,拜登成为1968年以来首位不寻求连任的在任总统。当年,林登·约翰逊因处理越战的政策饱受批评,突然中途宣布退出竞选。
回顾拜登的退选之路,看似突然,实则是大变革时代个人无法抗拒时代和潮流的必然结果,是党派政治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突出体现,更是美国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到新高度的体现。

拜登成为1968年以来首位不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资料照片)

从“听灯”到“献灯”24天
自2024年美国大选周期开始,年龄和健康问题就被视为拜登连任的重大障碍,但这一问题长期被隐藏在经济、堕胎权等更贴近选民的议题之下,并未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议题。
与特朗普的首场电视辩论显著放大了这一问题,对拜登胜选的沮丧和恐慌开始在民主党内部广泛蔓延。变化之大、发展之快、影响之广都极为罕见,注定成为本次大选的分水岭事件。
首场辩论中,拜登面色呆滞、声音嘶哑、错误百出,糟糕的表现引起舆论轩然大波,党内对拜登能带领民主党赢得大选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罕见发表社论公开要求拜登退出大选,掀起了这场“换人风波”的第一轮声音。
电视辩论结束后的几天里,拜登竞选团队不断澄清总统健康状况良好,加紧竞选活动,努力平息外界疑虑。此时民主党普遍采取确保拜登参选的策略。一方面,党内舆论将拜登表现不佳归咎于其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准备不足,坚称民主党选民不会因此而放弃拜登;另一方面,党内高层发声支持拜登连任。前总统奥巴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均为拜登辩护,认为总统竞选不是看辩论表现,而是看总统任期内的表现。同时,潜在的接替者也明确支持拜登继续参选。副总统哈里斯、加州州长纽森、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等均表达了不更换拜登的意向。
随着事态不断发展,民主党“支持拜登”的共识明显松动,“换拜登”风波已超出舆论范围,开始在党内扎根。7月2日,得克萨斯州众议员劳埃德·多克特发表声明,成为首位正式呼吁拜登放弃竞选连任的民主党众议员。此后,公开敦促拜登退出竞选的民主党众议员名单越来越长。与此同时,拜登竞选团队在筹款方面遭遇困难,Netflix联合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迪士尼家族财富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罗恩·康威等民主党主要捐款人均已威胁停止捐款,以迫使拜登退出竞选。

7月11日,为了进一步平息各种“换位”噪音,拜登在北约75周年峰会结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深入阐述国内外政策,试图恢复党内信心。这是他近8个月来首次单独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是他在首场辩论后首次面对媒体关于身体和健康状况的众多提问。在发布会上,拜登的整体表现相比辩论时有所改善,但开场就出现了口误,误称哈里斯副总统为“特朗普副总统”。此外,他在北约峰会上误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普京总统”。如此“低级”的错误迅速跃居媒体头条,使他在发布会上试图展现的光芒黯然失色。 结果,这场新闻发布会不仅没有改变外界对拜登的固有印象,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党内党外要求他退出竞选的呼声。但对拜登来说,失言并不能掩盖他的治国功绩,更不能与他的竞选能力划等号。这些外界压力不足以改变他继续竞选的决定。
然而,祸不单行,一朝一夕。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竞选集会上遭枪击,掀起美国政界和社会舆论风暴。这一“黑天鹅事件”成为特朗普当选的重要助推器,进一步巩固了特朗普对拜登的领先优势。枪击事件一度转移了人们对拜登个人问题的关注,但这一问题从未离开民主党人的视线。事实上,特朗普前所未有的大选形势,进一步唤醒了民主党人对大选前景的深切恐惧,成为“权力更迭”的倍增器。随着拜登7月17日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讨论进入了“何时”换人而非“是否”换人的新阶段。
表面上看,“替代”之谜扑朔迷离,实则从未陷入双方势均力敌的局面,反而更像是反对力量不断壮大,直至积少成多,成为压倒拜登的最后一根稻草。

7月22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白宫发表演讲。这是拜登退出大选后哈里斯首次公开露面。图/视觉中国
民主党精心计算的政治结果

拜登是否会在7月21日前退出大选,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党内领导层的意见是否统一、选民支持度是否会明显松动、是否有强有力的替代候选人以及拜登自身的参选意愿。其中,自身的意愿是最关键的因素,但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党内领导层的意见则是最直接的外部压力。从此次风波来看,拜登并没有主观上退出大选的意图,但党内大佬们的“离心离德”和“背叛”,让拜登很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另谋出路。
对于拜登来说,民主党领导层的团结与支持是他竞选连任的重要基础。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正是党内领袖的声音支撑了拜登,帮助他艰难击败桑德斯,为他的竞选铺平了道路。在宣布参加2024年大选后,拜登迅速获得党内广泛支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竭尽全力为拜登筹集竞选资金,帮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锁定了提名。拜登一直与佩洛西、舒默、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动多项重要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支持拜登就是支持民主党三年来的立法成就,反对拜登连任显然有损党内团结和党的政治遗产。
但“改名”风波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核心逻辑在于,民主党领导层把这次选举视为高于一切的政治事件,把党内利益视为高于一切的政治优先事项。为了确保党内利益不受损害或少受损害,他们宁愿牺牲一切、重新开始。这正是拜登一度看不懂的“政治正确”,也是外界困惑的症结所在。
早在初选期间,民主党领导层就意识到年龄和健康问题可能成为拜登竞选的一大软肋,但当时拜登没有对手,党内缺乏考虑替代方案的合适土壤。但6月27日的首场电视辩论及其引发的舆论震荡强行打开了理性讨论的空间,让替代不再是一个禁忌话题。此时,民主党领导层虽然表面上支持拜登连任,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本党候选人的政治正确性,低估了辩论的政治效果。随着自由派喉舌几乎一致唱好拜登当选,反对拜登竞选的声势不断高涨,党内领导层看到了顺势而为、寻求替代方案的机会。佩洛西表示,拜登的表现是插曲还是形势,是一个合理的问题。特朗普枪击案成为民主党重新评估大选前景、探索第二条道路的重大觉醒时刻。
据美媒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后,舒默与杰弗里斯通过私下会面或中间人等方式向拜登施压,要求其退出竞选。奥巴马对盟友表示,拜登胜选几率已大减,需要认真考虑继续参选的可行性。尽管拜登屡屡表态将继续参选,但佩洛西仍公开要求拜登尽快作出决定,并在私人电话中告诉拜登,民调显示他无法击败特朗普,如果继续谋求连任,可能会导致民主党失去赢得众议院控制权的机会。针对上述报道,民主党高层在公开场合含糊其辞,表面上仍维持对拜登不稳定的支持,但拜登继续参选的政治基础已经崩塌。

奥巴马是支持拜登的“老朋友”
对于民主党领导层来说,经过首场辩论,拜登击败特朗普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枪击案发生后,民主党如果不尽快推动“换人”,不仅会输掉总统大选,还可能把参众两院拱手让给共和党,彻底沦为反对党。这是民主党领导层无法承担的政治和历史责任。权衡利弊后,换掉拜登或许不是最佳选择,但或许比让拜登勉强参选更好。
在领导层的默许或授意下,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议员数量在短时间内激增。其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仅一天的7月19日,成为拜登自首次电视辩论以来遭遇国会退选呼声最高的一天。共有13名民主党议员加入呼吁拜登退选的行列。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统计,截至拜登退选时,共有37名民主党议员(包括32名众议员和5名参议员)公开呼吁拜登退选。 从议员构成来看,这些议员跨越了党内世代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涵盖了所谓的“安全选区”(如加州)和摇摆选区(如亚利桑那和密歇根),还有国会黑人党团和西班牙裔党团成员等拜登的长期坚定支持者。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共同诉求。这些都表明,拜登的重点支持已经充分松动,并成为最终压垮拜登的重要推力。
在选民支持率没有出现断崖式下滑、党内对替代候选人(如哈里斯)不抱希望的情况下,拜登退出大选的最重要原因,除了健康问题,就只能是党内领导层精心策划的退位。在退出前的24天里,拜登的竞选态度从坚定不移到微妙转变,引用天意、火车事故、医生意见等,虽然仍坚持竞选连任的决心,但已不再毫无保留地坚定。拜登在退出声明中表示,虽然自己“一直有意谋求连任”,但“为了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应该退出大选”。这充分说明,拜登退出大选并非个人主动,而是在党内巨大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民主党将走向何方?
宣布退出竞选后,拜登正式推举副总统哈里斯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调显示,哈里斯已获得过半初选代表的支持,有望以较为稳定的候选人身份出席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不过,由于民主党仍在消化拜登退出竞选的后果,哈里斯的竞选之路或将不会一帆风顺。

从党内提名看,高层支持仍未回归。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加州州长纽瑟姆等人均表示支持哈里斯竞选总统,但奥巴马、舒默、杰弗里斯等尚未表态。部分国会议员表示支持开放提名程序,以便为其他候选人留出空间。从大选前景看,哈里斯担任副总统期间的表现乏善可陈,并未向选民展现出她作为未来总统的政治潜力和能力。与拜登共事的经历,使哈里斯难以摆脱拜登执政时的负面资产,更可能成为共和党攻击的对象。
接下来民主党如何能迅速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并有效调整竞选策略,将成为其能否与特朗普抗衡,甚至保住至少一院席位的重要因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张腾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聂维曦)
刊登于2024年7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第1150期
杂志标题:拜登的退欧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