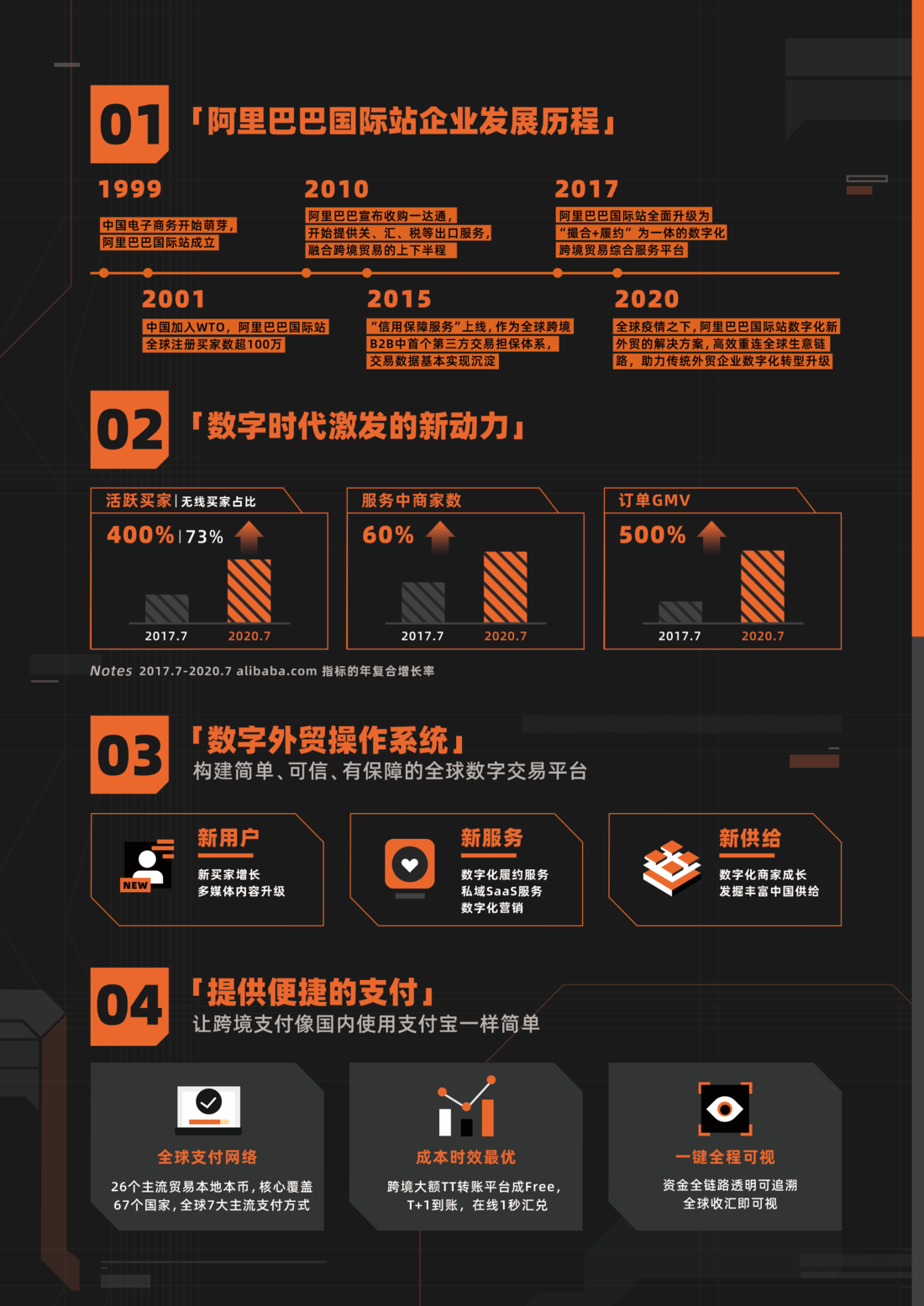在外流浪的人们,最怀念的是烟台的新鲜味道。
这种美味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不是某种海鲜的味道,而是风的味道,海水的味道,家家户户门前炒菜的香味,小摊前烟花的味道。

第一是海的味道。一下火车,轮渡码头就在烟台站后面,海的味道和温度正好的风将味道带到了我的鼻尖。烟台的风很狂野,烟台人从小就被扇扇子吹惯了。冬天,这风能划破你的脸,吹掉你的嘴,钻进你厚厚的羊毛围巾里,走路时还会把你推得东倒西歪。下雨天,这风能把伞骨扯断,大家拿着倒扣的锅盖,撑伞成了笑话。
唯有九月,风儿不再冷酷无情,而是温和宜人。站在火车站楼顶的透明大厅里,海风吹来,凉凉的。人们从空调列车里走出来,做好了炎热的准备,但僵硬的头皮却一下子放松了下来。车厢内外的温度几乎一样,这全都是风的功劳。

熟悉的海风比身处海滩还要舒服,你可以想象海浪拍打海滩的声音,冲击着岩石,落进岩石的缝隙中,然后一口气吞下海水,哪怕闭上眼睛都可以。
但不管是在沙滩还是在礁石边,最热闹的肯定还是人声。孩子们追逐嬉闹的笑声烟台海鲜加工大排档,情侣们的窃窃私语,烟台一位身强力壮的老人击水搏浪的声音,疲惫的人们只是默默地在背景中看着大海,一句话也不说。小时候在海边晒伤过,晚上躺在床上,后背火辣辣的,不能躺也不能趴着,这是因为白天玩得太多了,泡在海水里不肯出来,整天都泡在太阳底下。


海水是咸的,非常咸。但海里的生物却神奇地甜。游一会儿后,找一处浅滩站定,把脚往下挖,下面的沙子细腻柔软,很容易踩到贝壳。把两个贝壳撞在一起,运气好的话,可以把贝壳掰开,软软的蛤蜊肉就摆在眼前。吸一口汁水,粗略咀嚼,然后扭动转身去踩下一个。
在海边最容易钓到的是花蛤,壳呈黑色,上面有白色的花纹。运气好的话,还能钓到飞蛤,壳呈黄色,肉质厚实,不过不太好钓,有时踩上去明明就在那儿,弯腰去摸却不见了。它们溅起水花后能自己飞很远,所以叫飞蛤。

这个做法是我小时候爸爸教我的,我看着他吃了好几个才肯尝试。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海鲜可以生吃,也不知道后来在饭店吃到的淡菜、扇贝比我家门前菜市场三块钱一斤的淡菜、飞蛤要贵得多。虽然仔细一看,它们也是祖传的。
妈妈说,小时候,我们家很少买螃蟹,要吃螃蟹的时候,爸爸就会背着麻袋,拎着半袋螃蟹回来,一顿吃不完就煮一大锅螃蟹,分给邻居吃。这些东西我早就忘了,但我记得我们家确实有带呼吸管的游泳镜,跟浮潜镜差不多。想想30年前爸爸那么时髦,不禁感叹,现在的生活确实不如从前了。

忘了说了,在烟台,潮汐就是脑袋不好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说“潮”人。但到了晚上退潮的时候,这里确实人山人海。叔叔阿姨、下班后的家庭主妇、玩得不亦乐乎的孩子,提着塑料袋、网袋、小铲子和水桶,奔向他们的战场。
战利品不只螃蟹、蛤蜊,还有海藻、水母,从岩石里捞出来的牡蛎、海螺都装在小桶里,晚上回家就能吃上一盘。

当文艺青年们到大海里寻找爱情的时候,我们这些生活在海边的年轻人,却到大海里寻找食物。
这次回家,舅舅请我吃饭,切了一大碗海蜇。海蜇就是水母,不蜇你的时候圆圆的,很可爱。新鲜的海蜇汤只有在海边才有,因为海蜇身体90%以上都是水,所以一会就化了,不喝的话,很快就变成一碗海水了。所以只能在海边喝,餐厅也很难备货,就算多也卖不出去。

这个跟你在饭店吃到的老醋海蜇头是一样的,但不是同一个品种,那些一般都是经过加工的海蜇头和海蜇皮,腌制浸泡而成,当然还是有鲜味的,但不如喝鲜的好吃。
海蜇汤是我妹妹最想吃的。因为除了这个,在北京什么都能买到。趁海蜇还是整只的时候,洗几遍,剁碎,撒上切碎的香菜和辣椒,加一点麻油和白醋,就可以喝了。冰爽滑润,咬起来脆脆的,酸酸辣辣的,很鲜。

我可以一口气喝下四碗海蜇汤。当然,这不包括主菜里的三四只螃蟹和一小盆螳螂虾。我们称螳螂虾为“爬行虾”,因为它在水下爬行。像飞蛤一样,它们的名字来源于它们的运动天赋。

在其他温州小吃摊上也可以吃到新鲜的螳螂虾。不过我总觉得椒盐不如清蒸好吃,而且也不用蘸什么,直接剥一碗就可以了。
螳螂虾、海螺、螃蟹等肉多肥美,但都性寒,蘸上姜醋、两滴麻油,可祛寒解腻。米酒煮螃蟹,温一锅,加点姜丝,撒上枸杞红枣,一口螃蟹,一口酒,是神仙永远换不掉的美味。

2017年夏天做了一大锅醉蟹钳,配酒也很不错。活蟹用白酒浸泡,蟹洗净,加入绍兴陈年黄酒、大姜、小米椒、干辣椒、八角、花椒、香叶,下锅煮熟,味道很鲜,加盐调味。密封罐头放冰箱冷藏。贪吃的打开一口,酒香扑鼻而来,鲜香可口。将蟹膏抹在白米饭上,热气腾腾,扑面而来,仿佛坐在大海中央。
还有一种最适合下白米饭的,是我儿时的美食。那时候海胆不贵,班长(我一直叫妈妈刘班长)骑着摩托车带我去砍价,她总是等大家都走了才开口,一下子就买了好多。避开层层的刺,掰开,黄黄的海胆一个个露出来,软软嫩嫩的。一锅鸡蛋汤,里面煮着海胆肉,汤汁浓稠,海胆肉嫩滑,能多吃一碗饭。

新鲜是大海的馈赠。有时风好的时候,海边会突然变成一个宝库,一夜之间出现很多海鲜,全部炸开。有时是生蚝,有时是水母,有时是别的什么,炸开后整个沙滩都会炸开。晨练的叔叔阿姨们会赶回家拿点罗勒,像过年一样,一直到中午才收海鲜。
去蓬莱长岛之前,我对钓鱼一无所知。长岛最有名的金钩虾,都是摊在街上晒的,就像内陆村子里晒玉米一样。晒虾的时候,整个村子的街道都是金黄色的。晒海带的时候,又变成了深褐色。

图:赵锦阳(齐鲁晚报)
走在街上,随便摘几个吃,虾米个头虽小,但鲜香的味道却能撑爆你的整个嘴巴。
长岛的海域是个富矿,鲍鱼个头大,海参肥美,鱿鱼、鱼就更不用说了,个个肥美嫩滑,干巴巴的更不用提了。

那时,一袋一袋吃海鲜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经常跟随渔业部门记者李娜拍摄休渔期和开海的情景。当扇贝肥美的时候,我们找来一艘刚停在海边的船,把刚从网里捞出来的扇贝捡起来,费劲地把它们扛回家。
那家是临沂人,以前很喜欢吃三文鱼,但在烟台从事渔业三年后,她就吃腻了。这成了我们吹嘘烟台的笑话。烟台那么大,我们也没办法。
坐在桌前剥螃蟹直到筋疲力尽,我突然想到,鲜并不起眼,它从来都不是主角,大多伴随着酸甜辣咸,但似乎里面有种不同于其他调料的东西,仿佛鲜让这道菜活了过来。
鲁菜的鲜美背后还有一段故事,最早的故事与海参有关,故事中厨师临终前将自己的烹饪秘诀告诉徒弟,将海参晒干,磨成粉,藏在上菜的袖子里,等上桌时,在人们背后撒上,这道菜自然独树一帜。

这就如同如今的味精和鸡粉一样,人类要学会保存鲜味并不容易,但又无法将所有的鲜味都归类,并对应到化学原料上。大骨汤的鲜味、用黄油在铁板上烤松茸发出的滋滋声、以及一口汤汁都充满的牡蛎壳的鲜味,各有各的魅力。
我爱烤海参里的汤汁,海参在炭火上收缩烟台海鲜加工大排档,腔内留有少许汤汁,实在是美味。3元一小块,我必须横着拿着慢慢移动,把嘴贴近,一边吸,一边吸。吸完汤汁,再慢慢咀嚼另一根海参,顺着胃部下去,感觉很舒服。


很多年以后,我曾让父亲做辣虾,他拒绝了。父亲的理由是,辣虾从前海运到内地,鲜味已经流失,所以多放辣椒来掩盖。刚捕捞上来的虾,只有经过清蒸,才能保留原汁原味的鲜香。
我当时不接受,但现在我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