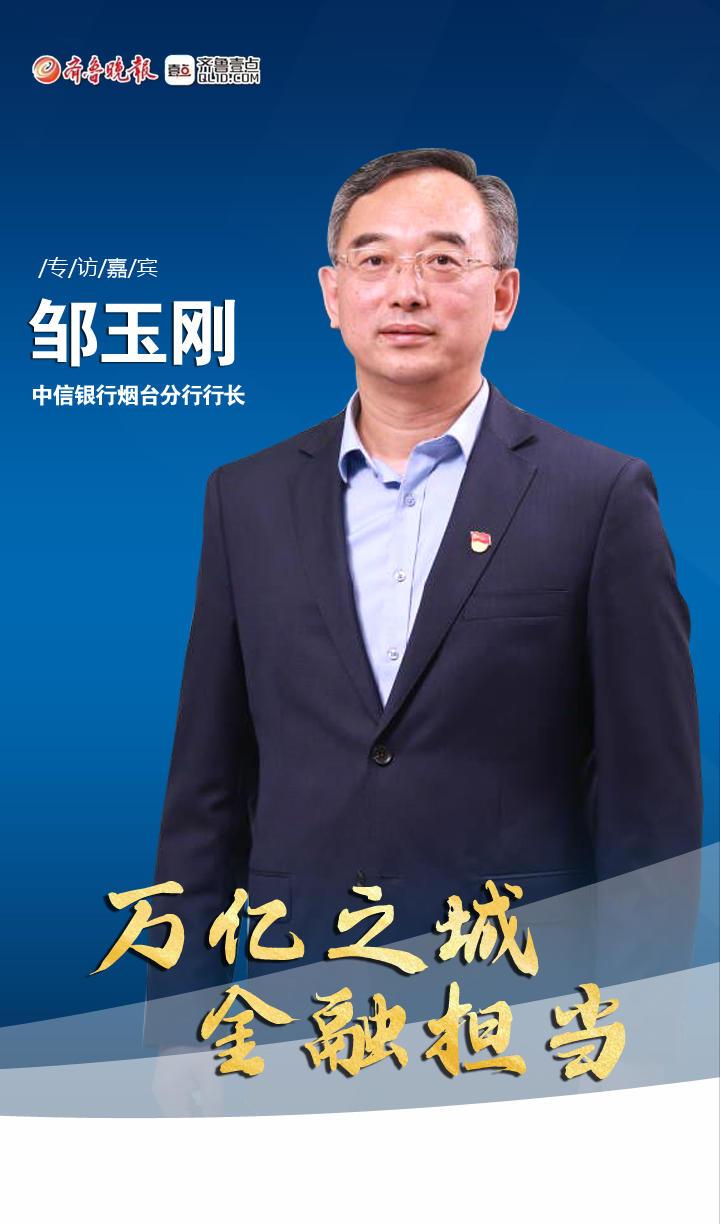《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当时韩愈是四科博士。文中所谓的“师”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教师,也不是指“授书授句”的启蒙教师——唐人并不否定这种能读书识字的教师,而是指学有所成,能“传道纳生解疑”的人。这样的教师的标准很高,不但要通晓经学,而且还要是一个“通晓道理”的人。俗话说,“道理在,师在”。韩愈不仅自称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以师为人师。柳宗元在《答魏钟离论师道》中说:“魏晋以来,人愈不肯事师,今不闻师,若有师,必笑之,以为狂人。”(《刘鹤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下略)这也充分说明,“师”已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有特定的含义。
与此相关的,是对“师者,教道、教学、解疑”的理解。人们通常认为,“师者,教道、教学、解疑”这句话,揭示了教师的作用。其中,“道”指孔孟之教,“受”与“授”同,“学”指儒家经典。这种解释出自曾国藩:“教道,即修身养性之道;授学,即古文六艺之学;解疑,即解疑此二种之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皆有追求,所以常将二者并提。” (马其昌、马茂元,《韩昌黎文集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以下只标明页码)另一种观点来自吴晓如先生,他在《读韩愈《师说》中提出:“师者,教道之人,受学之人,解疑之人。”紧接着第一句“古之士”,意思是士人求师,是为了继承古人之道,接受古人之学,解自己的疑惑。并不是教人,传授知识给人,解人的疑惑。(吴晓如,《中国古代文献精读例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如何正确理解,值得探讨。
韩愈以澄清佛道思想,恢复和确立儒家正统为己任。他在《道源说》中说:“吾谓道,非老佛之道也。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子,孟子死后,不传了。”(第20页)韩愈自认为是正统思想的继承者,他最早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传承进行了总结,将正统思想追溯到尧、舜、禹、周公,说明他所创立的正统思想源远流长。因此,把韩愈所传之道仅仅看作孔孟之道,恐怕并不全面。韩愈在《进学说》中借学生之口说道:“师不辍,六艺之文,百家之书,无不读。”(第51页)由此可见韩愈主张以儒家为本,向百家学习。他在《送孟东野序》中,除了肯定孟子、荀子外,还肯定了墨子、庄子、屈原、张仪、苏秦等人:“庄子以荒言而出名;楚国之大国,屈原而亡;臧孙臣、孟子、荀子以道学而出名;杨朱、墨子、管义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师郊、孙武、张仪、苏秦以术学而出名;秦国之兴,李斯而出名;汉朝之兴,司马迁、相如、扬雄而出名。” (第261页)韩愈在《答后稷》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学习态度:“吾自幼好学,五经之外,百家之书,皆读之,而无不通其义。”(第184页)由此可见韩愈兼收并蓄的胸怀。《经学解》中“上师尧巳,浩瀚无边”,《师说》中“孔子之师,郯子、苌弘、施襄、老聃”等,都体现了韩愈的胸怀开阔。
曾国藩解释的另一个缺憾是,将“受”理解为“赠”。上海字典出版社出版的《古文赏析辞典》在《师说》注中,将“受”视为“赠”。《唐宋八大家赏析辞典》则直接将“受”改为“赠”。(《唐宋八大家赏析辞典》,上海字典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这一点值得商榷。首先,从版本上看,宋末廖应中适才本《韩集》、近代古文大师马其昌与其长孙马茂元教授编撰的《韩昌黎集》,均以“受”代之,不以“赠”。市面上的书,不要随意更改古人的版本。其次,“受”不是“赐”的同音字。“赐”是后生字,在“受”后面加了一个符号。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受,说这个,受,说那个,相通。”(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580页)“受”本身就含有受和赐的意思,也就是所谓“赐受”一字之分。就是你给我,对我来说是受,对你来说是赐。古字上面一个爪,是手,下面一个爪,也是手,中间就是受和赐的东西。 “授”和“受”不可互换!后世的词怎么能借用古词呢?而且,韩愈在《师说》中,把“受”和“授”分开了。文中有一句话:“其子之师,教其书,使其学其文,非吾所谓教其道,解其惑。”这里用的是“授”,是传授学术的意思。很显然,开头的“受”不能解为“授”,解为“接受”也不准确,这里的“受”只能解为学习。这种用法在唐代以前很常见,如汉代刘歆的《辞去太常郎中迁书》中说:“及至孝文帝,史官晁错,始从伏生学《尚书》。晋代杜预《春秋释义集序》云:“左丘明从仲尼学经。”唐代李延寿《北史》卷五十八《齐阳王传》云:“少时随武帝学诗传,通要而得精髓。”这些句子中的“受”就是学习。“受”就是学习六艺的经典。在懂得修身治人之道、学习经典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疑惑。“解疑”就是曾国藩讲的解这两个疑惑。所以,对“师者,教以道,受以识,解以疑”的正确理解,是作为教师,必须肩负起复兴正统、学古文六经、解决求道求学过程中出现的难题的责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韩愈在《师说》中,只强调教师有“道”可教,必须解决“道”的难题,而没有对“受”作展开。原因在于“受”是教师自身的要求,“受”本身也是求道的过程,因为在古人眼中,修身养性也是一种知识的学习。所以韩愈在写作时,并没有对“受”作展开。“师者,教以道,受以识,解以疑”其实是在讲教师的标准和要求。文章提出了跟谁学的问题。
韩愈之所以写《师说》,是因为他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担任四门书院的官职。许多人来找他或写信向他请教,韩愈就把自己对文学和道教的看法告诉他们,劝他们注意修身养性。这些请教的人中,有年纪较小的,也有年纪较大的。对此,韩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生于我之前,闻道先于我,吾当以师;生于我之后,闻道先于我,吾当以师。”他把所有向他请教的人都视为弟子,而一般人则往往把“人之难处,在于好为师”当成一种警示,不以师自居。如柳宗元在《答魏钟离师道》中就提出“取其精而留其名”,即可以帮对方,但不敢以师自居。但韩愈并没有回避师徒身份:“唯韩愈勇于不顾俗,受尽讥笑辱骂,招收学生,写《师说》,因抗拒而为师,天下怪人云集,聚众骂他,指指点点,拖拉他,加添言辞。”韩愈的行为引起当时羞于拜师的文人不悦,甚至有人聚众骂他,视韩愈为狂人。骂声中,韩愈觉得有必要正一正师道。于是,爱好古文的李蟠在向韩愈献师之礼时,写下《师说》,挑战当时羞于拜师的陋习。这也招来了更多的嫉妒。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任监察御史时,写了《御史台上天寒饥民论》,十二月九日被贬到阳山。贬令一到,他便立即启程,连安顿家人、与妻子告别的机会都没有。韩愈在《往江陵途中,送王二世、李士仪、李二十六、三翰林学士》中回忆道:“钦差大臣登门送别,我片刻也不能停留。病妹卧床,我知明暗相隔,哭求离去,她不肯答应。” (方世居撰,郝润华、丁君里编,《韩昌黎诗年谱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0页)多惨啊!关于韩愈被贬,柳宗元在《答魏钟离为师途》中说:“居长安,无暇烹煮,被拖东去,屡次如此。”他认为朝廷对韩愈如此苛刻,不仅是因为他得罪了时任京兆尹李适,更是因为韩愈的师德名声。韩愈被贬阳山时,柳宗元是监察御史李行,应该很清楚朝廷的内幕。柳宗元的判断是可信的。
光明日报(2024年8月19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