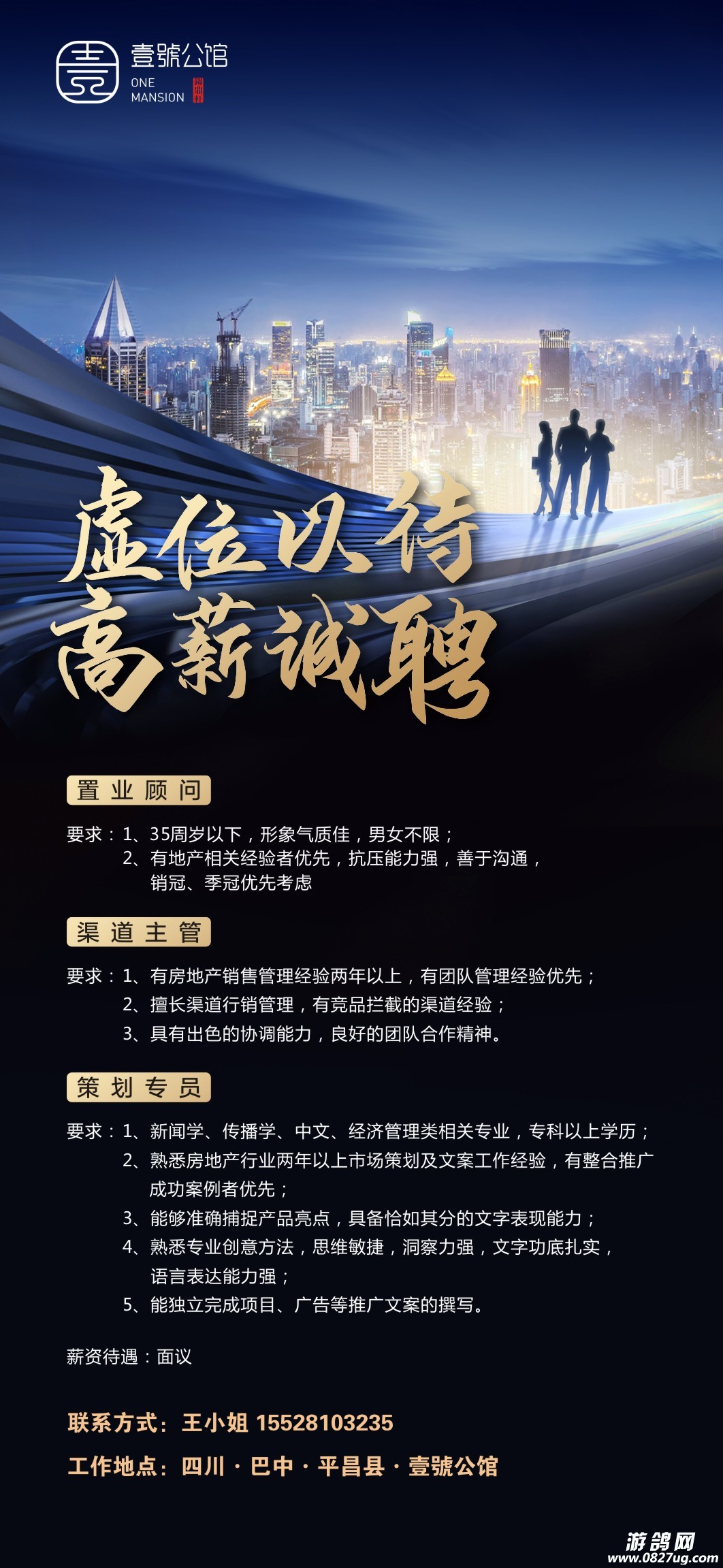连日来,地方债务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议。
起因是网上流传的重庆市碧山区政府的一则红头通知,要求成立专项小组落实推进国有资产振兴工作方案。其实目的很明确,就是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
一直存在的地方债务风险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中央政府之前已经有过多轮治理。此外,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债务比率并不算太高,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
然而,与法定债务相比,近年来地方隐性债务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受到了市场的更多关注。
2023 年 6 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其关于 2022 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中指出,部分地方市县债务风险较高,新的隐性债务仍在发生。
什么是隐性债务?在 GDP 冠军下,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要求通过融资来加速发展,再加上中央政府长期要求地方政府不发债,历史上积累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部分是通过城市投资借入的隐性债务,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各类债券。学术界也一般用城投债的规模来代替地方隐性债务的规模。
例如,2023 年,城投主体违约和风险预警记录多达 235 条,其中非标违约 181 家,共涉及 97 家城投企业。
这个标志本身就是一个警钟。难怪,2023年以来,按照“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减债方案”的决策部署,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纷纷为地方债务减债做出了具体努力。
减债无非是开放资源和减少支出。
我们先说开源,其实要看政府的收入从哪里来。
以前,不含税,房产收入是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放缓和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土地融资的好处也相应减弱。如何寻找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是释放地方债务的关键问题。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搞活国有资产的问题上。此前,国有资产收入与出让地收入的差距仍然相对较大,这也表明存量资产很可能得到充分利用。例如,2022 年,土地出让收入为 6.69 万亿元,而国有资本运营预算收入仅为 5689 亿元,差距很大。
近期,各地纷纷出台化解地方债务工作计划,路径也比较相似,主要是通过盘活存量资产来偿还债务。说白了,政府卖掉一些资产换钱,用这些钱来还债。
例如,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子县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该县盘活1489.6万元,从底部收回650万元,优先清偿债务和重大项目支出;
事实上,盘活存量资产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也是本地化债券的常见做法,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般来说,政府的存量资产包括三类:一是行政机构的实物资产,如闲置房屋和车辆、各国政府规划建设的闲置房地产、未得到有效利用的土地资源等;二是行政机构的金融资产,包括临时性金融存款、临时付款、 股权投资资产等;三是国有企业的资产,包括融资平台的资产。
不过,在具体操作中,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也存在诸多困难。首先,要盘活的“资产”不同,价值也不同,而且由于每个地方的经济实力不同,每个地方转债的能力往往差异很大。
更有力,在一些专家看来,地方政府缺乏出售资产的动力和意愿,尤其是优质资产,更是舍不得出售,最终“你看别省,别省看你,大家都不卖”。
正是因为“开源”如此困难,“节流”才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
2023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47 号文”,全称《重点省份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分类管理办法(试行)》。这种管理办法实际上是中央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采取的“一揽子债务”措施之一,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是严格控制政府新增投资项目,二是严格清理和规范在建项目。
该文件还确定了 12 个减债重点省份,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宁夏。
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政府投资项目的管理主要以项目建设的完成情况来衡量,其中项目总投资的完成率低于 50%,原则上会延迟或暂停建设,如果高于 50% 但存在重大问题, 不得继续施工。
说白了,就是要求地方政府“不该花的钱都不要花”。
这个规定不是没有空穴来风的,各地过度和无效的投资都有过去的教训。据今年年初的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显示,李在勇担任流盘水市委书记三年多,地方新增债务达1500多亿元,推动建设23个旅游项目, 其中 16 个项目被贵州省列为低效闲置项目。由于盲目借款,仅债务利息就造成了 9 亿多元的重大损失。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将其债务降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甚至“谈论债务的变色”。
债务本身归根结底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政府适度借款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也是国际惯例,以合理的规模和有效的支出促进经济发展也是国际惯例。
钱花不花,花了多少,就看能不能花在“刀”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