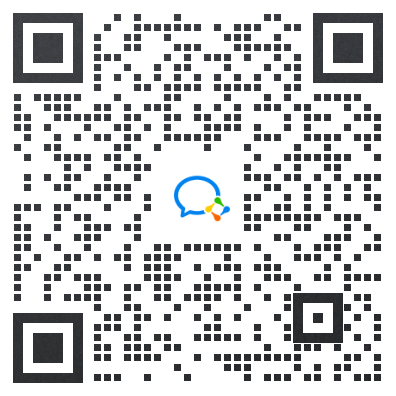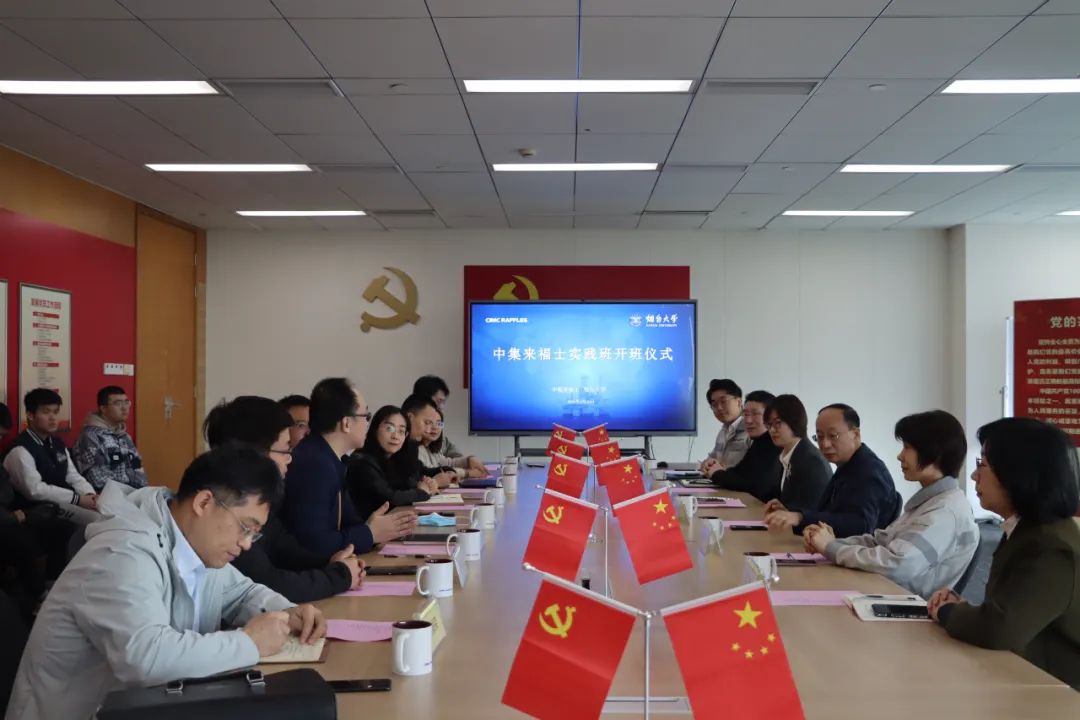明朝末年官员王守仁(1472-1529 年)——笔名王阳明——在讨论摇摇欲坠的明朝的军事需求时,会参考中国最受推崇的军事著作《孙子》和《吴子》。在讨论良知和圣贤时,他参考了孟子。王阳明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军事战略家,他知道孟子反对暴力和战争;鄙视梁惠王的“好战”;斥责齐宣王“兴兵危臣,激怒诸侯,然后自得其乐?”;认为梁襄王有所欠缺,并建议他只有“不爱杀人的人才能团结人民”。在 16 世纪,没有人将孟子视为战争方面的权威;尽管他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向人民灌输军事勇气的建议,但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完全被忽视了。

王守仁
不管作者是曾主持过数次军事战役的文官王阳明,还是写诗并和各种文人交往的伟大将军戚继光,军事问题只能在古代军事传统中讨论。这种文学传统(以《孙子兵法》为最佳代表)可能在战国时期发展起来,当时职业竞争日益两极化,政治顾问强调礼仪和美德,军事顾问强调保密和欺骗;在王阳明和戚继光时代,军事著作早已成为竞争激烈的科举制度的教科书。
和其他国家支持的正统思想一样,比如朱熹 (1130-1200) 对儒家思想的诠释,《七经》也成为成千上万希望通过考试获得晋升的学生年复一年学习的对象;学习朱熹的人希望成为文官,而其他人则参加武科考试。这两种思想传统遵循着相似的轨迹,经常相互借鉴,同时在形式上否定、抵制或忽视对方。要想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成功,就必须精通两者。理想的将军精通哲学,而最受尊敬的文官经常组织民兵镇压土匪团伙。此外,考试在人员、结构、地点、程序等许多方面都有重叠。那些精通兵书和射箭、身体健康足以参加武科考试的人,有时拥有与通过文科考试的人相同的文学技能。
许多文人观察家嘲笑清朝武举的文学内容,但那些登上成功阶梯的人留下了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证明了他们对文学文化的广泛和深入的了解。请看 1734 年版《山西通志》中的一首诗《寒食路》。
春风从哪里来?
晴朗的早晨来临了。
没有红杏花,
柳枝绿绿的。
这首抒情诗是马剑波在任太原将军时所作。马剑波和他的堂兄弟、兄弟和曾祖父一样,也是武科状元。虽然传记记载马剑波通过了陕西乡试、北京会试和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年在位)主持的殿试,但没有现存的武科文献提到他。1691 年秋天,他通过了会试和殿试,并被授予武科进士的称号。
1703 年,马剑波被任命为太原都护,这是武士的常任职位;太原是山西省的战略要地,从 1672 年到 1731 年,曾由两位武将和另外三位武士管辖。在此期间,只有九人担任过这个职位,其中两人相当于武士:一个是内务府的奴仆,另一个是禁卫军。在马剑波的五年任期内(后来延长到十二年),他向康熙皇帝上奏,揭露了非法猎枪的普遍存在,并建议没收猎枪并控制火药生产;这些建议很快被采纳。两年后,马剑波上了一份更为雄心勃勃的奏章。
《七经》注释有异,请择其一刊行。另祭孔时,驿长以上文官可随祭,武官副将以上方可随祭,请将武官视为文官,行相同礼仪。
这是根据《清实录》所记载的奏折,但其他文献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信息。虽然《清实录》在大部分细节上与《实录》一致(或者说,我们将会看到,缺乏细节),但它确实承认马剑波要求儒家官员选择正统的军事经典,并明确将奏折与前一年颁布的一道法令联系起来:康熙皇帝对参加武举考试的人的素质不满意,并敦促那些智力和体能都合格的绿营士兵将考试作为晋升的手段。然而,《清实录传》和《国朝集贤类政》(两本书中的相关段落大致相同)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
根据这些文献,马剑波提出的要求不只两个,而是三个。除了《清实录》中记载的建议外,据说他还建议奖励有文化的士兵:通过武举考试并能解释《论语》的人应该获得职位。

康熙皇帝
1710 年 11 月 10 日,康熙皇帝重新审议了这些此前被兵部拒绝的提议,并给予了非常积极的回应。长期以来对武举考试的不满促使他发起并批准了一系列改革,但他从未考虑过改变课程设置。相反,他在射箭考试中考虑到了距离,将许多通过殿试的男子分配到禁卫军中,并鼓励汉旗人参加考试,还有其他一些改革。《清实录》记录了康熙皇帝对马建波提议的异常个人化和深刻的回应:
《兵法七经》我都看过了,内容很杂,也不全都正确。里面说的火攻、水战,都是空话,如果照他们的话去做,就永远打不赢。而且还有法术、算命的说法,刚好能激发小人的邪念。我过去办过不少军事大事,平定三国、攻占台湾、平定蒙古,还亲自带兵征战,知道用兵之道,怎么能把《兵法七经》里的话都用上呢?孟子说仁者无敌,又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天要再编一本书,现在不是编军事大书的时候。……孟子说,可以弄个棍棒来打秦楚两国的铠甲厚、武器利。知道了这个道理,用兵就对了。总之,仁者无敌,这就是王道。与其用计谋、欺骗、胡闹,不如遵循王道,这样敌人不战而败。“王道”两个字是最妙的兵法。自古以来,好胜心强、好斗都不是好事,善战的人只有在时机成熟、形势危急的时候才会动用武力。吴三桂叛乱时,江南徽州属下的一个县叛乱,失败了。鄂楚将军前去征讨。有人给叛军献策,说满族士兵不善于徒步作战,如果诱敌深入稻田,就可以大败。但满族士兵身强体壮,勇猛无比,诱敌士兵还没到稻田就被杀了。献策之人也被我军所杀。凡用“七经”的人,都是这种类型。现在,《七武经》与《论语》、《孟子》该如何区分,请九位大臣商议后汇报。
只有在这里,皇帝才表达了他对正统武科考试课程的彻底蔑视。在其他地方,他都没有提倡将《孟子》作为将军的参考书。皇帝喜欢火器,喜欢优秀的弓箭手,重视勇敢的猎人和有成就的将军,但军事理论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当他想到那些将保卫宫殿并成为绿营军精锐军官的人时,他选择给一部谴责“好战”男子的文学作品。
从来没有一位中国哲学家明确地表示过反战立场。军事冒险最激烈的批评者墨子(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坚持认为惩罚性战争往往是必要的。这与孟子在各种对话中所持的立场很接近。正如历史学家李训祥所指出的,这也接近孙膑(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和其他军事战略家的立场。虽然孟子毫不犹豫地对抗那些不守承诺的统治者——他强烈谴责梁惠王——但《孟子》的编纂者在《孟子》的结尾对战争贩子进行了最严厉的抨击,这大大削弱了“有人说:‘我善于布阵,善于打仗。’这是大罪。”等言论的影响力。孟子的言论有时听起来像是在为战争辩护,但康熙列举了军事开脱的常用方法,最后却说“没有别的办法,就用兵”,这违背了孟子哲学的精神和文字。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他重复了“王道”一词。
在与梁惠王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对话中,孟子描述了统治者对臣民的责任:“王道”一词只出现在这里,其他地方都没有。在解释需要一套规则和条例来保护人民时,孟子巧妙地将一些关于暴力和战争的类比融入到他的论点中——这些类比既与对话者的好战产生共鸣,也揭示了其与不那么明显的杀戮政策的联系。在谈论网眼大的网和砍树的适当季节时,孟子提倡一种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保护方式,这是任何一位勇士国王都无法保证的。臣民愿意为保卫好国王统治的土地而战斗,但不应要求他们放弃家园和财产来扩大领土。孟子对战争的态度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他甚至似乎认为统治者可以正当使用军事力量对付其臣民,但他对战争的主要言论与他的核心信念是一致的,即统治者必须以臣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根据马剑波的奏疏,康熙皇帝下令在武举考试中使用两本主要的儒家经典,该命令出现在《清实录》的末尾:从次年起,直到乾隆皇帝撤销这项改革,每个参加武举、乡试和会试(仅次于进士的两个级别)的考生都必须写一篇大约六百字的文章,回答《孟子》或《论语》中的一小段。虽然科举考生从未被问及兵书,但他们经常被问及如何处理军事问题;他们被要求对剿匪等问题有实际的了解,以及对军事史的学术理解 - 例如,徐和清在 1851 年为科举考试写的政策文章就是一篇探讨军队组建的文章。
康熙帝晚年采取了更大胆的措施来改革武科举制度。他似乎觉得自己在培养儒家将领方面的尝试是成功的:四年后,他打破了传统的文武科举制度之间的界限。通过乡试和会试的考生可以从一条道路转到另一条道路。有些人甚至真的这么做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1710年的戏剧,并暂停一下。当康熙皇帝思考马剑波奏疏中提出的问题,并考虑如何提高武科考生的教育水平时,他最信任的官员李光地(1642-1718)插话说:“让那些习武的人读《左传》就好了。”皇帝粗鲁地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我们会仔细考虑。
多年来,李光地的日常工作就是审阅武举进士的试卷。1688 年、1706 年、1709 年和 1712 年,他担任武举殿试主考官,1691 年担任武举会试主考官,但从他的序言和奏章来看,他对这些考试不感兴趣。他对科举的评价则截然不同,他强烈谴责官员不道德和不明智,他们通过贿赂玷污自己的高位,让不择手段的考生获得文进士的称号;这鼓励了来自福建的雄心勃勃的史学家,他们以李光地的道德正直为荣,建立了一个崇拜他的宗教团体。
虽然李光地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儒家思想的贡献,但他在制定军事政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领导了台湾的平定,甚至涉猎了军事理论——他的《吴起经注》于 1700 年完成。陈其芳指出,李光地主张哲学整合和哲学真理的实际应用,并认为他是吕昆和乔安娜·汉德林在《晚明思想中的行为》中提到的其他学者的追随者。
虽然李光地在1710年武科改革中的作用可能被简要提及,但他与马剑波职业生涯的交集表明,他可能影响了马剑波对科举课程的思考,反之亦然。我认为,李光地作为十九年前的武科主考官,一定知道马剑波的名字,因为在那一年,马剑波通过了会试和殿试,获得了武科进士的称号。
当然,两人大约七年后又见面了,当时他们的事业让他们再次相聚。以下是李光地告诉他弟子的故事,弟子将其记录在李光地的年表中:
公爵任学政时,路过正定,与马剑波交谈,颇为佩服,便提拔他来帮忙。公爵有一次出去巡江,夜宿舟中。二更之时,他穿好衣服,打开舱门,只见舱外坐着一个人,左手拿着弓箭,右手拿着剑,屏气凝神。便朝他大叫,原来是剑波。问他为何,剑波小心翼翼地回答:“你泊在外面,不可懈怠警惕,要防备敌军和中央军。”公爵笑着说:“现在正值太平,有什么好怕的?你整天坐着不动,不累吗!”剑波说:“凡是将领,都要昼夜警惕,如果懒惰怠惰,就会习以为常,怎么能上战场呢!”公爵对他印象十分深刻,多次推荐他。
在这个回顾性的轶事中,马剑波被描述为一个在清军中忠诚而睿智的将领,但他并不摆出一副迂腐的架子。他严肃地提醒他的文官上司,皇帝坚持军事价值观,皇帝坚持满族科举人要表现出射箭和骑马的才能。但马剑波 1710 年的奏疏表明他具有高超的战术技能。奏疏中的第一个建议,包括去孔庙祭拜,可能并不让审阅它的高级文官高兴,但收到奏疏的皇帝曾在二十年前的孔庙祭拜仪式上呼吁军事官员与文官一起参加——马剑波的建议可能是一道开胃菜,以激发皇帝进一步改革的胃口。奏疏中的第二个建议并没有完全让皇帝满意;但李光地本人,尽管担任太傅多年,却没有预见到他学生思想的转变:用《左传》取代或补充军事经典的建议立即被拒绝。
虽然皇帝以自己的战争经验为依据,并坚称自己指挥过几场战役,学到了从孟子那里获得军事建议的重要性,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李光地的观点。李光地死后编纂的《荣存语录》中收录了一篇奇怪的文章,这篇短文中有两点与讨论的事件产生了共鸣。第一点是孟子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位完全不关心军事问题的思想家,但他对战争,特别是战略问题的理解最为深刻;第二点是《孙子兵法》中表达的思想是不能接受的。在第一点中,李光地引用了皇帝提到的一句话,即“可以做一根棍子,打秦楚的坚甲利器”。在第二点中,李光地和皇帝一样,单独批评了“火攻”。他还直言:“若将《左传》、《国策》、《史》、《汉》四书选取起来编纂一部兵书,应比现在所谓的‘七书’要好。”最后他提到了马剑波。
据我所知,李光地遗作没有确切的日期。马剑波死于1720年末,李光地去世两年后皇帝批准了马剑波的提议,也就是他去世八年后。人们想知道这篇文章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前是否存在,但马剑波向他的保护人提出的建议的形式只能在积累更多证据之前进行推测。
清朝时期,无论是文科还是武科,所有省级、会试和殿试的结果都以高度程式化的文本形式记录在翰林院(或紫禁城的殿试厅)中。其中一种记录是《提名录》,它只概述了具体考试的内容,并记录了参加考试和通过考试的人的姓名和职位。另一种更为广泛的记录是《实录》,其中包括序言和后记,主考官在序言和后记中提供了许多考试细节、他对军事和民事问题的看法以及一些成功考生撰写的范文。在许多情况下,清朝的武科记录构成了军事传统学者的唯一书面遗产,他们继续在文武、帝王和平民以及满族和汉族的关键交汇处担任重要职务,为国家服务。
五十年来,《孟子》和《论语》中的散文是武生面临的第一道文学考试题材。最初,这些文本中最明显的段落也被纳入其中。在课程改革后举行的第一次省级军事考试中,福建和云南的考官都提出了关于《论语》中孔子列出政府应提供的东西的著名段落的问题——“粮食充足,士兵充足,民信之”(12.7)。在其他地方,考官要求新晋考生讨论“仁者有勇”。康熙的改革还影响了其他问题,即来自三本官方军事文本(《孙子》、《伍子胥》和《司马法》)的问题,以及自 1064 年以来一直是军事考试标准内容的实际政策问题:前者与传统不同,侧重于与儒家思想产生共鸣的段落,因为它们涉及礼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以及士兵文学素质的重要性;后者引用了《孟子》和《论语》的段落,并要求考生对最近的课程改革发表评论。
虽然没有记载武科主考官之间交流的记录,但从考试中摘录《孟子》和《论语》的篇章来看,武科主考官之间确实存在横向交流的倾向。例如,1711年,福建和云南用的是同一篇《论语》;1726年,山东和顺天也用的是同一篇《论语》;1741年,湖广湖北和江西也用的是同一篇《孟子》。这种现象在摘录武科题目方面也很常见:同年的考试中,有两三个主考官用的是同一篇《孙子》、《吴子》和《司马法》。而同期,其他省份也发布了其他题目,这似乎表明当时并没有来自政治中心的全面命令来决定考试题目。与此同时,康熙皇帝在1710年颁布改革科举的法令后不久,武举考官和考生都明显地关注着康熙皇帝的统治,因此1711年顺天武举主考官吴廷珍和四川武举范文作者韩良清都强调了“王道”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在一段时期内,官方语言带有皇帝严厉批评的烙印。
文科举人必须评论朱熹注释的儒家经典,武科举人通常只需要相当简单和基本的文章就能满意。因此,彭楚才在评论《论语》中的“事君可以专心于身”一文时,只是将统治者和父母对个人身体的主张进行了对比,认为每个人的身体暂时属于统治者,但死后会归还给父母。然而,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一些武科举人的学习变得与文科举人相似。
例如,韩良卿承认朱熹的解释优越性,在1711年四川武举的考试中,他用与宋代思想家《帝王之道》相同的提法来解释经典。同样,石礼在解释《论语》中的“其养民也仁”一文时也使用了与朱熹相同的方法,描述了提问者(子产)的政治背景,并引用了《左传》中的一段话作为他的论点的一部分。李光地也许很高兴看到这部古代史经常被武举人引用:除了考试题目所依据的五部标准经典之外,考生中最受欢迎的问题也被康熙皇帝拒绝,认为不合适。
1759年1月4日,兵部审议通过了主考官葛涛(1751年进士)起草的两份奏章。这并不是乾隆第一次否决其祖父对武举制度的激进改革。
葛涛在叙述了武举笔试(内廷)使用钟声的情况并提出预防措施后,转而谈及另一个问题。“武举乡试……应以武学经典为基础。四书(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义非武学所能理解。”在提交此奏章时,葛涛已担任过两次乡试主考官:1754 年担任江西乡试辅考官,1757 年担任云南乡试主考官。然而,虽然许多主考官连续担任同一年举行的文武考试,但葛涛并非如此,他没有出现在任何相关武举的记录中。然而,这位缺乏经验的官员似乎与皇帝的观点一致,皇帝认为取消《论语》和《孟子》的考试题目会让事情变得更好。葛涛在奏折的最后甚至说:“我们也要挑选那些大致精通上述文学和逻辑的人,让他们通过考试,以表示我们对诚信的尊重。”
康熙皇帝表示需要不同类型的军事学者,已经过去了近五十年,但时代决定了不同的需求。乾隆皇帝发动了一场积极的军事行动,将领土扩大到西藏、新疆和蒙古草原,并对八旗军,特别是绿营军提出了要求。虽然康熙皇帝将军事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分支,并希望时光倒流,让皇帝的顾问既是文人又是武人,但乾隆皇帝接受了孔子、孟子、墨子、孙子等人对“文”和“武”领域的区分。
从十一个月后举行的省试开始,争取高级武功的考生将被要求讨论《孙子》、《吴子》和《司马法》中的段落,但不再需要讨论王道、霸道或孝道。
在本章开头,我提到了王阳明的作品,他是一位严格区分军事和民事事务的文官。但王阳明确实曾将《孟子》纳入军事问题的讨论中: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试图改革军事考试。王阳明认为边疆地区脆弱,国家有责任建立一支拥有超越骑射技能的军队:如果不了解战略,军队将一事无成。因此,在 1499 年,他提出了一种新制度,即与考试挂钩的训练计划,强调军事理论和决策,学生来自精英家庭和明朝军事学院。他坚持训练必须尽快开始。毕竟,孟子自己也说过:“不留人,一生无所获。”
这不是李光地及其君主的言辞或推论,而是这位年轻官员在精心呈交的奏折中,明确地向孟子这位军事圣人致敬。在之后的奏折中,他再也没有说过这样真挚的话。五百年后,那些谈论道德征服却避开国际上对使用暴力的限制的人,也将他们的计划与道德可信度无可置疑的教义联系起来。康熙皇帝在这方面的努力,试图赋予中国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以重大的军事意义,注定要失败。
(本文摘自尼古拉·迪·科斯莫(美国)主编、袁建译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