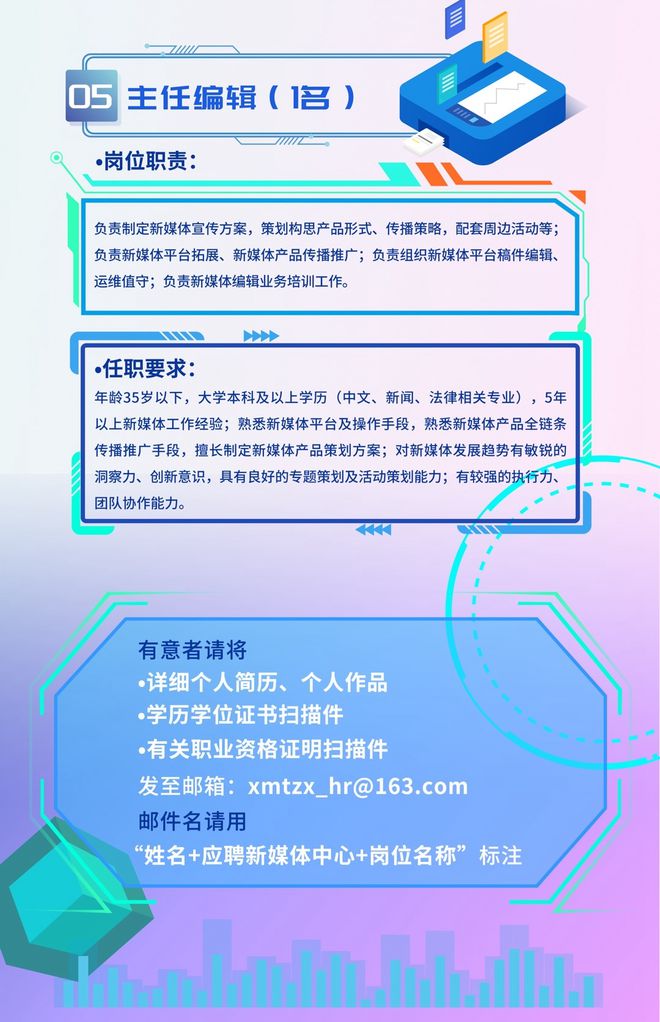作者:朱钰琪(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一
2024年元旦后不久,冯其勇先生的女儿冯友若给她寄来了刚刚完成的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粗布包裹的人生,心中有诗书画——相关书籍》我感叹时光的流逝,冯先生的诞辰已到了一百周年。读着文章字里行间对父亲的深情回忆,我感慨万千,自从1986年在新疆遇见冯先生以来,跟随他走过红庙北里、张家湾、古丝绸之路的场景不断出现。那些清晰具体的片段有时重叠又说不清,我回答她:“其实,我应该做点什么来纪念冯先生的一百周年。我只是还没有头绪。”她还安慰我:“我心里有他,形式不重要!”
冯其庸自作了一首翻越天山的七韵诗。
一年一度的佳辰佳节即将来临。我一大早起床,铺好纸,沾湿笔,想写一些字。我认为这是对春节的纪念。不知不觉中,我想起了冯先生《己卯除夕》中的西语句子“千里流沙来”。茫茫大海,千峰耸昆仑。”写着写着,我突然想到:冯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留下了那么多辛勤的著作,为什么不通过阅读来纪念他呢?从那天起,每天早晚从实验室回到家,我都会拿出一两册《刮饭楼系列》翻看,后来读了他的诗歌作品,受到启发,就临摹了一些。西域诗词表达我的心声这100首《诗歌中的丝路》是冯其庸先生从春到夏的六个月里临摹西方诗歌的痕迹。
记得2019年,也就是冯先生去世两年后,出版了一本纪念冯先生纪念日的文集,书名是《茫茫大海梦迹》。我写了一首诗来纪念:
住茅草屋,春转冬,老梅开红千枝。
夫归来已过数年,茫茫人海中的梦痕,追忆着旧日的痕迹。
人生似乎已被注定。现在,让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是,受冯先生教导的岁月并没有因为天人永隔而中断。在写西洋诗时,他仿佛在“茫茫大海上的梦痕”的指引下走进了西洋大国的山山水水。通过他的作品,我加深了对西方和冯先生的了解。

冯其庸的写意《龟兹山水》墨色浓郁,与他的诗一样,捕捉到了“美丽新疆”的神韵。
二
冯其庸先生自幼就受到司马迁等古代先贤的影响。他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求知之道。 20世纪60年代,他开始踏足关中,开始考察长安以西的古丝绸之路。此后,他又四次来到河西走廊。 1986年,他第一次西行阳关,来到了新疆。他深深地爱上了这片曾被中国经典记载得淋漓尽致、通向世界的西域热土。他沿着玄奘古道西行,十次到访新疆,深入罗布泊、帕米尔等普通游客难以到达的地方,成功完成了对古丝绸之路西段的探寻。这些搜寻的痕迹包括他的绘画、摄影和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下来。而诗歌则是他无数次被西方独特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和人民所感动的文学表现。
虽然我以前读过他的这些诗,并在本书后面的附录中写过一些鉴赏文章,但这次回想起来,仍然有经常读的感觉,让我回味无穷。
比如,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发现西方那些令他感动的自然风景之美,是与他生前旅行时所见所闻相比较的。在这些西方诗歌中,“生命”这个词出现得非常频繁,比如:
一生见过千山万水,唯独没有见过龟兹一朵云。 (《龟兹山水铭》)
生活中不要害怕危险,要从危险中看到精神。 (《攀登帕米尔高原》)
您今天所做的服务是最好的。当有一天我们见面时,我们会谈论我们过去的旅行。 (《游喀纳斯湖》)
我人生的伟大旅程如今已经衰落,我仍想向大鹏学习。 (《季卯除夕谈思想》)
我一生走遍了天山,也曾数次参观过玉皇宫。 (“绘画”)
我一生三次登上昆仑山顶,又去了楼兰纳夫波。 (《对自删文集的反思》)
从他在《风雨人生:冯其庸口述自传》中提到,他自幼喜爱旅游,直到六十一岁才去新疆,打开了新疆的山水画卷。西域地区。那些认知和情感,都是基于六十岁的经历。因此,诗中常常含有“一生”等惊奇或自豪的感情,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他的诗用“天”、“地”、“千”、“万”等词语,将渺小的个体置于无限的时空中,营造出西方山水的宏大意境,如:
灵灵突然觉得天上刮起风来有些奇怪,她感觉自己的身高被白云压低了。 (《麦积山七佛阁铭记》)
历尽千辛万苦才下山。过了万千山峰,只剩下一湾。 (《翻越天山丙大坂》)
万千山峦连绵细荡,孤峰披新银甲突兀。 (《从飞机上看天山博格达峰》)
茫茫人海里有无数的尘埃,人间有许多旧梦的痕迹。 (《自名《沧海尘劫》》)
十年梦想去乌孙,千里迢迢而来,探望祖国将士的英魂。 (《碑文》)
千里之外的荒野里有一个石人,风独立而强大。 (《铭刻草原石人》)
他在战场上直立了一千年,却倒在地上,依然以骑士的身份沉睡。 (《刻在白杨树上》)
如今新疆旅游业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美丽新疆”。冯先生的诗确实捕捉到了这种“大美”的神韵,用那些气势磅礴的词句传达了令他感动的“大美”。
对于他亲身经历的西域山水,他常常毫不犹豫地用笔墨多次表达出来。
如《龟兹》:
看完了龟兹的十万座山峰,才知道这五座山也是平庸的。 (《龟兹山水铭》)
流沙至龟兹千里之外,佛国西何支? (《古克孜尔克孜尔千佛洞之旅》)
离开龟兹已经七年了。当我回来时,我发现风景更加美丽了。 (《9月20日到达龟兹,晚上睡不着,就趴在枕头上看书》)
六次经过龟兹咸水沟,奇峰直插蓝天。 (《龟兹山水铭》)
来到龟兹已经十年了。我跑过云端,落入石头,追忆往事。 (《龟兹山水铭》)
如《昆仑》:
第三次昆仑之行多功劳,最高峰俯瞰华夏。 (《昆仑之巅歌声》)
昆仑之西郁郁葱葱,碧海万朵莲花。 (“绘画”)
万里流沙临沧海,万峰耸立昆仑壁。 (《季卯除夕谈思想》)
当年的豪迈气概尚未褪去,我直奔昆仑求更多的想法。 (“然后”)
如“楼兰”、“天山”、“大漠”、“西域”等,这些创造了不朽史实、造就了丝绸之路上无数英雄的西域地名,蕴藏着历史脉络。在他的笔下,它们气势磅礴,充满感叹。 ,并增添了更多壮丽、英雄的警句。非常难得的是,这些深刻的印象已经深入到了他的记忆深处,像一座座山脊,一座座山峰,以至于他晚年吟唱时,毫无相似之处。

《诗歌中的丝路——冯其庸先生的大西域诗》
冯其庸学术馆编
朱雨绮的书
凤凰出版社
三
使冯先生的西方诗歌丰富多彩的是他的同时代人。以各种方式为祖国边疆做出贡献的西方人士,都成为冯先生的挚友。比如考古学家王秉华,冯先生被这位扎根新疆考古事业的默默耕耘者的精神深深感动,曾主动发诗:
①沧海桑田寻找梦的痕迹,楼兰又见小河码头。君家事业代代相传,英雄辈出,英俊潇洒。
②龙沙是生命,雨、雹、风、霜更重要。冰天不炼骨,怎能雪中红云?
(《献王丙华诗二首》)
这次,我还在冯先生纪念喀什一位普通司机的诗集中找到了这首诗:
老朋友远道而来,却不见踪影。昆仑风雪夜,水流稀。 (《哀马震霞》)
马振霞是冯先生1995年在喀什认识的司机,他曾载我们去帕米尔高原。一路上他话不多,但开车时的责任感极强,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我随冯先生回到喀什。下车后,他问马队长在哪里。没想到几个月前,马队长就不幸去世了。这种深深的痛苦,一直压在冯先生的心上。当晚,他为已故的朋友作了一首诗,以永存他的品格。
在这首诗的下面,有一段长短的引言:
1995年9月,我来到南疆,见到了袁振国、马振霞。我去了塔什库尔干和红其拉甫,振霞陪着我。我说了再见并答应明年再来。第二年,事情对我来说很复杂,今年事情更复杂。但我不能违背老朋友的诺言,所以我决心要回到喀什。虽然路途坎坷,但我终于在8月23日到达了喀什。而后几个月前,振霞因车祸不幸去世。他闻言,悲痛欲绝,遂赠此二十九个十字架,以表哀思。不用古韵,只用口语,就能看到真情。宽唐吉。
长短的引文可以读作一篇感伤的散文。诗中所记载的“思念”,更是像李白的“哭在宣城,好酒在吉叟”,让我们在昆仑之下的雪夜里,看到了冯先生在丝绸之路上的生死交谊。山脉。 。
四
冯先生留下的这些诗词,以其独特的诗句,成为西域山水的锦上添花。 “我西行追寻旧梦,青面锦发远行。” (《从北京飞到乌鲁木齐,见天山博格达峰独立如银柱》)沉浸在冯先生的诗里,仿佛能看到他总是走在那个平凡的地方。走常新古道。今年8月,我重游南疆,发现他的《不如龟兹一朵云》、《看尽龟兹十万峰》等诗句通过不同的载体展现在古老的龟兹山水面前;而他在帕米尔高原上竖立的“玄奘古道从佛经东来”的碑刻也被复制到了游客方便到达的景点,成为了拍照圣地。毫无疑问,他为玄奘英雄西行而写下的优美诗篇,必将被后人西游的人们所铭记。
本书抄写的诗歌主要参考《冯其庸·瓜荠楼诗集》(青岛出版社,2011年)、《瓜荠楼诗集》(青岛出版社,2017年)、《瓜荠楼西域诗笔记》(中华书局)图书公司,2016)每卷收录的诗歌各有不同。另外,诗的年代也略有不同,因此,还需要参照年表重新整理一部完整的《瓜荠楼诗》。
此外,本书还附有一些我三十年来观察冯先生的艺术创作和阅读他的学术著作的经历的文章。如果能帮助读者了解他的学术和生活,将是我最大的荣幸。我曾在《云路居随笔》序言中提到:“冯其庸先生在我去了新疆后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成为我丝绸之路上的向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指导变得越来越重要。痕迹似乎越来越明显。我也会以他的西诗为鞭策,铭记“少年时欲作徐霞客,游西而东”(《改名龟兹山水》)。在丝绸之路研究的漫漫道路上,冯先生沿着未竟的道路不断前行。
《光明日报》(2024年12月26日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