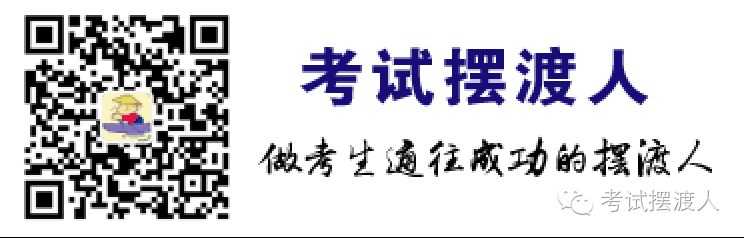近年来,作家张艺伟先后出版了小说集《四合如意》和《丧眠》。
这两本书都是对世界的探索,但关注的是不同的概念空间:《四合如意》以手机、瞬间、VR、人造人偶等机器为媒介,阐明人性的冲突和世界的复杂性,而《睡眠》则关注女性在城市、侨民和家庭内外的生活状况, 探索家庭的意义和当代青年的生存坐标。
在从“四合如意”到“沉睡”的写作中,张艺渥逐渐构建了一个与当代生活对话的新奇世界。在她的笔下,社交媒体下的人际关系、二次元人的生存方式、老年的状况、对婚姻的思考、移民的命运,甚至是最微妙的友谊结局,都呈现出新的面貌和轮廓。
10月27日,张译渥小说《四合如意》和《哀睡》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会议以“突围日常”为主题,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洪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王昌盖主持。

张艺伟参加了关于小说《四合如意》和《睡眠》的研讨会。
个人生命的秘密法则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平金认为,张艺桅小说中关注的老人、绝症患者和寡居孤独的人,是非常生动的人,有着无尽的思绪和思绪,代际、世代、性别之间的力量相互搏斗,所呈现的声音和观点相对复杂。
《小说世界》杂志主编乔小华注意到,张艺伟笔下的那种家庭生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或理想的家庭生活。她小说中的母女关系、父女关系,甚至包括闺蜜、恋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我们一般印象中的存在。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叶紫表示,张艺薇的女性故事探讨了在更大的世界和更多样化的叙事类型中,情感深度和身份的复杂性,她在理解和故事之间建立了丰富的关系。
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王玉萌认为,在张艺渥的小说中,家庭其实是一种背景和场景,个体是连接整个社会的最小、最重要的家庭单位。她的故事中很少有超过两代人的故事,有我们称之为正常、温暖的非常稳定的家庭关系,而年轻一代在她的文字中对家庭生活的戏仿,绝对捍卫自己的个人空间,废除他人的凝视,这反映出与上一代作家不同的观念。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刘欣悦表示,自《最优之宴》以来,张译伟小说的变化将来自一种个人的危机和焦虑,像涟漪一样推动更多以前未被关心、被系统性忽视的个体生活秘密的规律, 比如短篇小说《免疫风暴》,就提到了脱发药的发展与孕妇和老年人的关系。

《四合如意》的封面。
“打破日常”,引起共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科学部主任顾小青注意到,张艺伟近年来的关注和自我迭代,通过细腻而平静的日常描述,充分呈现了个体身份和社会流动中的文化张力。
南京师范大学文文学学院副教授朱静表示,张义伟笔下的工人新村虽然衰落,但在追忆的精神之光下却焕发了生机和烟火,而《海》的日出则讲述了中国最前沿城市的故事,它捕捉了从地平线跳出的“机器时代”, 新青年的生活逐渐展开。

暨南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唐士仁认为,张艺伟小说“冲出日常”,包括惊喜、痛苦的文学野心,以及如何让个体化的日常生活与时代和社会现实相联系。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詹玉冰看来,张艺渥的小说想冲出我们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想要捕捉的日常生活。传统现实主义所捕捉的日常生活,其实与我们现在生活的日常生活脱节,但正如詹姆逊在《未来的考古学》中提到的,或许在现实主义的退化之后,科幻小说可以感受到一种日常。“她的小说《杜乔》中讨论的表情符号或弹幕文化如何塑造我们对表达的理解,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优秀文学所能提供的共鸣。”
《青年文学》杂志主编张静提到,文坛一直处于对都市文学不满的状态,张译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我们对都市文学的期待。
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编李然认为,张艺伟具有超越自身经验的分析能力,会带着读者丰富和刷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能给读者一种安静的平静力量。
上海文艺出版社主编胡锡路表示,从散文开始,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张艺桅小说的情节为什么会设定下来。从张艺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存在着丰富的感情。

《Sleep》的封面。
重塑现实的意图和力量
张义伟也在复旦大学任教。《长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斌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艺斌“仿佛要离开”了学术界和文坛。张艺伟有着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外表,但实际上,她的思想最终出现仍然是虚构的,而不是理性的。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尹洁认为,张艺伟小说所代表的生活世界里有一些哲学元素,这可能与她自身的哲学背景有关。除了抵制生活的平庸之外,讲故事本身当然具有重塑现实的意图和力量。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力说,当我们分析当今年轻人的状况和性格时,我们尤其失去了一种向外提问的习惯,不考虑历史、政治、结构和制度等原因,例如问“这一切将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生”。他特别关注张艺伟对《西游记》的研究,“她内心是一个像孙悟空一样的角色。
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夏伟认为,张艺伟真正的成就有两件事,一是从历史中看恐怖,二是从恐怖中看现代,甚至构成了自尊和骄傲的辛酸。
《上海文学》杂志社副主编赖英燕认为,在这两本新书中,张艺薇的叙述差距拉大了,她的处境转换更加自由,节奏也更加轻松。以至于在她的这个虚空中有一种流动的秩序,使生活成为一种命运,也许还为恐怖或幽默腾出了空间。
《文艺日报》副主编岳温认为,每个作家都会形成自己的人格,这种人格由她的写作构成,也是在与读者的勾结博弈中形成的。
如果要概括这个作家的形象,张艺伟就是用阴暗的女性视角,有时甚至是老妇人的眼光,反映一种女性的处境。如何避免理性的压倒和情感对理性的掠夺呢?她的小说如何开启新游戏?或许这就是张艺伟需要不断思考的,也是我们需要一起寻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