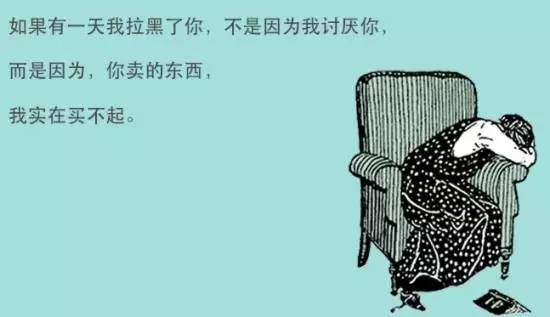惠娃,原名李昭,1927年出生于陕西临潼秦川中部一个绿树成荫、泉水充足的村庄。在他还没有记事的时候,他就跟随父母来到了古都长安。父亲在中学任教,母亲在中学任教。 1931年,他进入陕西省西安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到六年级。抗战爆发后,惠娃一家搬到了一个村庄。 1939年,他被姐姐和表弟送到距西安百里的地方暂住,进入“延安儿童艺术学院”学习音乐和戏剧。新的人生征程,那时的延安不仅是战争的大后方,也是文化艺术的“大后方”。惠娃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文化艺术影响。1946年,惠娃与作战参谋吴兆峰结婚。 1948年,她因患肺结核,到南京治疗。 1951年,她被转到北京西山疗养院。同年,丈夫吴兆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1955年,惠娃身体康复,考入北京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系。 1960年分配到北京编译出版社任编辑,后因病提前退休。 1964年,与开国少将、战争史专家白白结婚。这段婚姻一直持续到1974年白白病逝。1966年“文革”开始后,惠娃陷入精神分裂症,一病就是六年。

灰宝宝
1972年,据医生称,灰宝宝已康复。然而,外人无法真正“探究”她内心深处的恐惧、怀疑、怨恨、绝望和苍凉。于是,她试图通过写诗来排解自己的悲伤,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个出口。起初她对自己写下的“东西”感到惊慌,暗暗猜测有人会用某种新武器来探知她诗歌的秘密。她常常把刚写完的诗撕碎扔进厕所冲水。这种写撕的状态直到张鼎发现才停止。张鼎是惠娃就读延安儿童艺术学院时的美术导师。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同居北京,往来频繁。他迅速而敏锐地捕捉到了惠娃的诗意才华和灵性,建议她把心中的美好放进心里。写下你的感受,用诗歌作为美的宣泄口。受到鼓励,惠娃把自己写的诗放进铁盒子里,埋在花盆下。直到1977年春天,她才敢拿出诗稿给别人看。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诗歌有《大地之母》、《无题》、《心脏病》、《路》、《嗯》、《当我死时……》、《大地之下沉睡——》、 《墓碑》、《额头上绿枝绿叶》……《没有玫瑰》《只有一只鸟还在歌唱》《我该如何分辨》《电动儿童》《童声》 《九月十二》《鸽子与钢琴已憔悴》《穿越深渊的废墟》等
惠娃曾说过:“我所有的话语都是我生命的热度和情感体验的表达。”惠娃开始写诗时已经45岁了。此前他几乎没有任何写作经验,但当他20岁的时候,她能够通过诗歌释放内心的焦虑,摆脱精神危机,获得灵魂的自我救赎。此后,慧娃在诗歌创作事业上坚定不移地奋进,持续创作的热情尚未耗尽。每首诗的创作都给她带来“心灵洗礼的灵感和震撼”,正如她在2020年创作的诗一样。《心伤香》诗中写道:“难得的日子,如相思鸟”。 / 躲在花开的静影里 / 与自己聊天回忆往事,每晚走进黑暗 / 侵蚀人与灵魂记忆的噩梦 / 被污名被人性随时间毁灭/感谢宇宙之神赐予我靠近上帝的本性/废墟中低低流淌着与天使独处的忧郁哀歌/夜莺与水仙的歌声,使者傍晚薄雾中的上帝/神秘、空灵、在天空深处闪烁、振荡/你听到心灵洗礼的震撼灵感了吗?”当遭遇命运的坎坷时,她“逆风而行,带着觉醒的激情”(《琐碎无名的思念》),及时记录下每一次“短暂的诗意经历”(《带着伤痕的芬芳》)。灵魂”)。她告诫别人,也告诫自己,“梦想破灭的人,不要虚度年华。” “听完自由之歌,万灵之泉消失又出现/隔着小溪的余味悠扬飘忽/星星的火花也在蔓延它的火焰”(《拥抱》《故乡病》),或者选择“像神一样,穿越冰冷的蓝光/沉浸在迷迭香的神秘芬芳中/默默地聆听自己的良心说话”(《愿缘仍见证》)。 “我的最初的梦想,我依然爱/我的星星,照耀我的第一道光/唤醒我的牵挂,我的依恋/我的爱与痛,我的恐惧与惊喜……”(《绿色天堂》)慧娃的人生经历充满传奇色彩。如果说她的前半生是站在信风中/喂食沉默无花的果实,那么她的后半生就是“编织骑马而来的春光/整个大地”。万物皆相通”(《山》)。她的诗歌不仅“可以被视为她的‘一个人的灵魂的历史’”,而且在当代诗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研究考察她的诗歌创作历程无疑具有文学史意义。
慧娃的个人经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延安时期的童年生活;精神分裂症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成为新时代张鼎的搭档;张鼎去世至今。惠娃自“文革”后期以来一直从事诗歌创作。她人生各个阶段的诗歌创作,正如她在2019年写的诗《怀旧》中所说,“生命的密码已被编织成多彩而漫长的日子/刻在我的心里”。继续,写在歌里。”
时代症状:“我的太阳穴和额头布满了星星”
许娃1966年患上精神分裂症,20世纪70年代,他在病痛的折磨下不由自主地开始了写作生涯。在此之前,惠娃几乎没有写作经验。最初,诗歌创作是她释放内心焦虑的一个出口,也是治疗疾病不可或缺的“良药”。因为诗歌,她得以在虚幻的世界中找到心灵的寄托,最终奇迹般地从精神分裂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她的诗歌给读者带来了心灵的洗礼和美的享受。荣格将“艺术创作方法分为心理的和幻觉的”。 “心理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寻找素材,因此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而幻觉艺术则取材于隐藏在无意识深处的人类意识领域。”他是一位在原始图像中寻找素材、背离现实、面对自我的艺术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惠娃的诗歌创作属于幻象艺术,她是一位典型的“背离现实”的诗人。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个人主体性回归的创作范例。
慧娃青少年时期经历了残酷战争的洗礼,也接受了红色革命的教育。从她的成长经历来看,她应该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投入到新的学习和工作中。但真正开始工作后,她发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当时的大环境格格不入。进入城市后,慧娃发现周围的环境和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实的力量对于从小就喜欢对着星星和银河唱歌,睡在自己种下的花草旁边的慧娃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践踏。她无法从根本上接受虚假的“现实”。
社会现实让格雷娃感到困惑,她的单纯、敏感、专一也让一些人难以理解和接受。日复一日,紧张终于难以忍受,惠娃陷入了精神分裂。 “文革”开始后,她越来越难以忍受抑郁。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她忍不住把自己积累的感情写下来。格雷沃患病的根源可以从荣格对精神病人的分析中找到:“精神病理学告诉我们,有一种精神障碍,是从病人使自己脱离现实,越来越深地陷入个人幻想中开始的。”结果,现实力量的丧失,导致了内心世界的决断性增长。矛盾时常与她敏感的心灵发生碰撞。最终,这些情感借助诗歌得以表达,诗人心中积攒的忧郁、混乱的思绪得到了清理和释放,焦灼、忧虑的心灵在诗歌的世界里找到了暂时的平静。
惠娃从小就“想着两件事:旅行和作曲。他通过管弦乐来表达心灵对世界的奇妙理解。在他的幻想中,他应该很穷,买不起蜡烛,坐着月光下的屋顶上的编织音乐”,这样的浪漫理想只属于纯洁而美好的灵魂,她始终以一颗朴素的心捍卫着世界的“真”与“美”:
我的太阳穴和额头布满了星星
我用沙哑的声音呼喊着我善良的心
即使世界上没有任何感觉或反应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 “墓碑”
诗人无法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无限悲伤和委屈,只好转身,面对黑暗,独自面对路上的黑暗:“我生来不幸,经历过毒箭的重压/与我背靠悬崖,独自奋战”(《墓碑》)。无论是被毒箭重伤,还是被曾经的信仰欺骗、抛弃,诗人都陷入了孤独的绝境。现实生活中,生命被禁锢,精神无法自由,对美的追求无法实现。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反差促使惠娃拿起了笔。诗歌成为精神的避难所,抚慰苦难的心灵。
“生命力被压抑而产生的苦恼和烦恼,才是文学艺术的根基……”尽管“文革”时期的许多诗人都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但像惠娃这样的人,却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拿起了诗歌,为自己的生活寻找出口。灵魂。走上自我救赎之路的创作行为尤为独特。这些文本为当代诗歌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也开辟了女性诗歌创作的新面貌。
诗神的祝福:“我们在人间摇摇欲坠,拥抱苦难”
惠娃在开始写诗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写作经验。当她的忧郁、压抑无法消除时,她开始随意涂鸦,从一个字,到一个短句、一段、一首诗……并逐渐积累,直到后来编撰出版。这也是为什么惠娃被视为“自学”下的“业余诗人”的原因。荣格曾经解释过艺术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艺术是一种自然的力量,它抓住人并使他成为工具。艺术家不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寻求实现个人目的的人,而是一个让艺术实现其个人目的的人。”艺术的目的是通过自己实现的。”惠娃是一个被诗神“抓住”的人。她有意识地、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过程:“有时候,在我的心里,有一种旋律和节奏,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萦绕在我的心里。无论我去哪里,做什么,这首音乐永远在我的心里。”音乐坚持占据心灵,控制心灵,此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在这种音乐的催促下,以人们称之为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修改的”惠娃的诗不拘一格,充满神秘魅力,处处显露出他的诗意才华。
纵观中外女诗人的创作历程,诗歌总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茨维塔耶娃18岁时自费出版了诗集《暮光专辑》。阿赫玛托娃23岁时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黄昏》,冰心上大学时,她编印了短篇诗集《星星》《泉水》……古今中外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都自觉地年轻时以诗练诗,文风在创作中逐渐成熟。慧娃则不同。她中年开始诗歌创作,自始至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风格。也就是说,她写诗时,先形成诗的旋律或节奏,然后跟随它们,然后将诗情或诗意付诸笔下。诚然,与许多当代女诗人相比,惠娃并不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因为她的每一首诗都来自她的灵魂深处。只有心灵被触动,她才能开始写作,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从未去过的世界。奇怪的情况。
灰宝宝天生的敏感和细腻,注定了她孤独而孤独,这让她一度成为了常人眼中的“他者”。她曾在诗中暗示自己无法与世界沟通:“据说我们的怀抱热切地相爱/我们摇摇晃晃地周游世界,拥抱苦难/路人都注视着这巨大的悲剧/和这隐藏的秘密”。他们笑着聊天时感到痛苦”(“路”)。
诗人看到了生活中叠加的虚假和谎言,心中充满了不能向世人倾诉的委屈和“隐退”。一颗本真的质朴的心被沉重的孤独和无聊所笼罩,所以有诗“我们摇摇欲坠的世界拥抱苦难”。但正是这种“孤独与孤独,对外有助于观察沉思,更深入、更冷静地观察社会;对内则有助于反思自我,充分认识生活,凝聚心灵的活力”,使诗人有对自己有深刻的认识。曾经坚守的信念,让我对现实、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缪斯女神选择了灰婴,并将灰婴引入了诗歌的育婴室。就像一粒种子遇到了阳光和土壤,就像一汪泉水找到了出口,诗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渠道,将心中积攒的焦虑和各种美好倾诉出来。她依靠精神直觉渗透到作品深处,探索分裂的自我和复杂的情感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对内心幻想的正视和处理,也是她对自己人生的反思。
结论
惠娃的独特性是不可复制的,她的诗歌风格在当代诗坛极具标志性。他的诗风既奇特又含蓄,他的审美既古典又现代,他的诗篇既清晰又神秘,他的思想既朴素又丰富,他的感情既奇特又灵性,又充满人性烟火,他的艺术表现手法既浪漫又超凡,他的语言既凝重、苦涩,又纯洁美好,想象力既奔放又充满野性。她因病而写诗,也因诗而从精神疾病中走出来,变得更有活力。她的诗歌创作可以看作是对权力话语控制和自我对待的反抗。在这种“治疗”中,她创造了一个完全个性化的诗歌话语体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九十高龄仍坚持诗歌创作,诗歌题材、意象、风格、表现力都有新的变化。从小到大,惠娃“心里只有一个词——美”。四十多年来的创作,她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诗歌观,创造了神秘而美妙的人生境界。惠娃的诗直率,具有迷惑人心、自救精神的力量。她为女性诗歌提供了新的精神资源。

本文节选自《漂流到远海:中国妇女诗歌史(当代卷)》(孙晓雅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