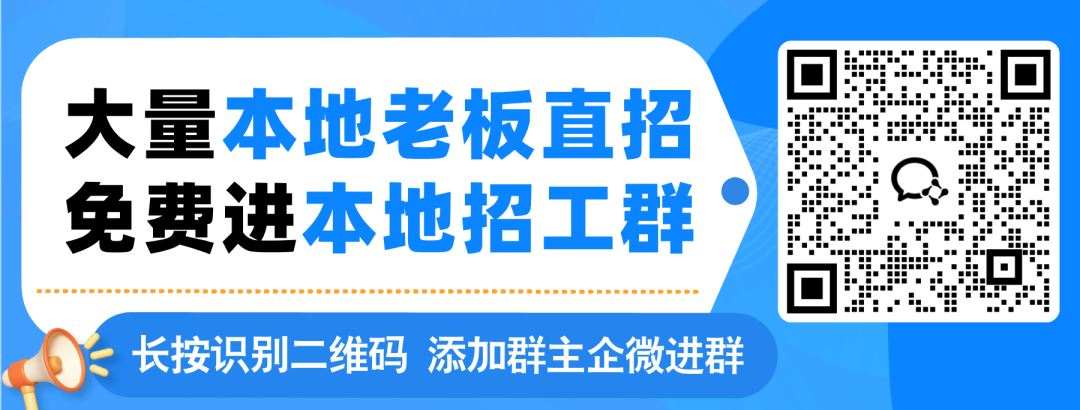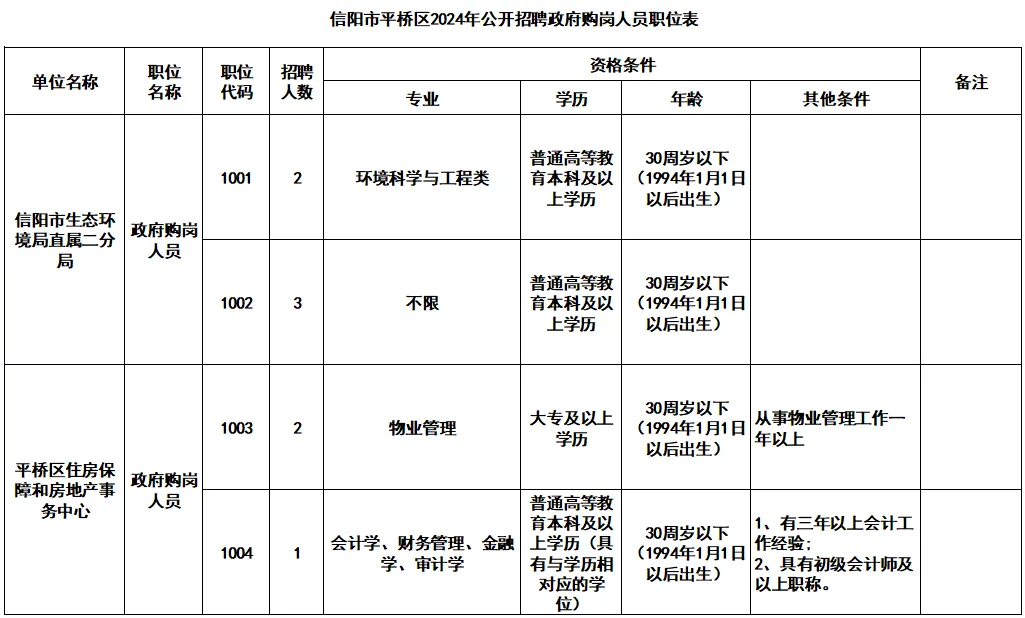史长生是我儿时在故乡溆浦小城一条街上长大的伙伴。从土话来讲,就是“一起在泥巴堆里长大的”。我记得他家是为了“躲避日本侵略者”从宝庆(邵阳)逃到这里来的,他家就安在商会会长向瑞龄家的对面。向瑞龄是女革命家向警予的父亲,他的故居到现在都保存得很完好。当年院门常常是开着的。在橘熟的时节,我们这些伢儿经常可以随意进入园子去“偷”橘子吃。如今,院内那几棵老橘树大概已经开花了……这些童年的往事,在史长生的诗里有很多记载,这或许就是我读他的诗集能够意趣盎然的原因吧。
诗集名为“鬼妹子”,这是当地人给姑娘起的昵称。在我们那里,“鬼”这个字多少蕴含着一些嗔怪和疼爱的意味,就像屈原的《山鬼》那样。现在我们来看看史长生是如何用采桑子新韵来创作《鬼妹子》的:
“朝红晚绿轻纱绕
绛唇轻描
眉发弯俏
神彩飞扬落吊桥,
清纯淑女花沾露
姐也苗条
妹也苗条
媚甩骚舞醉魂销。”
我对古韵并不了解,所以不便在此对他的新韵进行评判。我只能从诗的角度来谈论诗,从词的角度来谈论词。感觉上,作者像是拥有了《山鬼》的神韵,像是要创作一个“山鬼”的翻版。而我对他知根知底,能看出他似乎是在写故乡辰河戏团中饰演“山鬼”的一对姊妹。因为当年的辰河戏园子就在他家旁边,并且他还在剧团里当过乐手。这个词的辞采很飘逸,情思也很飘逸,虽然没有太多新意,但却较为真切地表达了内心的情感,很有一点“文气”。
溆浦是我俩的故乡,此地自古“文气”就很旺盛。它一方面得益于以屈原为代表的历代骚人墨客的熏染,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后现代文人的推举与抬爱。大作家沈从文以写湘西著称,他也承认溆浦“文化水准特别高”。写了《围城》的钱钟书与父亲钱基博从湘西蓝田辗转来到溆浦陈家垴的“三闾书院”落脚,他们对当地的“文气”也有很多赞语。出生于溆浦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很有文才,很早就出版了与蔡和森恋爱的赠诗集,并且得到过毛泽东的赞誉。第一任《辞海》主编舒新城是溆浦人,史学家向达是溆浦人,以方言注释《楚辞》的陈抡是溆浦人,直至以小说《国画》脱颖而出而惊动文坛的王跃文也是溆浦人……我必须承认,自己与文学的结缘,是得益于故乡的“文气”的。史长生也不例外,都是溆浦“文气”的受益者。他有一首现代诗《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其中写道: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唱这首歌。在唱着唱着的过程中,我们自己变成了爸爸妈妈。继续唱着唱着,爸爸妈妈离开了我们。再唱着唱着,我们自己也老了。月亮依然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依然在,晚风也依然在。然而,他们——我们的孩子,却不会再坐在我们的身边,听我们讲过去的故事了。他们都很忙碌,对我们过去的事情不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听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他们要关心自己的饭碗,关心自己的升迁,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子女……接着,作者在诗中描述了我们共同经历过的“替人占位、排队买菜”这样的小城平民生活……
他察觉到“孩子们不听”这件事,将其当作“天方夜谭”。接着,“我们只得把那些话说给自己听,说给当年的小伙伴听,并非是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在说着的过程中,“女人们流下了眼泪,男人们也开始抽泣起来……”。最终,作者感慨起来——“想到自己那如花朵般的岁月,竟然就这么悄然流逝了……”
诗初看有些“口水诗”之感,读起来却能深深触动人心,引发某种情感的共振。实际上,诗达到这样的程度,就已经足够了,也具备了一定的品位。这里存在一个关于如何看待诗的语言的问题。
老作家徐怀中在一次跟我谈论“诗的语言”时,说过一句极为经典的话:“语言如同作家诗人的内分泌……”此言不虚。我所理解的他所说的“语言”,并非指普通的词汇和句式,而是凝聚了作家诗人整体素质的那种“文气”。史长生的这首诗,从表面上看是在平平淡淡地叙述,既没有采桑子《鬼妹子》那般的华丽,也没有那种绮靡之感,但却不乏立意方面的内蕴以及深沉之处,很有“文气”。马克思称“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史长生作为“乡党”,对其奥义深有体会。我们虽在同一地面成长,但人生经历和结局各异,都沾染了故乡的“文气”,痴迷于“文章之事”,却未领悟“簪组万年终长物,文章千古亦虚名”,看不透“红尘”,难道也是被故乡“文气”所误?故乡有句老话讲“文章不能当饭吃”,诗更是如此。我们却为“千古文章事”而不懈地去探寻,这是为什么呢?这里,可以用一个字来回答——“净”!意思就是在纷繁的尘世里,去寻找一种能够与自然和心灵交流的途径,从古今贤人的典籍中获取力量,以求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这或许是自我和解、自我救赎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到了晚年,也就是人生的后半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与其抱怨上天和他人,不如向苏东坡学习,把原本“苦”的日子过得“甜”起来。当然,这里所说的“苦”与“甜”是相对的,完全凭借内心的价值尺度来进行衡量。简单来说,就是让自己多一些“文气”,少一些“戾气”,做到“净”。希望能用这质朴的乡情之语与史长生先生相互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