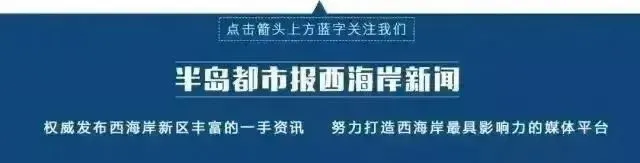一位名人曾说:“世界虽乱,但书桌不乱。”然而我的书桌却是乱的,书桌周围更是杂乱无章。正因如此,在年前我稍微对书桌进行了整理。我把一年来随手放置的读者来信收集起来并捆在一起,而最近新来的读者来信则留在了案头。
1989 年开始有读者来信。因为在初版《挪威的森林》译序最后留了“广州市石牌·暨南大学外语系”的通信地址。所以几乎每天都有读者来信埋伏在系办公室信箱里等我。上个世纪末调来青岛后,信就跟我来到了青岛。2003 年那次让我记忆深刻。我赴日一年后回到学院办公室,院办主任指着一个大纸箱对我说“你的信”。然后我看到满满一箱子信在墙角静静地等着我归来。
三十五年转瞬即逝。究竟有多少封呢?一摞摞的,一堆堆的,肯定有几千封。说来颇为奇怪,大家都说高三是人生最为紧张的阶段,然而在来信当中,以高三生居多。其次是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白领”等年轻人。有的感慨村上春树的作品引领自己从青春的沼泽中走出;有的透露自己的孤独,“在偌大房间里只找到了自己”;有的称赞“爱你的翻译就如同爱初恋的对象”;有的纠正我的误译,将“比齐·鲍易斯”(Beach Boys)改成“沙滩男孩”……当我在夜晚温馨的台灯光下拂去脸上的粉笔灰,看着那些信时,信笺上常常浮现出一张张如花般的笑脸,跳动着一颗颗如水晶般的心——那无疑是我一天中最为美妙的时刻,我因此忘却了诸多烦恼和忧伤,也因此保持了与年龄不相称的不息的青春激情。


近年来网上联系增多,导致来信日益减少,但还是需要隔些天去收发室集中取一次信。此刻我在翻阅刚才放在案头的信,其中有一封来自武汉读者的信格外引起我的注意,信中表达的是对《挪威的森林》的读后感,信中写道:“这是一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的爱,在灵与肉之间游荡的美,飘散在心头的泪。”写信的是一位男中学生。他接着说八年级那年遇到了一个有抑郁症倾向的女孩。女孩的父母离异后,她跟父亲一起生活。她的父亲对她很严厉,经常打骂她。而他自己当时也正处在一种精神旋涡里。女孩的不幸使他产生了类似渡边君那样的感情,即“两个在黑暗中生活的人相互拯救”。后来他察觉到女孩有男朋友,并且一直对自己隐瞒着。正如渡边君所说:“她压根就没爱过我。”这自然使他内心感到痛苦。然而,最终他还是从中摆脱了出来。有时候,青春所经历的苦涩,恰恰是青春激昂的歌声。在冬日的午后回忆起来,那段经历就如同敢死队送给渡边君的萤火虫那般,一闪一闪的,十分美丽动人……
信的篇幅很长,足足有两页纸,且写得密密麻麻。这个男孩有着很浓厚的文学感觉,心地也很善良。同时,他的这些特质让我心中有些伤感。为了冲淡或者确认这种伤感,我拿起了村上的书,然后在书上找到了萤火虫。

村上有一部名为《萤》的短篇,它是长篇《挪威的森林》的最初模样。在萤火虫描写方面,这两篇几乎没有差别。
萤火虫过了很久才起身飞离。它像是忽然有所领悟,猛地张开翅膀,随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开始在黑暗中滑动。它绕着水塔快速地拖着光环,仿佛想要挽回失去的时光……那微弱浅淡的光点,就好像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来回徘徊。
我朝夜幕伸出了几次手,指尖在夜幕中什么也没触到。那小小的光点总是与指尖保持着一段细微的、无法触及的距离。


可以得知,萤火虫象征着直子抑郁的精神状况。那“小小的光点”与指尖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距离,这无疑在暗示“我”与直子恋爱关系的走向和结局。
合上书后,再次看向那位八年级中学生的信。在看着的过程中,突然想起了半个多世纪前自己也是八年级的时候,也想起了东北乡下那间茅草屋窗前的萤火虫。萤火虫从附近西山坡的荒草中飞来,有的纷纷扬扬,有的星星点点。它们飞进了满是黄瓜架和豆角架的菜园,接着又飞进了隔一道木篱笆的院子。在窗前不紧不慢地往来盘旋,仿佛在苦苦地寻求着什么。它们飘飘忽忽,闪闪烁烁,时而贴着窗玻璃连闪几下。注视着它们,不由得让人想起班上一个女生眨闪的眼睛,此刻那对眼睛是不是也在看萤火虫呢?

八年级,八年级男生,一个微妙的年龄。
一千多年前是杜牧写下了“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的诗。天上有那么多星星,然而杜牧却偏偏要看牵牛星和织女星。“疏篁一径,流萤几点,飞来又去”,在一代情种柳永的词中,萤火虫更能让人产生幽思缠绵的情感。难道自古以来萤火虫就与男女之爱存在着某种关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