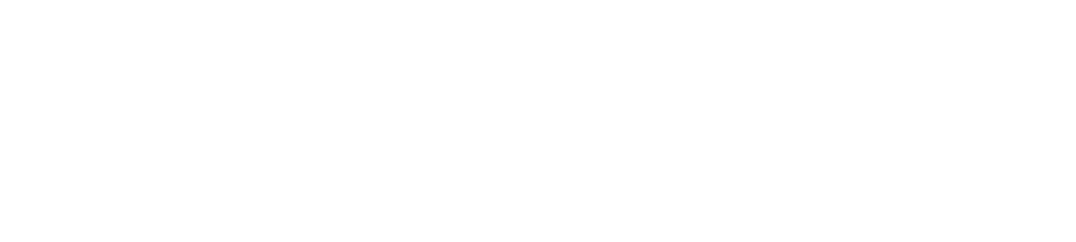南宋诗人杨万里开创了“诚斋体”诗歌,此诗歌独具特色。在中国诗歌史上,“诚斋体”诗歌有着较大的影响。他的诗以清新自然为特点,也很活泼灵动。多运用口语、俗语入诗,语言浅白如同说话一般,充满了生活气息,例如《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等。而他还有些诗是以说理为主,情感较少,能反映出诗人对宇宙人生的理解,《夏夜玩月》便是这样的一首诗。
《夏夜玩月》
宋·杨万里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
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
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
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
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
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
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中国的很多文人骨子里蕴含着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基因。在南宋时期,杨万里生活于此,当时程朱理学极为发达,并且他本人还与朱熹有过交往,所以他也受到了理学的影响。自唐代禅宗在世间广泛流行之后,大部分中国文人都能够谈论禅理。然而,杨万里的思想具有很大的自主性,他的诗歌始终将文学性和生活性作为创作的核心。他有不少说理诗。这些说理诗并不直接去阐发义理。而是把哲理融入到生动活泼的景物意象里面。
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论诗说道:“诗具有别样的趣味,并非与理相关。”他说出这样的话,是在反对宋代诗歌过度进行说理的倾向。诗歌通常是以抒发情感为主的,然而并非不能阐述道理,关键之处在于说理要有“理趣”。钱钟书在《谈艺录》(六十九)里谈论诗歌的理趣时指出:“至于理趣呢,就是理蕴含在事物之中,事物包含着理在内,事物秉承着理而形成,理因事物而彰显。用事物来赋予道理,不是选取相近的事物来作比喻,而是列举事例来概括。”我们来看杨万里的《夏夜玩月》诗,它颇符合这样的特点。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首诗的理趣,我们试着从理学、禅宗以及西方现象学的视角来解析此诗。
《夏夜玩月》诗的前四句为: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

前面四句的表达如同口语,乍一看平平常常。实际上,它是借助月、我、影这三者的关系,把本体与现象的哲理揭示了出来。以月、我、影的关系当作基本意象,前人在诗歌文章里已经有过运用。在庄子的《齐物论》中,是通过“罔两”与影子的对话,来探讨自由的问题。东晋的陶渊明创作了《形影神》(影答形)这首诗,其中写道:“与子相遇以来,未曾有过不同的悲喜。在树荫下休息时仿佛暂时分别,而在白天停留时终究不会分离。”“此同难以长久,悄然一同泯灭。”诗中“影”与“形”进行对话,意思是“形”和“影”悲喜与共,即便在树荫下暂时分离,在阳光下也始终相伴,然而这种形影不离并非长久之事,因为“形”终究会消亡,“影”也会随之消逝。诗歌的主题与当时神灭与不灭的话题相关,富有哲理趣味。李白《月下独酌》有诗句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作者邀明月和影子共饮,以此来衬托孤独。北宋梅尧臣在《月下怀裴如晦宋中道》中写道:“此时引发我的情怀,我在月底看着自己的影子行走。唯有影子和月光,它们的举止没有猜疑和毁谤。”诗人在月下徘徊,望着自己的影子,认为只有影子和月光不会对自己有猜疑和毁谤,并且通过人与影的关系,衬托出世间人心的险恶。苏轼在《后赤壁赋》中有“人影在地,仰见明月”这样独特的描述。杨诗对这些典故进行了借用,并且以口语的形式进行了重构。杨万里在写诗时很擅长化用俗语,他觉得对于俗语需要进行点化,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诗本来有以俗为雅的情况,然而也必须经过前辈的熔化,才可以继承。”(见于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这也是江西诗派“点铁成金”的观点。
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
前人已通过月、我与影表达过哲理。然而,杨万里在此处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哲理,开始讨论我与影到底是一还是二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禅宗经常讨论的话题,就如《坛经》中所说:“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
“月能写我影?”这两句的意思是,在漆黑的夜晚,月光有照亮世界并让万物留下影子的能力,然而月亮能否照见自身呢?就像眼睛能够看见外部世界却看不到自己一样,月亮是不是也这样呢?在生活里,我们凭借着持续地学习,逐步地认识外在世界,却往往无法反观自我,去认识自己。这与古希腊人“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在道理上是相似的。

偶然行走在溪旁,月亮却在溪水中。上面一轮月,下面一轮月,哪个是真正的月亮呢?是水成为了天,还是天成为了水呢?
偶然行至溪旁,却见月亮在溪水中。溪边漫步,这暗示着路径和视域发生了转换,于是便发现溪中也有一轮明月。“水月”在禅宗和理学里属于经典象征,在禅宗方面,有“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月万里天”等表述;在理学方面,有“一月照万川,万川总一月”等表述。前者以天上月来象征清净佛性,以水中月来象征人人都具备佛性;后者以天上月来象征“理”,以水中月来象征“气”以及万物,以此体现“理在气中”“理一分殊”的哲理,正如同邵雍所说的“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二者均能够反映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杨万里又进一步进行了追问:
“上下两轮月,哪个是真实的呢?”这里已然不只是本体与现象的问题啦,而是开始进一步探讨真幻的问题啦。通常人们都觉得天上的月是真实存在的,而水中的月是天上月的倒影,是虚幻的呢,就如同庄子《齐物论》里做梦的人把梦中的事当作真实的,醒来后才发觉那只是一场大梦,又怎么知道其实清醒的时候也如同在梦中呢。白居易《读禅经》中有诗句说:“必须要知道各种表象都不是真实的表象,如果执着于没有多余的东西却反而有了多余的东西。”“言下忘言,可一时了却;梦中说梦,便两重虚妄。”《金刚经》有云:“但凡有所相状,皆为虚妄。” 无论是天上之月,还是水中之月,皆因因缘而起,皆是虚妄之觉。倘若执着于天上月与水中月究竟何为真,便落入了“真妄二边之见”。从理学的视域去看,天上月和水中月可被看作体用关系。然而,正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表明天上月与水中月并非对立关系,而是本体与功用相互显现的关系。
“复水为天,复天为水?”天与水相互连接,天和水究竟是一体还是两体呢?水自然就是水,天自然就是天,然而水与天又有什么不同呢?天与水又有什么差异呢?此地正是前人所说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那番道理。

哲人大贤对于世界以及自身的理解,通常具备普世性。正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倘若我们借助西方现象学的视域去分析这首诗,那么便能够获得别样的体会。
我行走时影子也行走,我停止时影子也停止。在此处,能够把我(身体)视作原初意向性的承载者。法国现象学家梅洛 - 庞蒂觉得身体是世界的关键所在,诗中“我”和“影”的这种动态关系并非主客二者的二元对立,而是身体运动在空间里的现象学延伸。影子作为身体的“知觉侧显”(Abschattung),一直指向着身体在世间存在的具身性。月光对影子的“书写”,实际上是身体与世界的一种互动编码。诗人对“我与影为一为二”感到困惑,这种困惑可以被看作是对身体的主体性与对象化界限的一种判断悬置。
两轮月呈现出现象学意义上同一本质的不同侧显。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倡通过“现象学还原”来搁置自然态度与判断。诗中“若个是真底”这一疑问,恰恰是对“自然实在论”以及经验的一种主动搁置。天上月与水中月并非真假相对。天上月是视觉直观所呈现的“原初印象”,水中月则是水面折射而形成的“当下化再现”。这二者共同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月”的现象学整体。
偶然步于溪旁,这一转折引发了空间境遇的意向重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着重指出“空间是存在的澄明之境”,这里所说的“澄明”(Lichtung),并非是人类主体凭借自身的认知能力去照亮或揭示事物,而是存在自身的一种生发,是存在自身的呈现方式。它属于一种先于主客二分的原始境域,在这个境域里,存在者能够得以显现并且被理解。诗人移步至溪边时,月光的境域发生了变化,从天空的投射之境转变为水月共辉之境。这种境域的切换,让我们看到了知觉对空间的依赖。水中的月并非月的“摹本”,而是月光在溪流境域中真实地绽放出来的。诗人对“两月”“天水”关系的追问,实际上是对存在者被遮蔽状态的揭示,以此进入到澄明之境。
“月能写出我的影,而它自己写出来的又像什么呢”蕴含着身体与世界互为镜像的现象学隐喻。就如同梅洛 - 庞蒂所认为的,世界是身体的外在表现,身体是世界的内在呈现。诗中的月光既投射出“我的影”(这是身体的外在化),又通过溪水映照出自身(这是世界的内在化),从而形成了身体 - 世界 - 他者的交织网络。这种循环映照揭示出:主体不是独立的实体。主体是在与世界的反射性关系中构成自身的。“我”与“影”的关系,“天”与“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这种辩证关系实为存在通过身体媒介的自我诠释。
从现象学角度来分析,此诗让月光与我、影、水、天产生了互动,并且完成了一次在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直观。诗人没有把这些现象简化为物理实体或者主观表象,而是在动态的知觉过程中,让现象的显现一直保持着神秘的状态,这与现象学所强调的“描述而非解释”的方法论是相契合的。诗中的“为复…为复…”这种句式,是对自然态度的搁置以及对存在多重显现的开启。最终在“天-水-月-影-我”这样的现象学场域里,达到了海德格尔所讲的“天地人神”四方一同舞蹈的那种清晰明亮之境。
这首《夏夜玩月》主要是在说理,几乎没有情感。它与《诚斋集》里的大部分诗歌不一样,体现出了杨万里诗风的多样性,还为我们提供了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解读的可能性。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