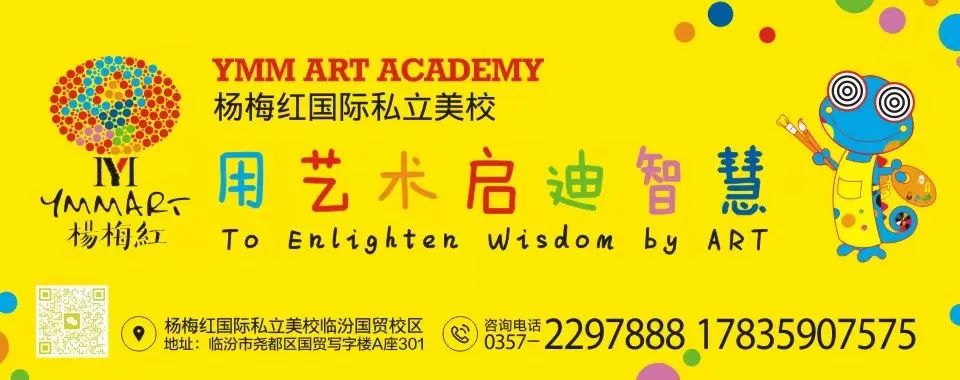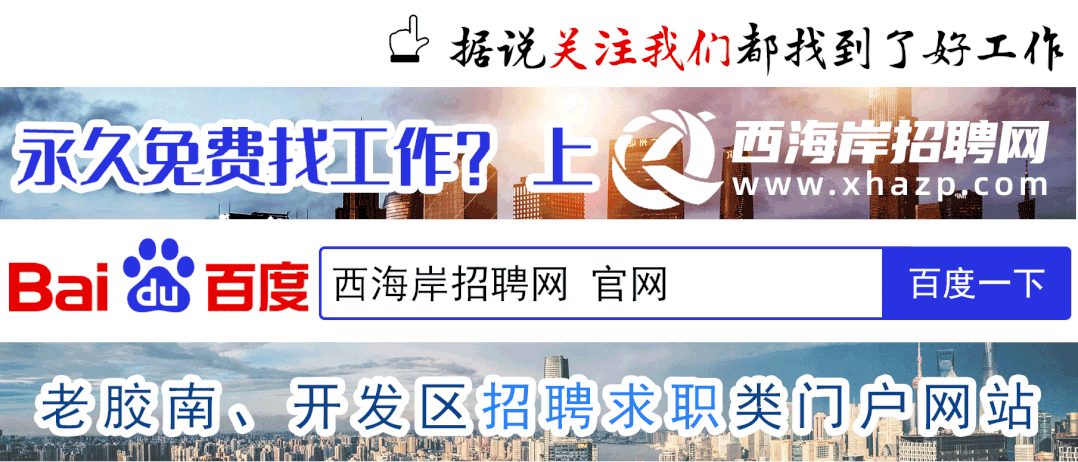经历多次删帖和投诉的打击,他逐渐积累了应对经验,并开始调整自己的表达策略:原本尖锐激烈的言辞已被更为温和的“换汤不换药”所取代。
而且,这位阅读量颇丰的作者,通过使用查重工具和电子书平台,发现众多其他写作者的作品中,也普遍存在相似的问题。
蒋方舟,今年即将迈入36岁。自7岁起便踏上写作之路,9岁时便完成了散文集的出版。12岁起,她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作品数量众多。然而,在对比“抒情的森林”这一系列作品时,其中多篇与加缪、纳博科夫等人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

蒋方舟作品与契诃夫作品对比
由此,“抒情的森林”这一概念如同滚雪球一般逐渐壮大,不仅涉及到了蒋方舟,还延伸到了他母亲尚爱兰的创作;在阅读尚爱兰的作品之后,人们发现李凤群的《大江边》中隐约可见尚爱兰的旧作《永不原谅》的影子;更进一步,蒋方舟和李凤群的文字中,也都能寻觅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文学印记……

李凤群作品与尚爱兰作品对比
环环相扣,文本间的相似性愈发显著。随后,他的帖子中涌现出了更多名家的名字:,,,。
孙频的《玫瑰之宴》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诗歌《我的手艺》、他的《安的列斯群岛,史诗的记忆片段》以及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的《柏拉图对话中的神》存在某些相似点;徐衎的《肉林执》则与韩松落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有相似之处;焦典的《孔雀菩提》亦与格非等作家的一些作品呈现出相似性……

红星新闻:持续这样的调查,作为一位读者,你是否会对文学界产生失望情绪?
在这段经历中,你或许会惊叹,《包法利夫人》之强大,福楼拜之文笔精湛,加缪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实至名归,更不必说马尔克斯、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否则,孙频、蒋方舟等众多作家又怎会如此钟爱他们呢?
为何常常出现环环相扣的现象?原因在于他们所青睐的文本种类彼此之间极为接近。若方向正确,便会表示敬意、汲取灵感、进行学习;反之,若方向错误,那些卓越的经典文本便会如同黑洞一般将人吸入其中,而身处黑洞周围的人也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红星新闻报道,不少作家在长期面临“涉嫌抄袭”的争议困扰的同时,依旧持续推出新书,仿佛这一切并未对其产生任何负面影响。对此现象,您有何见解?
抒情的森林,我的观点与你略有不同,实际上他们承受了相当大的影响。记得在蒋方舟的某个视频中,她曾提及与她相关的争议,由此可知,她本人对此事应是有所了解且颇为在意的。
对他们而言,“回旋镖”终将降临。无论你是以白纸黑字形式发布的公开出版物,我们都能将其寻觅得到。
要“公开”,不要“私信”
但没有谁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如此相似”的拷问。
于是,某些作者或是编辑选择了私信的方式进行沟通,还有的是通过中间人传达他们的“看法”。在蒋方舟的主页评论区,众多网友见证了蒋方舟从关注到取消关注的整个过程。
“抒情的森林”中那段回忆,发布了几篇有关蒋方舟作品的讨论帖子之后,其中一篇帖子因“相关权益人投诉”而被删除。紧接着,蒋方舟注意到了自己的账号,她主动联系了我,表示是她提出的投诉,并向我表达了歉意。
据他透露,在后续的私信交流中,蒋方舟一方面将其作品称为“早期的不成熟之作”,并表示愿意“理解和虚心接受”批评;另一方面,她渴望进行深入的交流,对“较真”的态度表示认同,并希望建立对文学的探讨。
“抒情的森林”感到疑惑:“撰写《主人公》时,她已经年过三十,持续创作已有二十余载,为何作品仍显稚嫩,这样的说法合理吗?”


蒋方舟《主人公》和卡达莱《梦宫》的对比
他总结许多私信的潜台词是“求放过”。
有的情形甚至让他感到内心的矛盾,“一位编辑通过私信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提到‘今后请多提醒’,然而不久后,他又发来信息,请求‘能否先将这一内容删除?’”
孙频近期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达了对“抒情的森林”的感激之情,指出该平台指出了她早期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她回忆道,在初涉写作领域时,她对福楼拜的作品情有独钟,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会将一些自己钟爱的句子融入小说之中。

关于这一点,“抒情的森林”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她的态度既坦率,却又并非全然坦率”:她仅承认福楼拜是我所推崇的;然而,后来我又推崇了严歌苓、钱钟书、朱天文等人……那么,是应该逐一向他们道歉,还是逐一声明“我对每一位作家都喜爱至极,以至于不自觉地将其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
红星新闻:你在帖子中提到,恳请作家和编辑们不要给你发送私人信息,这是出于何种原因呢?
抒情的森林,与我并无瓜葛;你所创作的书籍,面向的是广大读者,是公之于众的,因此无需向我透露你的内心轨迹如何,你背后所承受的苦楚。
同理,我坚信作家不应与读者建立私人关系。他们的职责在于向读者提供明确的解释,而非私下与我沟通,请求我放弃某项行为。若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应公开发表。

红星新闻:你希望他们给出怎样的反应?
抒情的森林,我未曾对他们抱有期望或过分的要求,因他们无需迎合我的期待。无论是作家、出版社还是编辑,一旦作品被指出此类问题,他们理应承担起回应的责任。这并非针对我个人,而是面向读者和公众。遇到此类情况,作者和出版社等各方责任主体都应建立相应的应对措施。
红星新闻报道,部分年轻作者的首部作品颇具争议。对于这类作者,你是否认为公众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与机遇?
抒情的森林,自然应当给予机会。然而,这并非由我单方面决定,而是取决于那些刊物是否愿意提供发表的平台,以及那些曾对它们感到失望的读者是否愿意再次购买他们的著作,这一切都取决于读者的选择。
有些作家向我表达,写作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然而,在我看来,只要有笔、有纸和思想,写作便可以顺利进行。即便你被众人所遗忘,写作的能力依然在你手中。你这样问,是否真的对文学怀有热爱?你话里的深层含义是你不愿放弃现有的名声,不愿失去发表作品的途径。
“长脚”的帖子,会去到该去的地方
各种出乎意料的反馈,使“抒情的森林”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正逐渐触及某个临界点。他明白,尽管众多编辑和作家并未公开发表看法,但他们确实在关注他的帖子。
最初在投放“文本对比”主题帖时,“抒情的森林”会主动@涉及的相关人士,意图通过这种方式提醒他们关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意识到,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文学界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紧密的社群,那些帖子自然会自发地传播至它们应当抵达的地方。
至于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答复,以及答复将以何种方式呈现,他并未抱有确切的期待,“这并非我能够掌控的范围”。
他关注的焦点是另一件事情:他能够决定是否将此事公之于众,他表达的内容是否客观且合乎逻辑,以及众人是否认同此事的合理性并认为其值得讨论,这些因素构成了他目前最大的动力。

红星新闻报道,部分网友提出,被指控的作者或许只是借鉴了文中的一小部分内容,然而整篇文章仍旧是作者独立创作的。对此,您有何看法?您认为在致敬、模仿与抄袭之间,有何清晰界限?
抒情的森林:这无疑是争论的焦点,然而对我来说却从未构成困扰。抄袭行为确实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判定,然而,若人们仅仅因为不触犯法律就认为可以接受,这实际上是对写作伦理的一种妥协。对于一名作家来说,与另一位作家在几十个或几百个字上完全相同,这样的情形是否合理?
“致敬”的例子不难理解,比如提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1Q84》,读者立刻便能察觉到其灵感源自《1984》。村上春树有意让读者轻易辨识这一致敬。
作家们无一例外地都是通过研读他人的作品来提升自己的写作技艺。然而,当他们着手创作自己的小说时,理应设定明确的界限。文学创作极具个性化,两位作家即便再有相似之处,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于任何抱有尊严和远大志向的作家来说,将自己的作品与他人的文字雷同视为一种耻辱。

红星新闻报道,帖子发布之后,部分作者及刊物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对此,您有何见解?
抒情的森林:有人通过其他博主与我取得联系,指出我发布的内容显得有些抑郁,或者直接晒出病历,向我透露“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病情可能会迅速恶化”。因此,我提出不进行私下交流,因为这很容易演变成倾诉苦楚和道德上的束缚,甚至变成指责:“你这是要害死我,让我陷入抑郁。”
然而,这些压力是否与我们从事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联呢?这些压力并非由我自身产生,而是源自无数读者的期待。阅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合作。作者倾力创作出优秀的作品,读者购买并阅读,若喜欢便给予赞美,若不喜欢则提出批评,双方应当保持这种相互交流的动态关系。若提及“压力”,创作过程中存在压力,发行阶段同样承受压力,编辑提出的建议亦带来压力,那么为何在普通读者那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却变成了“巨大的压力”?
红星新闻:在整个过程中,你会有“独自抗争”的感觉吗?
抒情的森林:并非如此。我始终关注的,是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同时,我也期待大家能够言之有物,尽量围绕作品本身展开讨论。然而,我坚信作家必须直面自己的创作,以及面对他们的读者。我自诩为一位真正的读者,会以严谨的态度阅读他们的作品——即便莫言阅读焦典的小说,也可能不及我阅读焦典的小说来得专注。
我不是那种用放大镜在古籍中寻觅他人瑕疵的人,我仅仅是热爱阅读的人。作为一名普通的读者,我对阅读杰出作品、发现优秀内容依然充满渴望。请不要误以为我在指责他们,我对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年轻作者群体始终怀有满腔期待。
红星新闻记者 毛渝川 任宏伟 编辑 蒋庆
(下载红星新闻,报料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