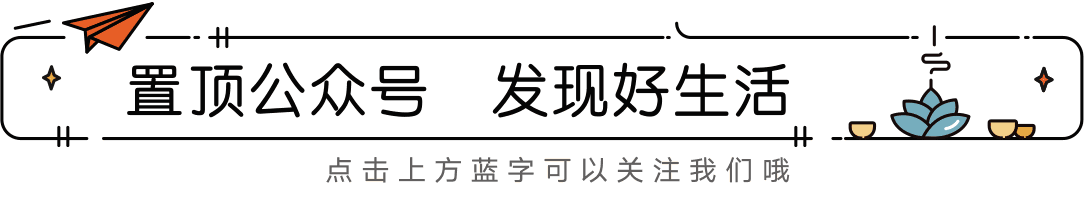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旨在提升进口税以捍卫国内产业,却引发了全球贸易的冲突。美国进出口贸易额急剧减少,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显著下降,失业率急剧攀升,最终将经济危机转化为地缘政治危机。相较之,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更为健全,金融监管和风险对冲措施的实施显著减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然而,特朗普的关税策略依旧揭示了类似的逻辑难题: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来调和全球化生产关系中的固有矛盾,这或许会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分裂。

重商主义主张国家介入、贸易保护和追求贸易盈余,而新自由主义则推崇市场的自我调节和资源的自由流通。特朗普新一届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展现出一种“双面性”:在国内,美国继续实施减税、放宽金融监管等新自由主义措施;在国际贸易方面,美国全面实施关税壁垒、推动产业回归等保护主义策略。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向世界推广其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策略,这一策略以追求生产成本的最大效率为核心。由此,美国本土产业逐渐出现空心化现象,有效需求受到压制,财富分配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具体数据表明,在1960年至2022年期间,美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从38.7%下降到了18.5%,而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也从20%下滑至8%。资本收益对劳动收入的挤压日益明显,跨国公司通过海外生产来获取成本优势,导致国内制造业的劳动收入不断下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整体消费需求呈现萎缩态势,进而对生产活动产生了进一步的压制。从1980年到2022年,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增长了16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劳动收入的增长比率也同步下降,贫富差距持续加剧。

当这种分配不均达到临界点时,经济上的问题演变成了关于政治认同的危机。特朗普利用“美国至上”的叙事手法,将矛盾归因于外部威胁,从而将国内的阶层矛盾转移开来,并给保护主义政策穿上了一件“民意支持”的外衣。在2024年的选举中,大约有60%的无大学学历白人选民支持了特朗普,这一现象揭示了社会底层对于产业流失所产生的不满情绪。
美国的代议制民主选举机制已转变为“短视政治”的温床,执政党派将总统选举的胜利置于长期社会治理之上。产业空心化凸显了自由市场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而选举制度则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政治影响。特朗普将经济上的不安转化为身份政治,这实质上是制度性困境下的应急措施,然而,若美国不能解决产业空心化的根本性问题,其政策将可能持续走向极端。

特朗普政策的转变背后,体现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战略从注重“效率至上”转变为强调“安全至上”,力图通过设置关税和运用地缘政治策略,重塑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有限全球化”格局。这一转变并非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而是在市场自由与国家调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可视为对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一种补充性调整。
然而,若美国不能实现新一轮的生产性投资累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与劳动大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不断加剧,进而引发全球经济的分裂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的显著上升,使得世界陷入“自由主义扩张——矛盾积累——保护主义收缩”这一周期性的循环困境。

特朗普实施的关税措施揭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蕴含的内在冲突集中显现,这实际上是美国在产业空心化趋势加剧及政治角力压力之下进行的制度性调整。从理论层面来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与原教旨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发展观念不尽相同,然而其核心是对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补充性调整”,旨在通过国家层面的干预措施,弥补全球化生产对美国国内制造业产生的结构性问题。
然而,由于美国实体经济内部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实施贸易关税壁垒的举措效果有限,难以打破“自由主义扩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不断积累——保护主义收缩——自由主义扩张”这一周期性的循环。未来,美国能否摆脱“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之间的摇摆不定,不仅关系到美国自身的命运,还将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发展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