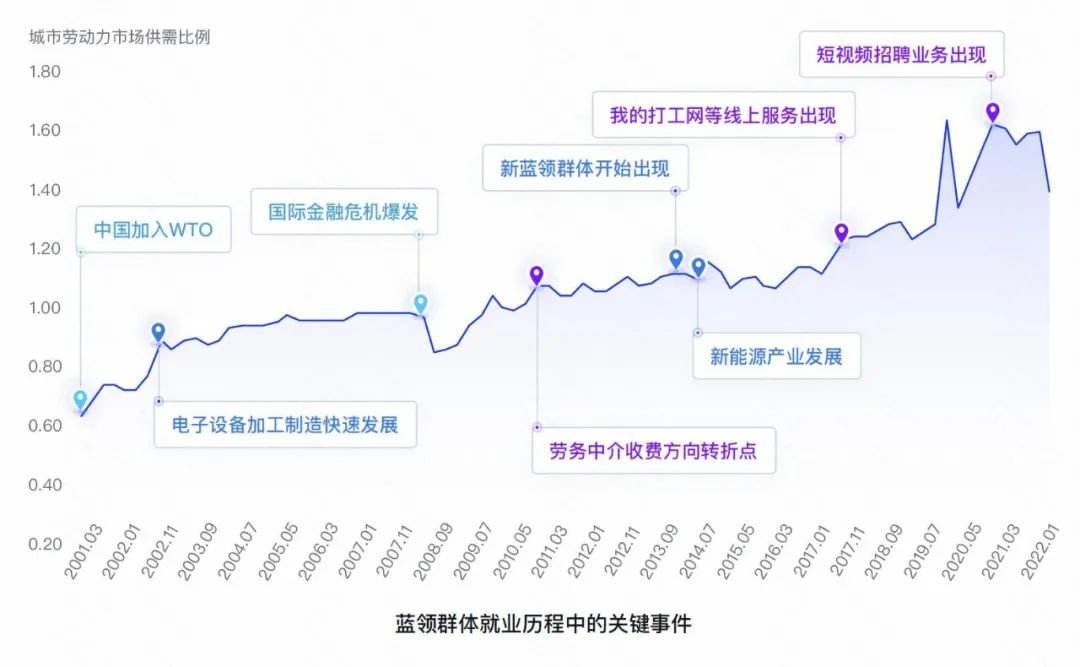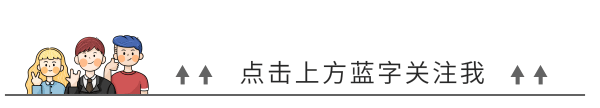格鲁吉亚裔导演巴库拉泽凭借《院中雪》入围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并最终斩获最佳导演奖。这是今年上海电影节秉持的“多元视角”的极致体现。这位导演此前已有两部作品入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和“一种注目”单元。随着资历的提升,他的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的价值也不断提升。和所有身份或作品包含一定“奇观性”的导演一样,他在完成特定的民族形象叙事的同时,也完成了通过作品传达的一种无意识“怀旧”氛围的建立。

《院里雪》海报
《院落雪》通过两位老同学——家住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列文和住在俄罗斯莫斯科的吉维——的平行日常生活展开,呈现当代第比利斯和莫斯科的“双城记”。一边是住在破旧老屋里的社会下层,一边是陷入创作瓶颈的中年导演。两人在网络上重逢,却并未上演惊心动魄的闹剧,而是随着电影极度生活流的平行剪辑,在各自的人生轨迹中不断延伸着旅程。
影片配乐极少,几乎与同时期的欧美当代艺术电影体系不相上下,甚至与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艺术电影鼎盛时期的悲情作品拉开了距离。影片大量采用室内定格+室外手持的镜头,以无限接近的姿态记录两人在不同空间的日常生活。在毋庸置疑的“故事片”外衣下(本片获金爵奖提名的是故事片单元而非纪录片),展现出最原始的电影镜头语言功能。
影片的叙事线索来自于导演与好友重逢的真实经历。影片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拍摄,在拍摄过程中,两队之间的协调也成为剧组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影片中出现的社会生态和景观,均来自当代最鲜活的生活场景。男主角列文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如今却是一个肥胖无业的糖尿病患者;季伟通过视频电话不断与家乡的老友联系,想把电脑寄回去。“双城”的社会地理地图,在“后冷战”的背景下,通过微妙的时空关联,向观众传递着通常容易被快餐视觉文化所掩盖的“元叙事”信息。而星东看似散漫、难以轻易捕捉主题的坐卧,则直接将叙事作为一种方式或审视对象呈现给观众。

《院里有雪》映后见面会
《院子里的雪》这个片名,以最明显的视觉元素“院子里的雪”呈现在影片的开篇。整部影片包括了列文每天吃的药丸、他养的狗“大杰西”和“小杰西”、第比利斯的社会经济现实,以及其他包罗万象的人间冷暖。如同“院子里的雪”这个视觉形象一样,它包裹着列文的梦境与现实,也点出了除了“造梦”之外,还应该理解和认可的一种“为现实而拍”的机制。虽然如今电影“接近现实”的内涵与安德烈·巴赞那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纯化”的镜头语言体系出发的方法论不同,但都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共同现实困境。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观众,看完这部影片后,常常觉得“无聊”、“催眠”、“看不懂”等关键词。 一方面,当然是导演的审美取向所致,另一方面,在当代大多数电影创作的美学结构中,包括今年上海电影节的其他参赛影片,确实也很少有像《院子里的雪》这样近乎朴实无华的案例。
虽然主竞赛单元的不少作品都表现出对前辈电影大师明显的借鉴与内化,但这部影片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苏联电影的某些鼎盛时期。不过,这部作品强烈的全方位“当代性”却无法被忽视。它成为2024年6月潮湿的上海电影院里一次“令人惊喜”的银幕体验,并在围绕“电影节”的观影实践中缓缓展开一个(和另一个)平行的陌生世界。人们自然难以相互交流,但银幕上的世界往往很容易成为一家人,因为它们来自人类眼睛的观影本能,也折射出人类的未来,或许不同,又或许相同。
王培蕾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感谢您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为了更好地了解电影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提高未来电影节的服务质量和观众体验,请您花几分钟时间,结合您的真实体验,填写这份问卷。本问卷为匿名问卷,感谢您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