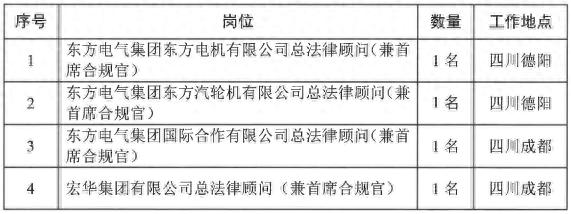【人才强国新征程:聚焦文物保护修复人才】
光明日报记者 任欢 杨桐桐 李云
走进北京故宫,犹如步入一幅色彩斑斓、不断展开的宫殿画卷:有人为东西六座宫殿的精美陈设吸引;有人为内廷园林的幽雅布局爱不释手;有人为古代建筑风格的沧桑而陶醉……
驻足故宫博物院常设文物馆,一件件稀世珍宝,正展现着无与伦比的美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物证,不时有人惊呼,这些精美的文物是怎么下来的?
我们在故宫西侧的一排平房里找到了答案。这里没有旅游区的喧嚣,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批文物被送来。有的历经风霜雨雪,患上了“病魔”;有的长期保持原样展出,急需除尘养护。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文物修复者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巧手,日复一日地为每一件文物“治病延寿”。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故宫博物院目前拥有古代书画、古代文物、宫廷文物、图书档案等珍贵藏品186万余件。”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部主任曲峰说,“文物保护修复类似于医学,医学关注的是人体健康,文物保护修复关注的是文物的‘长寿’。更好地保护好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是我们的责任。”

北京故宫博物院 新华社

书画临摹组副组长陈璐。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漆器修复团队负责人闵俊荣。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铜石修复团队成员尹航。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马赛克修复团队负责人孔彦举。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它们融合了古代和现代技术
镶嵌修复团队负责人孔彦举的工作台上,除了刻刀、镊子等工具外,还有一本《中国鸟类观察手册》。
“做文物修复,为什么还要学鸟类观察?”记者好奇。

“修复镶嵌文物,需要了解文物上缺失部位的纹饰。我们之前修复过一件镶有翠鸟羽毛的花鸟挂屏,通过显微镜观察文物上的羽毛,发现它们属于不同的鸟类,由于制作工艺不同,出现的病害也不同。只有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才能确保修复的正确合理。这本工具书可以帮助我更好地了解鸟类知识。”孔彦举笑着说。
什么是镶嵌文物?“镶嵌是用宝石等材料装饰金属、漆器、木材等的传统艺术,镶嵌材料包括宝石、贝壳、象牙、木材、金属等。”孔彦举介绍,故宫博物院藏镶嵌文物目前包括宝玉镶嵌、花丝镶嵌、羽毛镶嵌等七大类近15万件,其中不少都需要保护修复。
此前,孔燕菊和团队成员修复了一对紫檀嵌玉人立柜。该文物为清初文物,由于时间久远、黏合剂老化,嵌件缺失严重。修复的难点在于将修复材料制成合适的嵌件,使缺失部分与原件完美吻合。因此,孔燕菊和团队成员以两个立柜为参照,根据原件上留下的黏合剂痕迹,画出所有部位的轮廓,确定像貌,再将各个部位裁出,经过开料、切料、塑形、拼接、雕琢,最终完成修复工作。
“做镶嵌修复工作,首先要了解文物的制作方法,掌握多种传统技艺,才能在传承古法的同时,采用配套的修复材料,对文物进行科学合理的维修修复。目前,我们的团队已经发展到12个人,年轻人的加入,让修复工作充满了青春活力。我经常告诉他们,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镶嵌文物修复师,必须打好基础,认真思考,不断总结。文物的价值在于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要想讲好它的故事,只有努力去了解它、去接近它,才能读懂它、读懂它。”孔彦举说。
木质修复团队副队长刘凯拿起桌上的深红色方尺和小锯子反复打量:“我们团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新人必须先掌握木工基本功,才能正式开始接触木质文物。通常都要亲手制作一套这样的木工工具。”
“自己动手做工具最能体现你对木材的了解程度和基本功的掌握程度。只有真正动手做起来,你才能明白自己将要面对什么,才能思考如何付诸实践。”刘凯说。
在此期间,刘凯正在修复一件清代黄花梨圆桌。此前,有专家认为该文物属于明末清初。但在修复过程中,刘凯利用新技术发现,该文物采用了木镶嵌工艺。“通俗地说,就是工匠做家具的时候,会用一些柴木(比如松木、楠木、柏木)包边,外面用一些名贵硬木(比如紫檀、黄花梨)包裹、镶嵌在家具表面。在清宫中,这种工艺一般在乾隆时期开始大量出现。基于此,我认为这件文物是清中期以后的可能性较大。”
“看来,修复文物不只是修缮那么简单,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研究。”记者感叹。
“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精湛的修复技术,还需要丰富的文物知识。”刘凯频频点头,“近年来,我们团队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技的力量。前段时间,我们还和林科院木材鉴定中心探讨,希望利用人工智能,量身定制一套智能木材鉴定识别系统,为我们在文物修复方面的材料判断提供更多的参考和依据。”

在有机文物保护实验室,镶嵌修复团队成员龚天舒正在实验室成员王云丽的指导下,探索清代服饰“鲜黄色”为何没有固定的色度值。通过对大量实验样品进行染色,龚天舒发现,由于制作工艺、光照环境等原因,颜色可能会出现偏差。“我对文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龚天舒说。
“文物修复不能简单照搬传统经验,也不能依赖先进技术,而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症下药’。如今,团队里的年轻人都秉持着一种精神——不仅要知道结果,更要知道背后的原因。本着这种严谨,一定能走向更好的未来!”王云丽说。
在他们眼里,学习技能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漆器修复团队负责人闵俊荣时常想起自己的师傅张科学。“师傅一点一点教我基本功,从小器物的局部做起,上漆、打磨、贴金……等技法熟练了,再开始修复复杂的文物,年复一年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漆器修复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行业,每次修复一件漆器,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闵俊荣说。
他举了个小例子:故宫博物院的漆器藏品十分丰富,有两万多件,其中还包括古琴等乐器,馆藏古琴就有八十多把,大多都是稀世珍品。如果要修复一把古琴,学一手高超的修复技术就够了吗?
“远远不够!《漆器志》里有一条修复原则——巧手可以接手拙工,庸工不能代替精工。”闵俊荣解释道,“通俗地说,修复一件文物,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什么水平?不但要研究它的工艺,还要研究与之相关的技术。你不会弹琴,怎么修复?”
闵俊荣修复的第一把古筝名叫《万壑松涛》,当时他不仅跟董春起先生学弹古筝,还到全国各地拜访制古筝老师,学习制古筝。直到大家认可他的制古筝工艺和演奏技巧后,他才真正开始修复古筝。“老一辈的漆器修复师心里总有一把秤,如果技术不过关,宁可不修复,以免文物受损。”闵俊荣说。
秉承这样的态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代代漆器修复师运用传统涂漆工艺,修复了太和殿金漆宝座、古筝峨眉松等一系列重要漆器文物,以及太和殿金漆宝座、屏风、元代张成红漆栀子圆盘等复制漆器文物,一方面使一大批珍贵的漆器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使传统的涂漆修复工艺得以保存和延续。
时隔多年,闵俊荣已从徒弟变成师傅,如今,他把师傅教给他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团队成员。2015年成为漆器修复师的徐杰,正跟闵俊荣学习古琴修复技艺,闲暇之余,她也会弹奏几首曲子陶冶情调。“古人说古琴有九德:奇、古、透、静、滑、圆、清、匀、香。我们团队现在正好有9名成员,就像这九德一样,气质各异。但要想弹好古琴,就要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发挥到极致,这样才能更稳健、更迅速地跟上前辈们扎实的步伐。”徐杰笑着说。

金石修复团队成员尹航近日完成了文物“叶纹镜”的保护修复工作。这面战国时期的铜镜已碎成十二片,且下落不明,急需修复。“在故宫,如果要修复一件文物,首先要设计相关方案,方案不仅要包括修复方法、材料,还要写明工作计划和修复目标,然后请专家进行评审。评审过程中,专家会对存在的难点提出质疑,只有方案制定者对所有问题都回答正确后,修复才能获得批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尹航笑着说,“但大家都从内心深处认识到,故宫的高标准、严要求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成长。”
想要掌握“完美”的手艺,就要做好“十年磨一剑”的准备。尹航说:“像我2015年就来到这里,要完成一年的实习,才能逐渐开始接触文物。实习期间,要先学会制作复制品,加深对文物的了解,同时也要练习上色,培养对铜和锈的感性。”
如今,尹航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青铜器修复复制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对她来说,非遗技艺的传承离不开老一辈人的教诲。“在故宫,只要徒弟想学,师傅们就会把学到的东西全部教给他们。我们可以一步步踏着师傅的脚步,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新理念、新技术,找到最合适的材料和方法,做好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
在挑战中成长,在压力中突破。如今,团队年轻的面孔上洋溢着朝气。8月23日,预防保护团队成员李根收到喜讯,他的项目“基于多重散射理论的古瓷釉反射光场模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去年申请没有获批,但老师们鼓励我要耐心、仔细思考理论模型是否构建得好。于是重新审视项目的整体设计逻辑,竟然发现了理论推导中的错误。修正后又增添了新的研究进展,今年终于成功了。”李根说,“有了好的引导,我相信自己能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上做得更好。”
他们心中有着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
当记者见到书画临摹组副组长陈璐时,她正在讲述自己已临摹近两年的《胤禛妃乐图》的临摹细节。
“复制对于文物的保护和修复能起到什么作用?”记者问。
“书画文物终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临摹所做的就是延长书画文物的生命,让千百年后的人们还能欣赏到其原貌。临摹的产生和发展,对延续中国古代书画历史、保护我国古代灿烂的物质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陈璐详细说道。
临摹其实自古就有,历朝历代都有画家临摹古代字画,如王羲之的《兰亭序》、顾恺之的《洛神图》等古代字画,虽然原作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仍能从古抄本中领略到古人精湛的绘画技巧和深邃的艺术思想。

想要做到和原作一模一样,绝非易事。制绢、画稿、定墨稿、设色、调色、抄字、盖印,“每一道工序的目的,都是要尽量贴近原作,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钻研。”陈璐说。
2011年,“古代书画临摹复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陈璐入职故宫博物院。如今,她已成为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书画临摹团队也发展到10人,大部分成员都是80后、90后。
“在文物不方便展出的时候,可以用我们的复制品代为展出,一方面可以推广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技艺,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各个时代的复制品,向观众系统地普及中国美术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陈璐话语从容,自信满满。
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深感保护历史文物、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和重任在肩。
在袋盒生产组副组长张静静的工作台上,记者看到了种类繁多的袋盒,其中有仿制清宫旧藏的数款笔盒、如意云盒,还有设计创新,既可展示又可收纳的冠帽袋盒等。
作为文物配件,荷包盒以往受到的关注较少。近年来,在张静静等人的努力下,“传统宫廷荷包盒制作技艺”于2021年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甚至喜爱这项传统技艺。
“我们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积极改进传统胶囊结构,将无酸纸、半透明保护纸等新型文保材料运用到胶囊的配置中。”张静静说,“传承而不守旧,深入挖掘技艺背后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有利于传统技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促进文物保护更加深入、科学化。”
沿着中轴线,我们走到神武门,这里正展出着“辉煌宫墙——清宫珍藏挂屏风展”。《檀香镶宝明皇试马图》、《弘历梅杏图卷》……一件件被团队成员保护修复的挂屏文物,正向游客展示着清代宫廷屏风的精美雅致。不时有游客感叹,能近距离欣赏如此精美的文物,不虚此行!
“文物保护修复是多学科交叉渗透形成的学科,需要应用现代分析检测设备和技术,借鉴当今其他学科完善的理论框架,构建自己的体系,就像一百多年前医学引入科学的实验室方法一样。我们积极依托故宫博物院人才计划、太和学者计划等人才培养计划,切实加强故宫博物院学科带头人建设和科研人才储备。目前,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部门已经拥有150余名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巧手,让人们看到更多‘健康’的文物。”曲锋说。
光明日报(2024年9月8日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