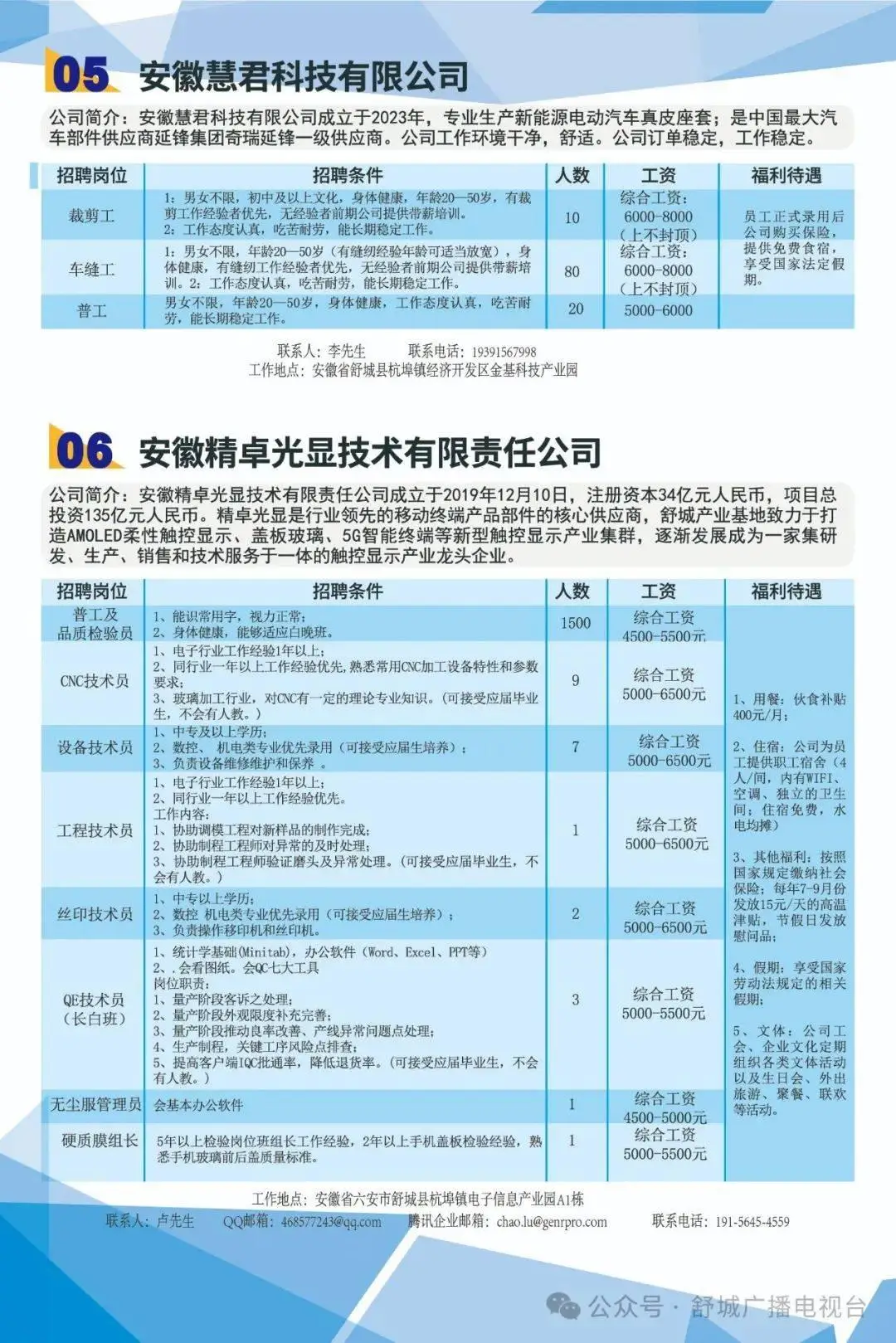雅典卫城与敦煌莫高窟距离很远,然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共鸣。它们都属于文化创新的标志。如今,雅典卫城的相关事物以及敦煌壁画实现了科技化,都不约而同地将虚拟与现实、教育与娱乐相融合,既能保护文化遗存的原本样子,又能积极拓展传播的范围。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文化创新到底是与历史的分离,还是跨越时空的交流?
「传统现代辩证共生」

文化创新遵循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则。其本质在于,文化基因内核具有恒常性,而表达形式则具有流变性,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以儒家仁学谱系为例子:孔子把“克己复礼”确立为伦理规范;孟子凭借“恻隐之心”构建起道德本体;朱熹把仁升华为“天地生物之心”这样的宇宙本体;王阳明通过“知行合一”让仁实现了实践转化。这一演进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而是对其核心价值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
再看佛教中国化的过程,禅宗通过“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来革新修行的路径,把印度佛教的禅定传统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心性哲学。《坛经》继承了佛陀“缘起性空”的根本要义,却以“菩提本无树”的这一公案,实现了教义表达的本土化转化,这恰恰是“变与不变”的生动体现。
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对历史文本进行当代激活。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的《五台山图》得到了现代阐释。这揭示了文化创新在认识论方面的突破。壁画通过高 3.5 米、长 13 米的全景式构图,实现了三重视域的融合。其一为文殊信仰的宗教圣境;其二为唐五代社会生活的时空坐标,且标注地名 195 处;其三为建筑形制的实证图谱,包含佛寺、草庵、城门等建筑类型学样本。1937 年,梁思成团队依据壁画线索找到了佛光寺东大殿,从而完成了图像文献与物质遗存的互证。敦煌研究院进行了数字化复原以及建筑类型学分析。通过这些方式,进一步揭示出壁画中存在着诸多建筑形制,并且这些建筑形制与现存的唐宋遗构是相对应的。

敦煌莫高窟

这种“图像证史”的方法论创新,印证了伽达默尔阐释学里的一个理论预设,即历史文本的意义能够在当代的阐释过程中获得新生。游戏《黑神话:悟空》借助虚幻引擎和光线追踪技术,对《西游记》神话体系进行了丰富和重构。它通过高精度扫描技术,把 36 处古建筑嵌入到游戏场景中。同时,借鉴敦煌壁画风格设计了通关画卷。这样一来,玩家在沉浸式体验中能够完成对古典文本的“数字考古”,让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在全球玩家的互动中得以焕发新生。
古典范式进行现代转换,这是文化创新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复古以开新”的运动,创造出了“古典形式+人文精神”的融合范式。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借助解剖学突破,达成了古典平衡的现代转变:雕像的高度为 5.17 米,右侧收紧的肌肉与左侧放松的曲线形成张力对比,把希腊静穆美学转变为人类觉醒的力量宣言。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通过科学实证来重构古典理论。它是以观察和人体解剖研究为基础的。用圆方嵌套的几何体系(即四肢展开能形成完美圆形与正方形)去验证维特鲁威人体比例论。这种将经验观察与数学理性相结合的创作方式,让艺术作品成为了连接古典传统与现代科学的认知界面。
儒家仁学的本体论在演进,敦煌壁画得到了实证性阐释,文艺复兴进行了艺术科学化实践,《黑神话:悟空》对古典文本进行了重构,这些共同证明了文化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传统通过现代阐释而获得新生,现代借助传统滋养得以实现超越。这种动态平衡的辩证关系,成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内在驱动力。

雅典卫城
「古今中外多维交响」

文化创新意味着传统元素在形态表达和精神传承方面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且需要构建起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体系。日本浮世绘的全球化演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19 世纪,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在巴黎引发了“日本主义”风潮,这一风潮催生出了凡·高《星月夜》的旋涡笔触,也催生出了莫奈《睡莲》的平面构图,并且还引发了持续两个世纪的文化共振。
中国的古琴进行了革新,这展现了传统艺术走中西合璧之路。20 世纪中叶,顾毓琇把宋代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等古谱转译成了五线谱,从而破解了古代乐谱的密码,搭建起了中西音乐对话的桥梁。1977 年,古琴曲《流水》(管平湖演奏版)被收录进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旅行者金唱片”,使得中国的千年琴韵成为了人类文明的宇宙信使。古琴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所遵循的是“本体守护—形式创新”这一原则。它在保持“吟猱绰注”这一核心技法的基础之上,一方面通过对乐器形制进行改良,比如用钢弦来替代丝弦;另一方面通过对演奏场域进行拓展,从书斋拓展到了音乐厅。通过这些方式,实现了传统艺术的创造性延续。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正在热映。它借助现代动画技术与叙事手法,对哪吒这一经典形象进行了重新诠释。它的成功一方面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另一方面在于通过主题精神内核与全球观众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人们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这种多维创新不是单纯的古今、中外拼合,而是依照解构与重构的深层逻辑。在浮世绘的数字浪潮里,传统线条变成了像素语言;在古琴的宇宙传播当中,东方韵律得到了星际表达;在《哪吒之魔童闹海》的赛博叙事之中,神话原型升华成了全息符码。文化创新的终极价值并非是形式的变换,而是通过持续的对话,推动文化创新以及文明的演进。
进一步来看,文化创新的本源动力是根植于创新个体的精神觉醒的。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历史揭示了个体觉醒能够对文明转型起到催化作用。薄伽丘的《十日谈》借助东方传说转化而成的市井故事,构建起了能够解构教权的“叙事穹顶”。在中国,清代有位书画家叫郑板桥。他“师古不泥古”,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提炼出了“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这样的创作理论。他把竹的形态与人格精神融入到绘画之中,从而形成了峭硬独特的风格。

总之,文化创新就像敦煌壁画里的“飞天”。它需要脚踏着“历史祥云”,同时手持着“未来乐器”。它既需要个体觉醒来提供基因突变的内驱力,又需要制度创新去构建生态演化的培养基,还需要市场机制形成物种扩散传播的链条。当承载着文化创新基因的河流奔腾向前时,每一次踏入都意味着对文明的重新抵达。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徐曼,同时也是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余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