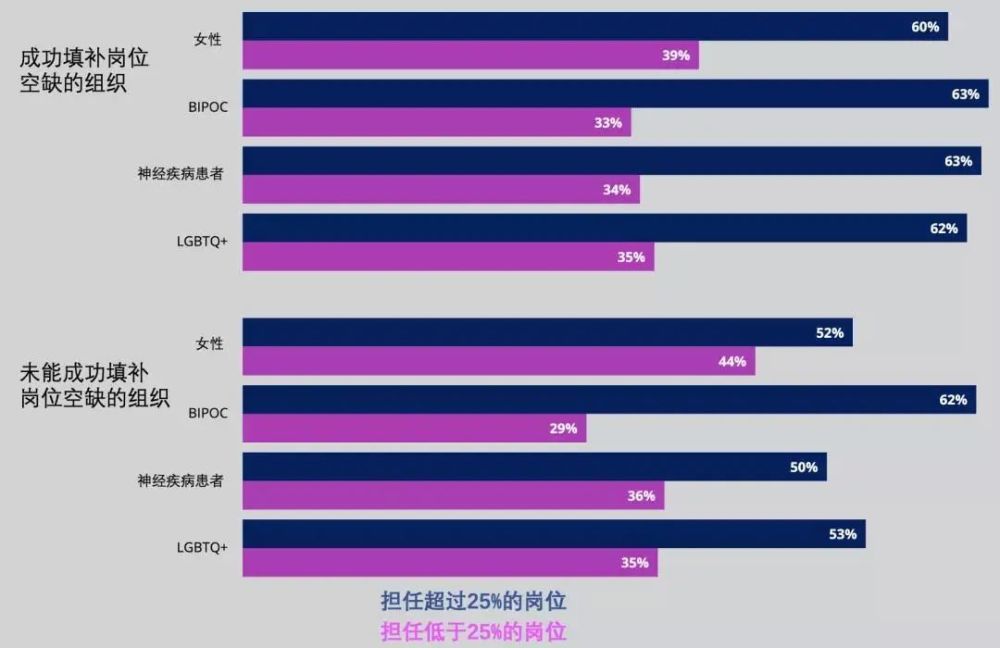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资产的估值出现了两波反转情况。其中,第一波反转发生在 2024 年的 9 月到 10 月这段时间;第二波反转则出现在 2025 年 1 月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反转的核心都是“信心”。去年 9 月出现反转,是因为市场察觉到主管部门会运用一切手段,特别是扩张性财政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决心。今年 1 月发生反转,是因为市场意识到中国民营企业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并且主管部门有意愿扶持民企的科技创新。
总之:第一次是在周期性层面的“信心”方面,主管部门在其中扮演了几乎唯一的主要角色;第二次是在经济长期动力层面的“信心”方面,主管部门与科技类民企在此共同担当主角。去年 8 月,整个中文社交媒体以及资本市场都处于那种“得过且过”,对未来丧失方向的迷茫状况,而现在则完全发生了改变。2021 年曾红极一时的“东升西落”理论,如今再度成为社交媒体的主流。英文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予以认可,不过认可的程度各不相同。
俗话说“信心比黄金还珍贵”。我想补充两句:当人们缺乏信心之时,信心最为珍贵;然而当人们拥有了信心之后,信心便不再是最珍贵的了。这看似是一个悖论,实则体现了人性的本质。试想,你在劝说一个完全对考大学没有信心的学生去努力争取考上名牌大学,在劝说过程未完成之前,信心是最为重要的;在劝说产生效果之后,努力便变得最为重要了!这个学生不能仅仅依靠“信心”来考上大学。信心只是万里长征的开端,仅仅走完第一步的人,绝大多数都未能完成长征。
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会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首次就职演说里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值得惧怕的事情便是恐惧本身。”然而问题在于,罗斯福并非凭借“战胜恐惧”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大萧条。只要看一下经济数据便能知晓,美国从 1929 年到 1933 年的大萧条中恢复的速度较为缓慢,确切地说,是直到 1941 年加入二战之后才得以恢复。
大萧条结束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是新政,还是信心恢复,亦或是战争?到目前为止,这一直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认为是信心主导了经济的复苏,这只是一种高度简化的经济学模型,不一定与现实相符。
不管怎样,有信心要比没信心更好。半年多之前,整个资本市场处于普遍迷茫的状态。某些外资投资者特别悲观,他们认为中国资产“不可投资”,觉得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其历史最高点。通常来讲,在这种情形下,超出市场预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市场压根就没有预期。对于一个饥肠辘辘的饿汉而言,即便只是清水煮白薯,也可算是一顿美餐!(据说这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名言,但我没有确认过)
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饿汉已经享用了一顿“清水煮白薯”。他既已经得到了陇地,又开始盼望蜀地,开始期待起黄澄澄的鸡汤和香喷喷的烤肉。依据一位著名投资人提出的“反身性原理”(Reflexitivity),资本市场的长期走势是由一系列“预期”以及“超预期/低于预期”所构成的循环:
在下行周期,经济数据表现不佳,经常达不到投资者的预期,这会使得资产价格下跌,同时也会导致人们的预期降低。
人们的预期下调,这会对经济本身产生反作用。比如,缺乏信心的人往往倾向于减少消费和投资,进而进一步促使经济下行。
“预期更差”以及“经济数据更坏”,形成了一个能够自我实现的循环。这个循环一直持续,直到市场预期低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而在这个时候,经济也就正式触底了。
人们看到经济数据并非想象中那般糟糕,信心得到极大提升。接着,资产价格开始从谷底慢慢回升,与此同时,人们的预期也逐渐提高。
人们的预期上调会推动经济反弹,这反过来又会构成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这个循环会一直持续,直到预期高到不切实际的程度,那时经济就会触顶。
上述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立足之处:其一,市场预期的变动速度始终比经济数据的变动速度要快,经济自身具有迟缓性且带有极大的惯性,然而人们的预期却能够每天都有所不同。其二,人们的信心能够对经济产生反作用,在周期性层面是这样,在长期层面也是这样。
如果经济本身没有产生不可调和的问题,那么人们的信心能够拉动社会总需求,进而促使经济进入另一个增长周期。凯恩斯主义者必然会对这套理论格外欣赏,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大部分宏观经济问题都能够通过“总需求不足”来进行解释。
依据“反身性原理”,当人们的信心普遍得以恢复之后,紧接着便会迎来需求的复苏。在当下的中国,最为重要的需求主要有两项,分别是房地产以及可选消费(Discretionary Consumption)。倘若将房地产问题予以解决,那么房企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也就随之得到了解决;而如果把可选消费问题解决了,经济的内生活力问题也就得以解决了。在短期,更重要的恐怕是前者;而在长期,更重要的显然是后者。
去年 9 月到现在,对于房地产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态势。情况看上去确实相较于最低潮时期有了回暖的迹象,然而,回暖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呢?部分数据表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其二手房交易出现了复苏。即便这是真实的情况,但也并不重要,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难题向来不在一线城市,而是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域。对于这个问题,我并非专家,所以不会对此过多进行阐述。然而有一个确定的情况是:广大的低线城市依然在期盼着需求的复苏。
消费方面,特别是可选消费,在 2025 年或许要肩负起前所未有的重要使命。实际上,2020 年到 2024 年的中国经济是由出口来推动的。中国的贸易顺差连续多年达到历史新高,贸易顺差占 GDP 的比例接近 6%。即便贸易战没有发生,出口也难以再给经济带来更大的贡献了;而现在新一轮的贸易战已经开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估计不会停止。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处于这样的状况:
2009 年我刚加入证券行业,当时所在的券商年度策略会主题为“经济转型,消费崛起”。之后我在多家不同的券商间辗转,这些券商有的是外资,有的是中资,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向客户强调,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必定会转向由国内消费驱动,因为所有大型成熟经济体都是如此。十六年转瞬即逝,中国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消费类企业,尤其是消费互联网公司。然而,总体来看,与“国内消费驱动型经济”的目标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最近一个多月,资本市场和媒体充满信心的迹象有很多,像 DeepSeek、Manus、宇树科技等。这些迹象固然证明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但都无法对经济数据起到立刻就能看到效果的拉动作用。严格来讲,恐怕再过几个季度,它们的拉动作用依然很有限。这里涉及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从 2022 年底到现在,美股市场以及美国风险投资不断取得进步、持续创出新高,其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仅仅是因为 GPT 引发的人工智能热潮吗?
显然不是这样。在 GPT 突然出现之际,美国经济呈现出令人诧异的坚挺态势。2022 年初,市场都认为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到 2023 年下半年,市场的一致预期变为美国不会有衰退,或者只会经历极短暂的衰退;如今我们都能看到,过去三年美国并未经历衰退。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通货膨胀过高,这使得基层人民的“痛苦感受”加剧了,而这正是经济过热的象征之一。简而言之,美国资本市场不断攀升的原因是“AI+经济”,其中“AI+经济”中的前者负责提供长期的想象力,后者负责提供短期的业绩。
对于中国资产来说,当下最重要的问题转为经济本身了。实际上,无论是谁,不管是不是投资者,都会对经济本身予以高度关注。近期我接连结识了两位应届毕业生,一位正读大四,一位正在读研三;可想而知,当提及 DeepSeek 等人工智能相关话题时,他们最为关心的都是“这是否会让今年的工作更容易找到一些”。很遗憾,他们的专业与人工智能距离很远。他们恐怕无法得到直接帮助,这也是绝大多数年轻人所面临的局面。(注:在长期,关于人工智能究竟会创造岗位还是毁灭岗位这个话题太复杂,在此无法展开讨论)
总之,只有将国内消费,尤其是可选消费需求充分调动起来,经济这整盘棋才算下活了。这个过程是缓慢且具有结构性的,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显著成效。资本市场肯定会特别关注一些重要的“先行指标”或者“指导性数据”;至于到底是哪些数据,因为我不研究宏观或策略方面,所以就不妄加评论了。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每个季度以及每个月,资本市场都在期待消费领域能够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目的是维持由信心驱动的“反身性”正循环。
希望消费行业能够交出这样一份好看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