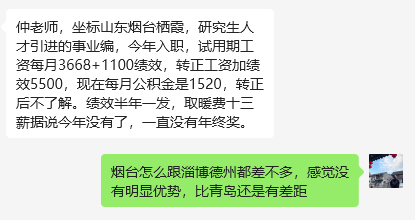邱阿姨,现年六十八岁,独自生活。在约十年前,她的配偶不幸因病离世。为了照看邱阿姨,她的儿子一直未婚无子,然而,三年前,他同样因心脏疾病离开了人世。
邱阿姨独居养老,原本拥有房产一栋、25万元理财存款,以及每月领取的退休金。但两年前,她的哥哥发现,邱阿姨不仅把25万元存款借给了同小区的一位“干儿子”,甚至还将房产抵押,并向银行贷款85万元。这笔贷款几乎全部被认定是借给了那位所谓的干儿子。而那位干儿子却否认贷款与自己有关,并已搬离了小区。2025年8月,贷款即将到期。
邱阿姨的亲戚们觉得她的精神状况不正常。自从借款事件发生后,她的哥哥便带着她去医院进行了检查,结果初步判定她患有器质性精神疾病。目前,她的兄弟正在为她办理残疾证。为了更好地照顾邱阿姨,兄弟姐妹们曾计划将她送到养老机构,但她坚决拒绝,她坚信“越早去那里,就越早离开人世”。
哥哥觉得邱阿姨性格固执,丧子之后更是变得让人难以理解,劝说她也无济于事。在向“干儿子”借款之前,她就已经从“干女儿”那里买下了满满一桌的保健品。
--85万元贷款去哪儿了?--
先后借款110万元?
“干儿子”称借款为25万元

邱阿姨的哥哥起初是通过别人的话得知“邱阿姨最近有些异常”。他的同学和朋友纷纷打电话告知他,邱阿姨正四处筹借资金。其中一位朋友回忆说,邱阿姨曾试图向他借40万元。
邱阿姨回忆称,她奔波于各个角落筹借资金,目的只为向陈某提供贷款,然而,具体借款数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从银行流水和微信转账记录中可以看出,从2023年1月17日至同年8月24日,邱阿姨向陈某的转账总额达到了40.38万元。此外,在邱阿姨的家中,她还发现了5张署名为陈某的借条,这些借条所列出的借款总额共计50万元。邱阿姨明确表示,她仅向陈某借出了25万元,这笔钱是她个人的银行理财存款。对于超出此数额的转账记录,她并未提供任何说明。至于借条上的金额,她的解释是,陈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为她开具借条。
邱阿姨不仅停止了转账,还把房产作为担保,成功贷得85万元。她表示,这笔资金几乎全部借给了陈某。这笔贷款是以邱阿姨个人的名义办理的。到了2023年8月1日,邱阿姨又成立了一家名为“纺织品经营部”的企业。紧接着,她便以该企业经营所需为由,再次以房产作为抵押,申请了贷款。在同年的8月31日,贷款得到了审批并成功到账,紧接着,那笔85万元资金便被悉数转移到了另一个账户中。
邱阿姨与陈某之间的联系,亦是一笔难以理清的账目。据负责该笔贷款业务的银行经理回忆,贷款发放之后,邱阿姨曾向银行透露,这笔贷款的真正用途是借给她的“干儿子”陈某进行资金周转。回忆起这笔贷款的介绍,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提到,陈某携带着邱阿姨前来寻求帮助,他亲切地称邱阿姨为“干妈”。实际上,这笔抵押贷款是由邱阿姨借给陈某的。当时,他还特意提醒双方别忘了签订借条。此外,邱阿姨的哥哥也表示,邱阿姨视陈某为“干儿子”。在此之前,她曾对家人的干预表示反对,认为兄弟姐妹之间可能会为房产产生争执,而陈某作为干儿子则能帮她养老。
邱阿姨明确表示,“我从未将他视为干儿子。”她进一步说明,在办理贷款期间,陈某确实自称是“干儿子”,但她并未对此发表任何意见。

邱阿姨签署的贷款相关合同

6月28日,记者成功与陈某取得联系。陈某表示,邱阿姨曾告诉他,她孤身一人,儿子已故,丈夫也已离世,并认他为干儿子。然而,陈某透露,他总共借款大约25万元,只签过一张借条,并承诺半年内归还,但时间尚未到达,邱阿姨便催促他还款。在未果的情况下,邱阿姨尝试向银行申请贷款,最后,邱阿姨找到了贷款中介公司,并通过经营贷的方式向银行申请了借款。
他表示,邱阿姨曾希望他一同参与贷款事宜,并提出让他协助担保一笔85万元的贷款,然而他婉言谢绝了。据他所述,截至目前,他已经偿还了几万元,“她通过微信转给我25万元,我已偿还相应数额,这一点我有明确的承诺。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利息如何,我都能承担。但现在,若让我独自承担这85万元,那是不现实的。”
--“有求必应”的借款?--
家人曾劝阻不要抵押房产贷款
借款后被诊断为器质性精神病
邱阿姨讲述,陈某不过是住在隔壁的居民。他们首次相遇,就是陈某向她开口借钱。她回想,那是在2023年,陈某敲响了她的门,自报家门称自己住在同一栋楼,从事工程工作,急需资金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不论多少都行。在此之前,邱阿姨并未见过陈某,也未曾想过要前往陈某的住处进行核实。只是匆匆一面,她便答应了他的借款请求,“我自身也曾身处工厂,负责车间管理,对他感同身受。”陈某对此借款原因,确认其真实性。
邱阿姨在讲述借款经历时,表现得极为慷慨。陈某初次向她借款时,直言“无论多少都行”,于是她便开始四处筹钱,甚至将自己用于理财的25万元也全部借给了陈某。
她之所以选择将房产抵押给银行贷款,是因为她需要为已故的丈夫和儿子举行仪式,手头缺少三万元。于是,她向陈某催促还款,而陈某则提出可以协助她借款。在陈某的提议下,她同意了。她回忆说,陈某曾叮嘱她不要将此事告知他人,她也就答应了。她认为这是陈某在维护自己的面子。

在整个贷款流程中,她对自己的情况一无所知,完全依照别人的指示行事,“他们驾车将我带到了一个我未曾涉足的地方”,接着,“我被要求签署了大量文件,而我并未细看”。当85万元的贷款到账并转出之后,她声称陈某曾给她转了3万元,这笔钱据说是用于她所说的仪式。然而,当陈某再次提出需要资金时,她又转给了陈某2万元。
那位负责处理该笔贷款的客户经理回忆,他与同事一同亲自前往邱阿姨的公司进行实地考察,发现她在退休前曾在纺织厂工作,考察过程中,她对办公场所和员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不仅如此,她还出示了购销合同来证明贷款的用途。邱阿姨也表示,这一切都是中介公司和陈某的要求,她“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去执行的”。
在这段时间里,并非完全没有“预警”出现。邱阿姨的弟弟回忆起,她曾拨打电话向他咨询,关于将房产抵押用于贷款,并将这笔贷款转借给他人周转的事宜,是否可行。他还特别提醒她,绝对不要采取这种做法。
邱阿姨的哥哥回忆道,在2023年8月1日那天,他多次尝试给邱阿姨拨打电话,费了很大劲才最终接通。在通话中,他询问邱阿姨为何不接电话,并得知她当时所在的位置。随后,他听见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男声指示说:“你就告诉我说你在吃饭。”邱阿姨据此回应了对方,随后便挂断了电话。由于没有录音证据,记者无法核实通话的具体内容。邱阿姨本人则承认了这一情况,但她对于具体的通话日期记忆并不清晰。通知文件表明,在2023年8月1日这一天,邱阿姨提交了相关申请,以登记一家公司,该公司日后将作为贷款申请的依据。
在讨论贷款事宜的过程中,邱阿姨的亲属与银行职员未能就相关事宜达成共识。亲属认为,邱阿姨的精神状况存在问题,这一点显而易见。而银行职员则指出,至少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她并未显现出任何异常表现。
关于那笔85万元的贷款具体事宜,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涉及客户的个人信息,他们不便接受采访。
哥哥在2023年10月发现了这笔抵押贷款,随后便带着邱阿姨前往了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在那里,诊断书明确指出邱阿姨出现了严重的焦虑症状,初步判断为器质性精神病。她的病史包括记忆力明显下降、情绪持续低落以及行为紊乱,这些症状已持续了两年。鉴于精力有限,哥哥还在权衡是否应该协助邱阿姨就85万元的债务问题提起法律诉讼。


邱阿姨被初步诊断为器质性精神病的病历
--“无聊”的独居生活--
买保健品,被指还为理疗、旅游消费
自称“没孩子,留着钱干嘛”
在陈某的叙述里,邱阿姨并未将所有财产都借给了他,她的资金主要用于打牌、外出旅行以及接受理疗等活动。至于为何借款85万元,陈某解释称,是邱阿姨提出想要进行理疗,而这笔费用大约需要十余万元。
邱阿姨的哥哥表示,她曾经“遭受过理疗的骗局”,然而在借款发生之前,她对于借款的具体金额“连自己都难以说清”。在他看来,邱阿姨性格十分“固执”,难以说服。在这次涉及养老房产的借款发生之前,他就已经察觉到邱阿姨的异常行为,而理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哥哥回忆说,这一异常情况是在邱阿姨失去儿子之后出现的。她之前曾加入了一个老年旅游团,旅行归来时带回了所谓的旅游“特产”。更为显著的是,她的客厅一角堆放着各式各样的保健品,诸如药酒、各种植物提取的原浆或胶囊,此外还有一台饮水机和一部吸氧机等。


邱阿姨家中堆满了各种保健品
邱阿姨并不愿意提及这些保健品的来历。据哥哥所述,这些保健品多数是那位自称为邱阿姨“干女儿”的推销员所推销的,哥哥曾试图寻找这位推销员,希望他能停止向邱阿姨推销这些保健产品。然而,邱阿姨总是反复强调:“你不要去找人家。”至于她购买这些产品的具体情况,她只是简单地说:“不要问了。这些都是我自愿的,没有人强迫我。”
邱阿姨与热衷于运动的哥哥截然不同,她并不怎么喜欢外出。由于腿脚不便,她常常需要他人的搀扶。哥哥劝她:“您应该多出去走走,这比购买任何保健品都要来得有效。”邱阿姨陷入了沉默。当哥哥询问保健品究竟有何效果时,她回答道:“推销时声称有二百种好处,但实际上使用后并没有什么效果。”哥哥继续追问:“那您为何还要购买?”邱阿姨再次沉默不语。
私下里,她向记者透露,她购买保健品的原因在于“健康至关重要”。她表示,这一观念是在丈夫和孩子的离世后领悟到的。她精通手机操作,经常通过电视和手机短视频来学习大健康知识。记者曾就她是否遵照医生建议服用精神类药物进行过询问,邱阿姨回应称偶尔会服用,“是药三分毒。”在健康问题上,她信心满满:“在我看来,医生的知识不如我丰富。”
在器质性精神病的初步诊断之后,哥哥提出要让邱阿姨搬到养老机构居住,但她却坚决拒绝,表示:“越早去那里,就越早离开人世。”
邱阿姨独居,她感叹:“生活颇为乏味。”这并非她昔日的养老设想。近年来,她一直在寻觅养老之道。她曾设想:“最好是能领养一个孩子。”为此,她曾咨询过是否可以收养孙子,却遭到了拒绝。今年,她的兄弟正为她申请残疾证,意图成为她的法定监护人,不过他们的住处相隔甚远,平日里来往并不多。她也曾考虑过再婚,但至今仍无进展。
她似乎有些消极应对。在多次借款甚至抵押自己养老的住所之后,她心想,“既然我已经没有孩子了,留钱又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