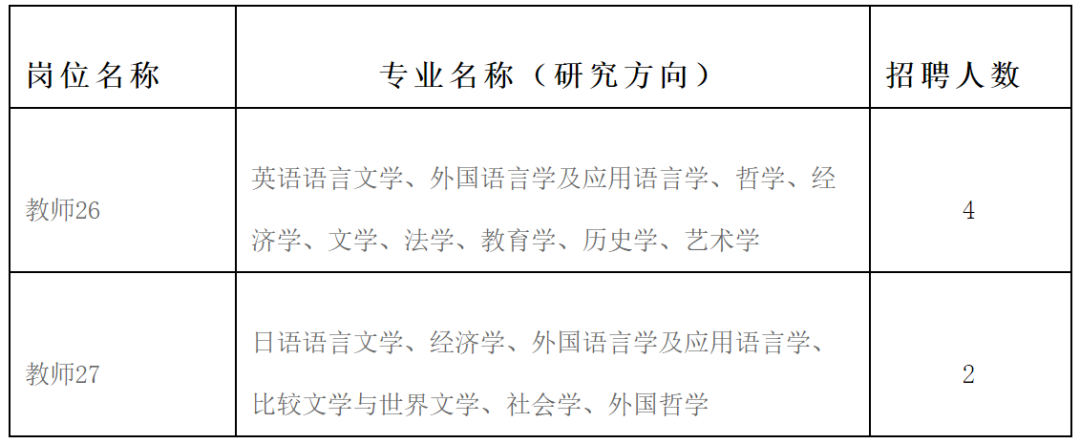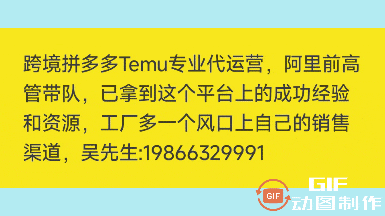17世纪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航行日志中不仅记载了充满挑战的航行经历,还详实记录了众多与市场、商品及利润相关的数据。在东印度公司的视角里,整个世界仿佛是一本记录着可开发资源的账本。异国风情与不同人种被简化为可量化的资产,用会计和交易的语言进行概括,而文化差异也被转化为贸易中易于识别的标志。这种观察世界的方法,被称作“商业视角”。
芒特马蒂大学的青年学者布兰登·泰勒近期对东印度公司的早期档案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其贸易言论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些言论如何逐步提升,最终转变为英国殖民事业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

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然而,与当时同样重要的竞争对手弗吉尼亚公司所获得的特许状相比,尽管两者都基于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基本法理结构,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状却以宗教和道德为外衣,凸显了其事业的基督教特质。该公司将原住民皈依视为最重要的任务,同时,它也对“追求利润是否合乎道德”产生了疑虑。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中并未包含此类规定——他们并未将东印度群岛的居民视为有待改造的“无主地”所有者,反倒是将他们视为可以交易的盈利群体。
自其成立伊始,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言论便显现出更为清晰的全球视野,其核心宗旨即为追求利润。该公司早期的航行记录已开始从经济角度描绘世界图景。《东印度航程实录详述》这部匿名著作,详细记载了1601年2月,詹姆斯·兰开斯特爵士所领导的首航历程。这部于1603年问世的编年史详尽记载了首次航行的种种艰难险阻:连番遭遇的风暴、致命的事故,以及夺走众多水手生命的疫病。这位航海家对各地的居民和文化形态持续保持着关注,并且细致入微地记录了船上的货物清单。

在简要介绍松巴哇人之后,随即转向了对该岛屿经济价值的评估:这里盛产适合制作主桅杆的优质木材。当航海者们拜见苏门答腊国王时,盛宴上那些熠熠生辉的金器、价值连城的钟铜以及来自中国的瓷器,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尽管对文化习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最终讨论的还是商品的交换价值。
这些话语中蕴含着对民族学的探索热情以及对商业价值的考量,正恰表明了早期东印度公司的记录者们仍在探索理解异国文化的途径。至1612年,这种摇摆状态不复存在。当年的科弗特报告则显现出了更为周密的商业推理。

《真实奇闻录》一书由罗伯特·科福特所著,是东印度公司早期的重要资料,书中详尽记载了船员在航行途中的交易、物品交换以及损耗情况。同时,该书也真实地展现了公司对东印度群岛当地族群和国际贸易的复杂性的极大不熟悉。书中有一段典型的描述:他们探访了“班尼亚人大城拿德巴利”,发现那里的市场十分繁华,铜器琳琅满目,随后便列举了各种商品。当地的风土人情已经不再引起记述者的兴趣,他心中所想不过是“这里的布匹肯定热销……金银矿藏丰富,与这些善于经商的人交易非常愉快”。
“商业凝视”通过贸易的视角重新构建了认知的新环境和社群的架构。它遵循价值掠夺的原则,对感官体验进行了重新组合——那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不再是令人惊叹的生态景观,而变成了有待开采的木材资源库。这种变化预示了东印度公司未来运作模式的初步形态,商业认知也逐渐转变为一种控制手段,可以说,贸易的修辞手法奠定了英国海外殖民活动的基础。
这种对世界的观察和记录方法体现了那个时代新兴的世界观:认知活动受价值规律所主导,文化差异则通过贸易体系来解读。因此,毫不奇怪,一百年后便出现了笛福(1660—1731)——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先驱。在伊格尔顿的《英国小说》一书中,提到了笛福曾撰写过一篇名为《贸易的神圣性》的文章。

笛福把自然本身比作一位资本家,它拥有着难以捉摸的资产阶级智慧,创造了能够使物体漂浮的水面,使我们得以建造用于贸易的船只;它悬挂着星星,为商人指引方向;它开辟了河流,使得我们能够直接抵达其他国家,获取那些可供掠夺的资源;它使动物驯服,使我们能够将它们作为工具或原材料使用;它精心设计出崎岖的海岸线,以便我们建造避风的港口;而各种原材料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极佳的分配,使得每个国家都有商品可售,也有商品需要购买。
此刻,用商业视角审视世间万物,它已融入文学领域,成为英国当代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