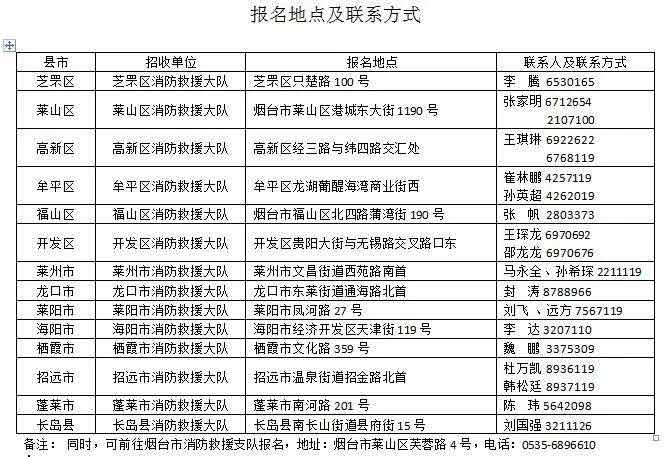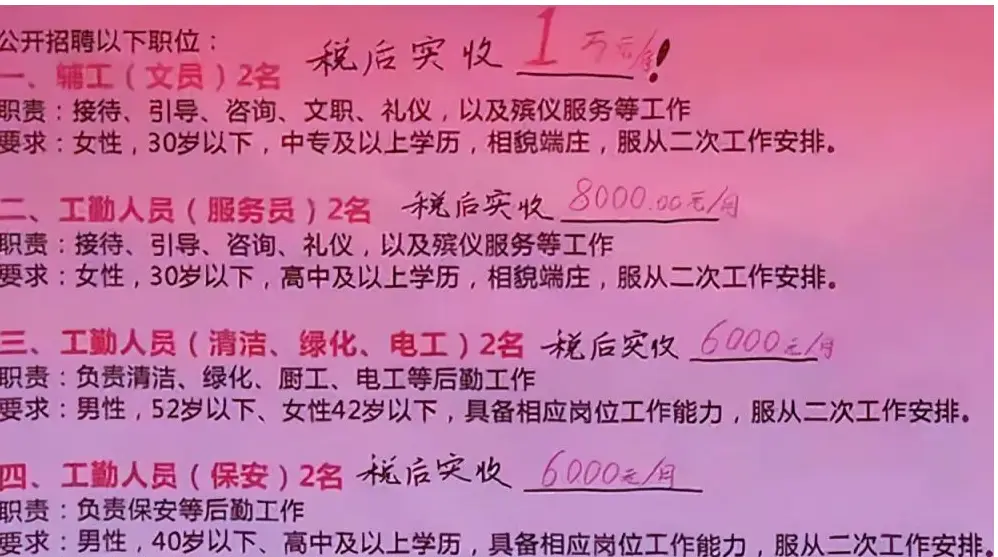桃溪发源于鹅峰山褶皱处的九股山泉,顺着山势的起伏,时而被冲撞得跌宕,时而又被逼得转折,之后又环绕着坑头村缓缓流淌。比桃溪更加曲折的,是坑头村通往山外的七条古道,它们几乎都以荒废或破损的状态,一直延伸到村庄历经千年的岁月深处。
婺源地区把“小溪”称为“坑”,或者表示“溪水穿行之地”。坑头村背靠山峦面朝溪流,桃溪河上设有众多古桥,河岸两侧的房屋排列密集。这些古桥仿佛是古老村落留下的一个谜题,它们既让行人通过,也承载着自身的历史。在崇尚读书入仕的时期,坑头村将荣耀寄托于桥梁之上,村中36座桥梁,是36位读书人成功后捐资修建的善举。显然,每一座桥都以长虹卧波的形式,牵引着一个“书香门第”。

应该是在很久远的时代,能够长久伴随桃溪水流动的,就是那熏陶人的书卷气息了。只有一百来户人家的坑头村,又有着多么深厚的求学氛围呢?我沿着桃溪往上游走,在坑头村仔细地探寻。和村里弯腰的老人谈论村庄的历史,他讲起的话总是离不开近旁的古老石桥,还有“一家之中有九位进士,六部里有四位尚书”的辉煌事迹。
崇恩桥、迎恩桥、登崇桥、德济桥、瑞滋桥等桥梁的名称,或许寄托了出资者的某种心愿,我在当地的历史文献和家族记录里,确实发现了他们的事迹:从宋朝到清朝,坑头村总共走出了15位科举成功者,以及126名朝廷官员,并且留下了156部书籍供后人阅读。

在坑头的村史记录中,我识别出一位文人地位非常崇高,他便是曾参与编纂《明伦大典》、先后在“四部”担任尚书职务的潘潢。他著有《论语阙疑》《乐成刀笔》《五宗考义》《朴溪集》等诸多作品,流传至今。
潘潢在古籍中记载,少年时期父亲首先将他送往私学接受教育,后来又进入县学继续深造。他年少时曾应私塾老师“鸿是江边鸟”之对,答出“蚕为天下虫”。而所谓“潢承家学”,其实是在他步入仕途之后才有的提法。没想到的是,潘潢在四个“部级”机构中都有过任职经历,相关内容在《婺源县志·人物传》里只是简略提及,但书中特别记载了他担任福建学政期间,严格规范学风,设立品行与学业两本记录,并且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明白,编修志书的人对重视教育的先辈怀有敬意,他们清楚明白,正是因为婺源存在“十户人家,没有不读书的”“山中茅舍书声传,放下农具去应试”的“缘由”,才形成了长久以来“耕田读书世代相传”的“结果”。

古代,坑头村有很多供读书讲学或文人聚会的地方,比如启元书屋、同异轩、文昌阁等,但这些地方都在岁月中荒废了。不过,潘潢书屋至今还在,它前面的池塘水依然很干净。
潘潢书屋始建于明朝弘治时期。到了嘉靖三十六年,也就是1557年,婺源县的郑国宾知县,因为敬仰潘潢曾从桃溪走出并进入朝廷为官,便在他读书的地方题写了匾额。这块匾额上写着“太宰读书处”四个字。郑国宾知县还将这块匾额,高高悬挂在了书屋的正门之上。

根据题匾上镌刻的年份判断,那个年代潘潢已经离世了。由于年代久远,郑国宾和潘潢之间是否产生过联系,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以佐证,但这并不妨碍那块匾额在后代中被视为荣耀的象征
天色已晚,不知不觉到了下午时分。潘潢书屋正对着桃溪和山垄,门头上的匾额在光线照射下,像一道深深的沟壑。路边站着一位年轻女性,她蹲下身子,以书屋的门楼为背景,给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儿拍照。在她们满脸笑容的时候,我感觉到一股文化气息在偏僻的山村里慢慢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