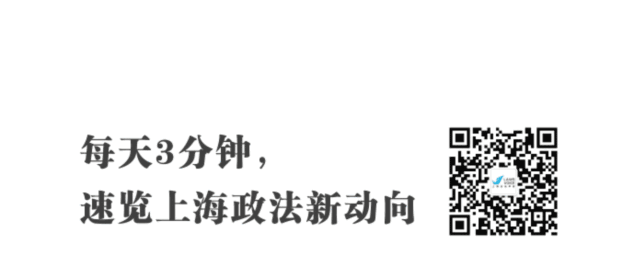“这是少数几次在网络风波过后,对立双方能退一步、共同做出改变的案例之一。”
作者:李欢
编辑|翟文婷
顾客接过于洋递来的一杯Manner咖啡,发现并不是自己点的款式。
于洋赶紧提议,“我再给你泡一杯。”结果对方却自责不已,说自己可能点错了,并安慰道,“辛苦你了。”于洋受宠若惊,尴尬地说道,“我很忙,可以好好服务大家。”
于洋是深圳曼娜门店的咖啡师,在店员向顾客扔咖啡粉的事件发生后,他告诉新梅晓,自己明显感觉到来买咖啡的顾客变得很有礼貌,自己也忍不住多注意一下自己对顾客的态度,双方的礼貌中甚至透露出一丝谨慎。
这是少数几次在网络风波发生后,对立双方退一步、共同做出改变的事件之一。
正是这件事,让之前不被重视的咖啡师群体被关注起来。这几年,国内连锁快咖啡发展迅猛,里面的咖啡师们戏称自己为“牛马咖啡师”、“咖啡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人”。
问题是这并不是咖啡品牌创始人的初衷,利用咖啡作为媒介,人们可以相互交流、互动,这才是咖啡最大的魅力所在。
说到底,这都是模式的悲剧。
1. 陷入“咖啡电子工厂”
曾在Manner工作过的咖啡师愿意把这个连锁品牌形容为“咖啡电子工厂”。
在他们眼里,这里是高效培养咖啡师的地方,只要留在这里坚持下去,就会是市场认可的优秀咖啡师,而一旦离开,就意味着“一家大公司在回馈社会”。
传统观念里,咖啡馆是让人放松的场所,但如今,尤其是受到9.9元冲击,咖啡连锁店却变成了一个让人紧张的地方。
经过在Manner上海总部三个月的培训,余洋是少数通过理论考核的员工之一,掌握了订货逻辑、意大利基础产品SOP等理论内容,但实操部分还是没通过。
从上海回深圳后,他甚至发现预约实操考试变得很困难。“深圳很多人一两年都没考上,我回深圳半年了,三个月才预约一次。”于洋告诉《新梅拂晓》,他知道考试难,但没想到这么难,他预约了两次,但都没能通过。
考试的一个明确要求就是时间和效率,俗称又快又好。
对于意式咖啡,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调整研磨度,粉重、时间、液重都要标准。于洋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场赌博,“考官会把研磨度在范围内弄乱,10分钟内你有4次调整的机会。”
通过这些测试后,你还会被给予另外十分钟的时间来制作拿铁艺术。无论浓度、粉末重量、奶泡厚度和温度都必须在标准范围内。拿铁艺术图案还必须面向标志和满杯。
更严苛的考验是手冲咖啡。从接单开始,一边亲手冲泡咖啡,一边给顾客介绍咖啡风味,然后推广公司的电商平台和公众号,告诉顾客可以自带杯子和罐子。整个过程必须在8分钟内完成。
这只是考核中制作一杯咖啡的时间要求。实际日常工作中,通常一个人负责一家店。一位咖啡师在小红书上发文称,他目前在Manner的工作效率是“8小时制作500杯咖啡”。这意味着制作一杯咖啡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还是在使用半自动咖啡机的情况下。
于洋的店需要每天稳定实现8000元以上的营业额,才可以再增加一个人。按照于洋告诉我们的10个小时工作时间,就意味着每小时营业额要达到8000元。按照Manner每杯25元的均价计算,于洋每杯的生产时间要达到1.9分钟/杯。
我们从M stand和星巴克的咖啡师那里了解到,2分钟/杯是咖啡师制作一杯咖啡所需的最大时间。Manner的时间效率也差不多。虽然不同媒介的测量口径不同,但大多数都分布在2-3分钟之间。
三次实操考试中,于洋在一些细节上出现失误,未能通过,几经挫折后,他心里很是郁闷,有时候,他会打开BOSS直聘来缓解压力,然后静下心来,照常去店里上班。
他认识的同事大多是90后,他们就像一个个孤岛,每天重复着收银、接单、煮咖啡、发单、打扫卫生……
于洋性格沉稳,对咖啡没有太大的热情,只是一份谋生的工作。平日里,虽然一个人在店里,心情很压抑,但他也会想办法缓解压力。闲暇时,他会和熟客聊聊天,或者用店里的手机和店里群里的朋友聊天。
他现在最大的希望,除了通过剩下的考试,就是店里的日营业额能稳定在8000元以上,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再有合伙人来支持店里的发展,这样或许自己才能有更多的喘息空间。
2.模特的悲剧
在M stand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余文入行较早,能明显感受到咖啡行业这几年的变化。
2018年前后,余文还在上大学,因为喜欢咖啡,他利用课余时间在星巴克兼职,两年时间,他从系绿围裙变成了系黑围裙。
当时,咖啡品牌与顾客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在他工作的星巴克,每周一都有一场固定的咖啡讲座,由穿着黑围裙的咖啡师主持和讲解。而在此之前,星巴克要求从绿围裙晋升为黑围裙的咖啡师必须通过手冲讲座考核。
因为这些预约的观众都是咖啡爱好者,他们会跟咖啡师互动,提问,所以主咖啡师必须能表达,懂咖啡。
星巴克的战略重点之一就是让顾客对星巴克产生归属感,即顾客和咖啡师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关系。比如,主动叫出熟客的名字,这些细节会增进双方的关系。
余文向新美黎明回忆,咖啡师在准备讲座时,要兼顾讲座的故事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轮到他讲课时,他会提前准备,查阅很多资料,从咖啡豆的故事到什么咖啡配什么口味的蛋糕,他都会考虑到。
大学毕业后,宇文离开星巴克,成为一名程序员。工作一年后,宇文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因为他还是喜欢咖啡,于是宇文重回咖啡行业。一段时间后,他来到了M stand。
但当咖啡店在中国流行起来时,一切似乎都改变了。
当各大咖啡连锁品牌都想成为中国版的星巴克时,他们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瑞幸的例子让大家意识到,性价比与本土风味相结合的即买即走的“快咖啡”业态才更符合中国国情。
这也决定了门店咖啡师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与星巴克强调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
Manner 的顾客都是追求时间与效率的都市白领,即点即走模式带来的宿命感让咖啡师秦桐意识到,在制作速度的要求下,她精心制作的咖啡未必会被顾客重视,她理想中的场景——与顾客建立友谊般的沟通模式——是不可能实现的。
两年前,她以“大Q同学”的账号在小红书上发文,讲述自己从转行做咖啡师,到一年后离开咖啡师行业的历程。除了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她还要面对公司规章制度和顾客的双重夹击,比如“外卖平台上的顾客投诉,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产品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外卖小哥一直辱骂她高峰时段没接到单。”
工作看起来并不难。秦桐说,Manner的SKU很简单,所有门店都使用半自动咖啡机,公司有自己的一套研磨参数。咖啡豆和材料的选择、门店订单,一切都由公司主导。
但她对幕后的一切却一无所知。选豆、冲泡、萃取,用什么方法冲泡,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如何调配……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秦童的脑海里,她一直想学,想搞清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
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缺乏价值感,陷入了无休止的重复。于是她决定离开。
此外,这一代咖啡连锁创业者都是科技的信徒,更在乎可控的标准化,而不是自由的浪漫或给予员工自主权。
曾就职于Tims、M stand咖啡品牌的王玲告诉《新梅黎明》,刚从Tims来到北京M stand时,她工作积极,每天都渴望进步,因为她的梦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
不过,经过一轮店长变动后,店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店长上任似乎并没有让工作秩序变得更有序,原本简洁的工作日志填写变得繁琐复杂,最极端的时候,她每天要上传几百张门店现场照片。
让所有同事都感到不舒服的是,视频(监控)审计越来越频繁,一不小心就会被罚款、扣钱。更让大家感到心寒的是,监控的清晰度非常高,员工手里拿的是什么,说的话,监控都能看得清、听得清。
3. 成为原创咖啡师
在经历“模特悲剧”引发的舆论风波后,曼娜咖啡于6月21日晚间在微博公开发表声明,称公司了解到相关情况后,第一时间向顾客道歉,同时也对涉事的咖啡师合伙人进行了安慰。
道歉声明中还提到,公司管理层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将重新审视自己,将在员工培训教育、门店运营安排优化、咖啡师伙伴日常关爱三个方面积极整改调整。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人发帖称,Manner顾客冲突事件发生后,看到上海一家Manner咖啡店的点单柜台上贴着一张长长的横条,上面写着“店里只有一名咖啡师接单,高峰时段订单集中,等待时间会更长,请大家见谅!!!”
Manner的一位咖啡师也表示,自己收到了公司的通知,准备开通“合作伙伴反馈渠道”。这一渠道将于2024年7月1日正式开通,设有企业微信和邮件两种反馈渠道。目的是“更好地收集合作伙伴的意见和建议,助力优化运营”。
于洋告诉新梅黎明,在公众渠道宣布的前几天,公司还启动了一项匿名意见调查,合伙人的反应非常热烈,提出的建议也很大胆。
除了意见渠道的开通,风波发生后,于洋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公司的门店巡检停止了,也没见到有人来巡查。
此前,有的门店每周要接受三次检查“查卫生、查商品、查一些奇怪的地方,还要检查单据和干货的保质期”,这些审计内容也超出了门店监控的范畴。
但这些变化似乎并不足以改变王令和于文的决定,离开M Stand之后,两人各自找了一家独立的精品咖啡店。
让他们欣慰的是,这两家咖啡店的老板都是咖啡方面的专家,相比于连锁咖啡品牌,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和精力去了解咖啡的来龙去脉。
王玲现在工作的咖啡店,位于北京一条胡同深处,来这里的顾客全都是回头客。每天出品的咖啡量并不多,但更注重咖啡的品质和店面的经营,连咖啡豆都是店家深度烘焙、精心挑选的。
与以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板对员工的关心和体贴会更加人性化,忙碌了一天的王玲下班后,总会收到老板一句贴心的问候。
渐渐地,王玲的心里开始萌发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她似乎找到了作为一名咖啡师最理想的价值观——不再被监控摄像头时刻监视,对老板的了解和信任越来越多,与顾客的联系也更加稳定深入。
作为一家立志走精品路线的咖啡品牌,这也是Manner的初衷,自创立以来就坚持走直营路线,即便近两年有加盟商由直营转为加盟,Manner也丝毫没有动摇。
无论是严格考核还是密集审核,Manner始终想把品质、服务和效率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任何连锁企业都渴望实现的理想,但也常常将它们置于“规模、品质、价格”的不可能三角中。
每一个曾经向往品质、追求咖啡的咖啡品牌,或许都和Manner创始人韩玉龙有着同样的初衷,“我不要机械化,也不要抹杀每一个咖啡师的个性”。
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差距,或许这场冲突将会是品牌思考如何还原“咖啡师原本的面貌”的最好机会。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于洋、秦桐、王玲、于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