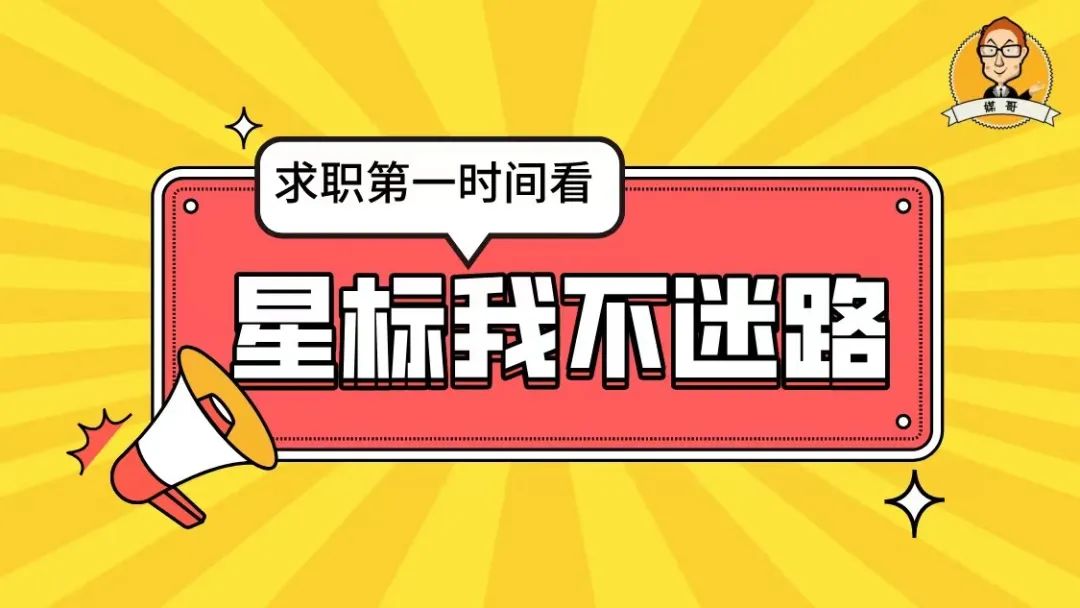《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张俊峰著,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出版,198.00元
我一直认为,张俊峰教授所在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无论是管理体制、学术作风、团队结构,还是资料积累,都是国内同类学术群体中最具活力、最有实力、最有凝聚力、最有竞争力的团队之一。张俊峰秉承乔志强、兴隆等教授开创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山西宗派,先成长后成熟,如今他又担任中心新任负责人,带领一批雄心勃勃的青年才俊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作为不同年龄的同事、朋友,我很高兴看到张俊峰在如此优质的学术平台上施展才华。我被要求为他的新作《史图碑刻: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写一些感想作为序言,当然,我视之为荣幸,不敢也不想拒绝。

山西省夏县南大里乡赵村青龙河石盆清代碑拓本

首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想必是“图文碑证史”这四个字对于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特殊意义。从理论上讲,“图碑证史”既非新事也非罕见,一般可视为类似于“双重证据法”的一种资料使用形式,即搜集、整理某一地水利碑刻的拓片、复制品、图片和实物,提取其中的图形信息,根据其反映的内容对某一地或某一类水利事件进行归纳,对相关细节和具体过程进行深入解读,并配合其他类型资料,发现新线索,解决新问题。随着石刻文化和社会史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全国性和省级各朝代石刻资料陆续被收集出版,如北京图书馆金石学组主编的《北京图书馆历代石刻资料汇编》(1989)、《山西明清石刻资料选编》(2005, 2007)、刘泽民主编,《山西明清石刻文集》(2006、2008)。 《山西石刻全集》(2015)等。许多学者发表了范围更窄但水利主题更明确的成果,也为开展该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董竹山等编著的《洪洞、介休水利碑刻集》(2003)、李松等编著的《洪洞、介休水利碑刻集》(2003)、主编的《邵北县志及邵北史料集》(2016)、赵志宏编著的《云南水利碑刻集》(2019)、赵超编著的《黄河流域水利碑刻集》(2021)、余丽萍等编著的《大理古代水利碑刻研究》(2017)、《大理水利碑刻调查与研究》刘士英等编著的《明清时期的武威》 (2021) 因其所收录资料所体现出的高度专业水平而受到学界的好评,能以“水利图志与古迹”为依据清晰地阐述水利史研究,以补充某一区域内现有水利文献的不足之处的著作实属罕见,具有独到之处,具有开创性。

运城市稷山县档案馆张俊峰教授团队
其次,“初创”容易理解,但“创制”则需要详细阐释,因为这个含义体现在作者对水利碑刻作为一种信息形式的深刻理解上。在他看来,“碑刻”是“中国古代人们在各自区域内处理人与水的关系,进行资源配置和管理过程中产生的新事物……它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每座水利碑刻都承载着相当多的区域社会历史和长期的发展历史……可以丰富和推动以文字、碑刻为核心史料的水利社会史研究,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一些研究结论。之所以受到高度推崇,并非因为现存碑刻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是因为以下两点原因:首先,水利碑刻的产生与演变体现了“从单纯的注重文字记述到图文并茂的发展过程”,即资料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其次,碑刻中的图像有助于研究者对文字、图片进行考证,因为“图像是历史的遗留,同时也记录历史,是解释历史的重要证据。从图像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过去的图像,而且可以通过对图像的解读,探究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信息。这大大完善和丰富了现有的研究方法,“由过去注重收集文字史料,转向注重收集图文材料,特别是图像材料……以达到以图像为基础的史证目的”。“图”能否直接称为“图像”,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见下文),但明确的并以“图碑”的直接创意,弥补“文碑”意义繁琐、含糊的缺陷,并以此法贯穿全书,每章皆有少量先例,其得失,亦由同辈之见所定。


《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图录
第三,作者在众多的水利碑碣中,着重突出了“碑刻图”这一范畴,这是作者对中国水利研究学术史进行宏观把握,深刻理解“碑刻图”的特殊地位后得出的结论。宏观把握具体体现在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个时代水利研究所用资料种类和所实现目标的梳理。第一个时代从1949年到1989年,主要使用资料是正规资料,即正史中的河渠书、沟渠志、水利志、历代统一志、省志、州志、县志中的水利志以及与水利工程直接相关的专著,其目标是对水利工程、水利事业、水利技术以及河流、湖泊、水库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概述。第二时期1990年至2010年,以类型学为指导,开展区域水利社会史研究,推出了《鄯善地区水资源与公民社会调查资料汇编》(共四卷),是一系列区域水利文献与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自2010年起进一步发展进入第三时期,编纂出版了水利碑刻、渠系图册、水利契约、水事案例、渔民文书等,反映的问题更加复杂,案例分析更加细致,涉及更多领域,随着区域、跨区域水利社会研究的推进,层次更加多元的水利文献受到国际学术同行的高度评价与广泛应用。以田地型、水库型、堤防型、集中型为代表的中国水利社会的中层理论积累,也已达到“潜在地为全人类提供中国范式、中国经验”的水平。不过,笔者认为,尽管上述三个时期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但在主要材料的选取上,仍然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缺陷就是“对刻在石碑上的、与当地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史料缺乏重视”,对某一地区民众熟知的水利碑刻的历史价值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充其量只是作为水利碑刻、民间水利文献等海量文献的补充材料而已。 ”他对此十分不满,决心加以弥补,因为“‘水利图’是把江河、湖泊、泉源等为水利发展而修建的渠道、堤坝、航道、航道工程图等直接镌刻在石刻上,以便永久流传和传承的一种特殊地图。‘文献形式’即使出于完成资料种类的工具性考虑,也不应该被忽视或低估,更不要说这类资料在覆盖面和系统应用方面对于水利社会研究方法的特殊地位了。”

清咸丰三年(1853年)山西杞县古莲村《大东渠水利图碑》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西省阳曲县西张村《呼延同心二脉图说》拓片
最后,水利地图与碑刻对于水利社会研究的特殊意义在于,与包括碑刻在内的一般水利文献相比,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地方社会的结构和水利事件的实际进程。通过碑刻的运用,研究者可以发现一些水利文献中不易反映的问题,甚至反向反思碑刻作为一种民间文献在反映基层社会事实方面的一些特点。舟州古堆泉地区西村、白村刊刻的两块《古水全图》碑刻就是典型的例子。两块碑刻传递的信息非常丰富,都是以古堆泉为源头的渠道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两块碑刻的侧重点不同,但两块碑刻表达的观点却大不相同。笔者结合其他文献的记载,发现这些不同正是古堆泉流域西村和白村不同的村落历史。 、居民构成、泉水资源利用份额不同等问题,多年积累的怨气、纠葛、愤怒和不满,迫使两村村民诉诸法庭、诉诸法律。但政府的介入往往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政府只能在不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与群众讲和”往往是民间解决矛盾的方式。《古水泉图》等水利碑石的特殊功能也体现在这里。刻制的碑石反映了各村的利益。村图“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村民,无论他们识字与否,都可以通过这张地图,对西村在整个古水河流域的位置有一个清晰的印象。”白村地图也是如此,“土地纠纷是白村地图出版的主要问题。”该图出版的直接原因……也以被接受为官方记录为特征”。作者得出两个重要结论:第一,“水利碑碣并不能处理一切纠纷,图像善于呈现空间,但其表达与时间相关的信息的能力不如文字。”这可视为受限于地图、碑数据类型的局限与“不足”;第二,“水利地图、碑碣的出现,并非水利社会中各利益集团博弈、调和所产生的公认秩序的产物,而是聚落作为‘最小利益集团’对资源需求的结果。换言之,水利碑碣并非标志着水利社会秩序已尘埃落定的共同声明,而往往是借不同性质的公共权力机构的默许而发表的,是带有私人单方面宣示‘商品’的碑碣”。


《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图录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上面的总结。水利纪念碑中的“私货”是一个惊人的判断。这四个字不应该被解读成贬义,如果能指出什么是“私货”,当事人在纪念碑公布时又会“偷偷”带进多少“私人信息”?这是在了解事件整个过程、重温所有细节后才能得出的“令人心碎”的论断。我们这些“旁观者”怎么能被允许看到呢?官方文件可以公然宣扬政治正确的“公”,地方文件也可以包含家庭和自我的“私”。没想到,巍然矗立的雄伟石碑竟然在复杂的社会中运作。当事人以图文形式“将自己的私见付诸实践”,以至于“几十年来图文所形成的观念、认知和印象动摇了几百年的传统,甚至挑战了正式的书面规则”。纪念碑被赋予或应该被赋予“证实历史”重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这里可以得到充分的阐释。
这也让我想到一些阅读文献的问题。一般来说,官方文献受统治者身份、立场、价值观念、利益观念的主导,对朝廷之外的社会事务往往带有一定的偏见或怀疑,也会对很多生动的生活细节视而不见、省略不谈,甚至有意无意地掩盖、抹去、否认、歪曲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事实。但由于官方文献面对的是不可控的读者范围,所以他们行事都遵循官方的原则,官方文献的编撰者会有心理压力,要遵守公开的、正式的职业规范。而民间文献如家谱、碑文、契据、规章等虽然具有官方文献所不具备的巨大价值,但其范围有限,可控性强,大大增加了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编撰者“偷运私货”的可能性,也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使用包括地图、古迹等各类民间文献时,进行必要的史料鉴别和历史批评是绝对必要的。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藩提醒我们,阅读地方志时,要高度重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性。中山大学刘志伟提醒我们,拿到家谱时,要时刻记住“倒着读”。厦门大学郑振满提醒我们,在处理地方文献时,要尽力理清“地方逻辑”。张俊峰的四字判断,也寓意着这一点,但与大佬们的“提醒”相比,“走私私货”说更贴近现实,更精辟地展现了作者对民间社会实际运作内在套路与外在表现之间微妙平衡的深刻理解,令人敬佩,值得细细品味和欣赏。

《图碑证史:金元以来山陕水利社会新探》内页
以下几点可供张俊峰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思考。

首先,如前所述,图像的“图”与碑刻的“图”看似不同,它能够“实现视角的创新,达到通过图像来观看物质文化、社会风貌、视觉叙事历史的学术目的”。而“图”的图像,应该是指人们通过对其所指涉的事物和现象的模仿而创作出来的各种肖像、塑像、图像、雕塑等,其能指与所指几乎是重合的,只有这样的图像,才能够使我们“不仅看到过去的图像,而且能够通过对图像的解读,探寻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信息”,我们的观念、情感和认知能够与这些图像所传达的信息“短路”,迸发出火花;而图碑中的“图”多是简单的线性示意图,按照本书的描述,它们是水利存在的通道。方向图、水利发展图、资源情况图、村落情况图、沟渠引水图、民族关系图、地形分布图等等。如何在这两幅性质、手法各异的“图”中寻找到共同的逻辑,让纪念碑的“图”如同影像的“图”一样引起研究者的共鸣,使之成为“理解过去文化的方式”?视觉表象的力量在现代世界宗教与政治生活中的最佳指引,是笔者在未来实践中需要展现,并不断探索总结的。
其次,本书第六章结论部分提出了几个颇具意义的问题:“水利碑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水利碑在地方社会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为什么会出现由文字到图像的转变?”这些问题的提出,表明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在用“图碑证史”之前,还有属于图碑本身的“内史”问题需要解决,就如同我们研究家谱,用家谱证史一样。在写史之前,必须问一问家谱是什么样的文献?人们记录家谱的目的是什么?人们认为记录家谱内容有什么意义?等等。更要有自洽的逻辑,得出初步的结论。
第三,如果真要用“图碑证史”,就要力求保证能“证史”的图碑具备系列性、连续性、系统性的特点。碑毕竟不是影像,但若要临摹得极好,也只能得中庸之道。抱有很高期望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也不一定无法实现(比如西村、白村出版的两本《古水泉图》就不错,只是大致差不多)。要知道,撰写《图说历史》的彼得·伯克,用了287幅已确定日期并已完成草稿的肖像画(还不包括他手头有的332枚有准确日期的纪念章)来做这项研究。在本书写作时(1989年)的欧洲,路易十四的历史形象几乎已通过文献为众人所知,人们坚信“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而对于“重要的史实”(见该书中文版前言),作者为了做到这一点,克服了巨大的困难。
以上是我读完张俊峰新作后的一些感想和联想,重点有些散,考虑不够透彻,有些内容可能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不过因为我和张俊峰关系很好,彼此了解也不错,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他理解我。
祝贺本书的出版,并期待张俊峰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