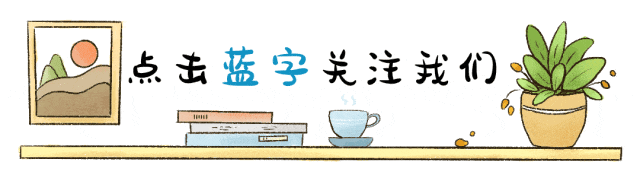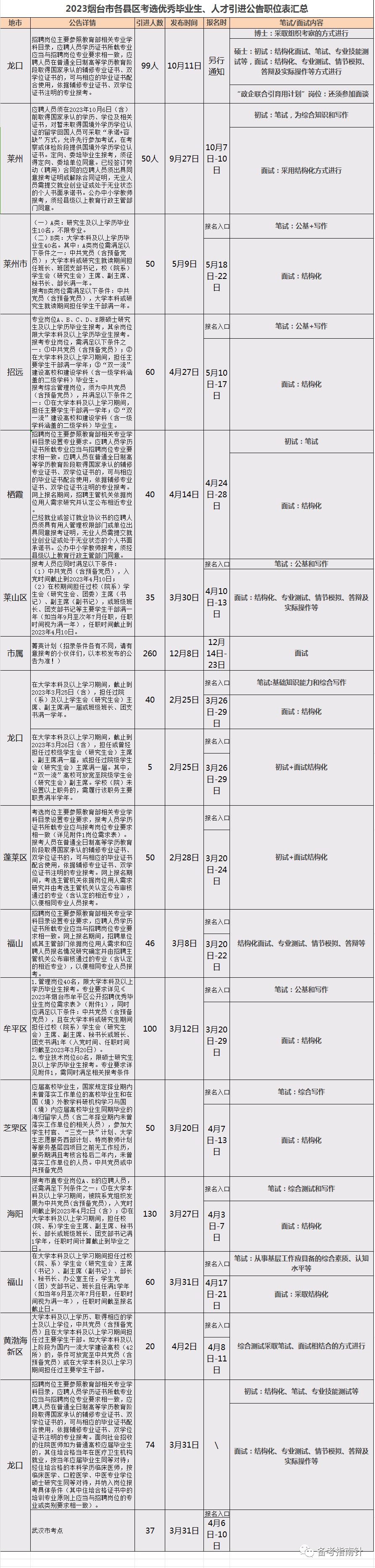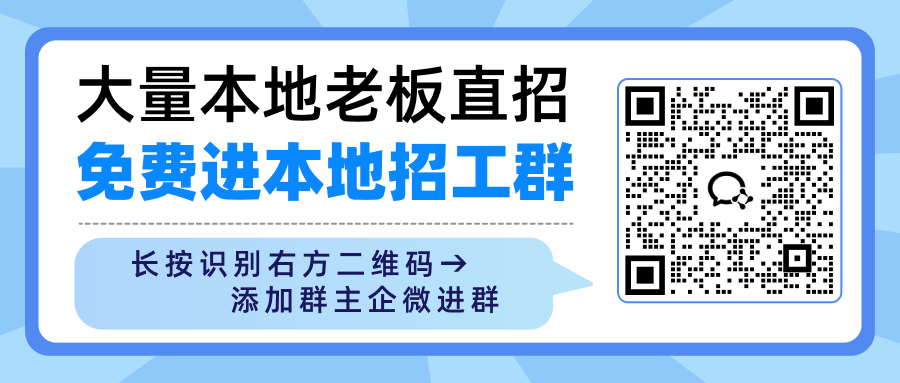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人们都习惯称幼儿园园长为“园长妈妈”,极少数情况下也称“园长爸爸”、“园长妹妹”。
2010年我成为全职校长时,孩子和家长都这样称呼我。一开始我有些挣扎:“叫我宫老师吧。”但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年轻的老师继续加入我的行列,他们称我为“守护者”。 “大妈”群体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自然。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像一个温馨的家庭,所以我只能顺其自然。

记得开学的时候,一个孩子兴奋地宣布:你知道,我们的教室就在校长妈妈的房间旁边。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多机会见到我并在我的办公室坐下来聊天。教师节那天,几个高年级的孩子拿着“小记者证”走进我的办公室接受采访。面对房间里的照片、特别的卡片和自制的礼物,孩子们不断地问:“你什么时候留短发的?” “这簪子是谁给你的?” “你在这里做什么?” ...
确实,每天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孩子们都会大声跟我打招呼,“校长妈妈好”、“好久不见”、“爱你,校长妈妈”……问候声不断传来。走着走着,我心里充满了喜悦。与孩子交谈、拥抱,增进彼此感情,拉近彼此距离。现在家长们的年龄和我当年的学生差不多,称呼他们为“校长妈妈”就显得特别亲切了。

直到有一天,一群“校长妈妈”走进了武南。其中,我介绍了我的几个朋友为“高校长”、“陈校长”等,然后随口问孩子们:“那么,我姓什么?” ?”这时,周围的高年级孩子们齐声说道:“我姓袁!”这个回答让大家都笑了。然后我又问:“真的吗?我肯定不是幼儿园的袁”。一个聪明的孩子立即回答道:“这是一个圆中的一个圆,对吗?”为了不打扰他们活动,我说:“是也不是,过几天再说吧。”同时,他对旁边的老师说道:“这个话题很有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当我转过街角时,我看到一群孩子在做运动。其中有一个孩子非常喜欢和我聊天。我有点不愿意受自己刚才的话的影响,就主动问他:我姓什么?他流畅地说:你姓袁。我说:我叫你小王,那你姓什么?他说:我姓王。我继续问:那你的姓为什么不姓“肖”?他笑着说:我姓王。不过,他的眼神却透露出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

这次看似简短的交流,让我明白了“校长妈妈”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看来孩子只是称呼他为“校长妈妈”而已。在小班里,一些不适应幼儿园集体生活的孩子会拒绝我的照顾。老师会说“这是校长的妈妈”,但孩子会哭着说“不,我想要我自己的妈妈”。他们的注意力点击“妈妈”这个词。高年级的孩子们对我已经很熟悉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校长”二字上。一位小学校长曾坦言,一年级的孩子们叫她“校长妈妈”,她很不习惯。原来,孩子们把幼儿园的名号带到了小学。
尽管它们只是标题,但这些有趣的讨论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得到回应和进展。
当我在锻炼时再次遇到小王同学,他主动说:“我明白了,你姓龚。”我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一群孩子看到我,纷纷说:“宫老师好”、“宫老师好”。甚至有人用上海话叫我:君老师(上海话“功”的谐音)。一位老师传达了孩子们对校长妈妈的印象:她喜欢笑;她喜欢穿西装;她温柔、优雅(这个词让我很惊讶);她很忙,经常去开会,去看望弟弟妹妹……孩子们似乎渐渐明白,“妈妈,校长”只是一个称呼。

一天早上,我在另一个公园巡逻。一个5岁的男孩在楼上迎接我,认真地对我说:“宫老师,你真棒。”我很惊讶,问:“你为什么说我厉害??”他看着我,笑着说:“你是校长,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说完,他就往自己的教室走去。我果断地跟着他进了教室,因为我还需要知道他的姓氏并告诉他,因为他的夸奖让我很高兴。我很惊喜,这是一天的美好开始。
关于“校长妈妈”的事情每天都会继续发生。幼儿园里有卫生老师、清洁工叔叔等,家庭也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给孩子时间和机会去了解每个称谓背后的真实人物,看到其中的关系他们和他们自己之间,让每个标题符号都更加温暖和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