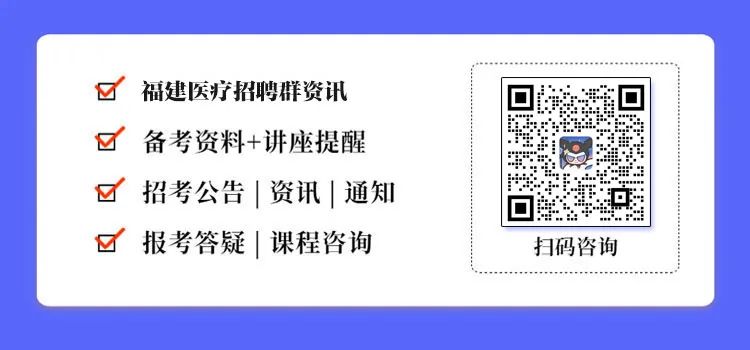制图:张英姿
印发的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体育工作的若干措施》,简称“体育八条”。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大力开展学生“班级赛”,实施“科学精准提升学生体质”等举措,共 8 条。以此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把身心健康教育融入学校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体系。
这是北京市针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又一项举措。
- 要有效控制近视率和肥胖率。但是,近些年,由于学业负担以及安全方面的顾虑等原因,很多地方的中小学都出现了“课间圈养”的问题。操场上奔跑且满头大汗的孩子变少了,楼道里也变得安静了许多。“小胖墩”“小眼镜”等这些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孩子们的社交场所甚至都转移到了厕所里。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国华在 2024 年 3 月全国两会期间,对中小学生“厕所社交”现象表示了担忧,即不能让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就此停留在厕所里。
如何破解这一问题?北京从顶层设计中给出了解法。
2024 年秋季学期开始后,北京市教委印发了《优化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学生在校课间时间指导意见》。此意见明确指出,为了优化课间安排,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按照原则要落实 15 分钟的课间时长,并且在上、下午分别安排一次 30 分钟的大课间。在学校的每一天,小学阶段的课间总时长不少于 90 分钟,初中阶段的课间总时长不少于 105 分钟。
暑期,我们开展了调研,问卷数量近 12 万份。超过 76%的孩子表明自己比较喜欢或者非常喜欢这个改变。同时,超过 61%的家长选择了有必要或者非常有必要。北京市教委副主任王攀如是说道。
课间 15 分钟的政策已经推行了一个学期。有了这 5 分钟的增加,操场会变得热闹吗?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哪些困难呢?这 5 分钟的改变能够撬动更多的教育变革吗?寒假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深入北京多所中小学进行实地探访。他们发现,这项破旧立新的变革使得一所所学校展开了创新探索,老师们在课内课外实现了角色转换,孩子们也变得“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这些变化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微改革”正在撬起“大变化”。
让孩子玩得充分学校“上天入地”破解运动空间难题
学校课间调整为 15 分钟的那天,郭珮甄在放学路上。她一路都在诉说,既意外又兴奋。一直到回家,她都还在诉说。
下课铃一响,我便会立马朝着室外跑去。自从课间多了 5 分钟后,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即“北外附校”)三年级三班的郭珮甄和她的朋友,凭借班级处在一层的便利条件,几乎每个课间都在教学楼门口的小广场跳跳绳梯。

2024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市第八中学西便门东里校区的学生在课间进行了打乒乓球的活动。任君进行了拍摄。
孩子们对课间时长从 10 分钟变成 15 分钟感到欣喜若狂。

孩子们玩的时间足够多了,这就需要给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活动项目以及更大的活动场地。而这对于北京的部分中小学而言,是一个难题。
北京的中小学有许多位于胡同之中。尤其在老城区,还有一些学校是以胡同来命名的。这些学校都面临着空间较为狭小的现实状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抵达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时候,在操场上,五六年级的学生正在进行做操这一活动。
学校拥有 42 个班级。我们将这些班级分成了两批来做课间操。现在正在做课间操的是五年级的 14 个班以及六年级的 7 个班。上一个大课间做课间操的是四年级的 14 个班和六年级的 7 个班。府学胡同小学德育主任李响如是说道。
朝阳区实验小学紧邻繁华商业街,也面临着体育运动空间不足的难题。这所学校努力挖掘空间潜力,“上天入地”,将学校的空地、空房、过道、楼顶以及地下空间等都转变为师生的运动场地,陆续建成了楼顶足球场、楼间连廊、楼内运动空间和体操房等活动空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获悉,2024 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朝阳区实验小学对空间进行了整合。校园南楼的二、三层设施得到了优化更新。新建了乒乓球运动空间、啦啦操运动空间、少年篮球运动场以及轮滑教室等。新增的运动场面积近 1000 平方米。对校园运动空间进行挖潜后,之前共增设了 3000 平方米的运动场地,这相当于 7 个标准篮球场的面积,从而极大地满足了学生的运动需求。
北外附校是一所包含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 12 年制学校。它的面积较大,但却存在人均使用面积不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对中学生课间和小学生课间进行了错峰安排。北外附校校长张文超表示,为让 12 个年级 100 多个班级的学生课间能有地方玩且有得玩,学校在教学楼下开辟了五六个区域,并将乒乓球、羽毛球场地搬入其中。这样,学生在课间就能非常便捷地走出来活动,因为场地触手可及。
城区的学校与郊区学校相比,在空间方面郊区学校具有很大优势。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小学进行观察,发现该校地处山坳,地域十分辽阔。
九渡河利用乡村学校的特点与资源,让孩子融入室外环境。秉持着“能户外就不室内”的原则,使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户外运动项目。让孩子尽情闹起来,走出了与城市学校不同的课间活动实施方式。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小学校长于海龙如此说道。
学校为学生准备了多种器材,有自行车,还有攀岩设施与护具等。学生在大小课间的时候,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课间攀岩这种活动,也可以选择单车骑行这种活动,以及其他多种户外活动。
乡村中有着独特的动物,这些动物成为学生课间 15 分钟活动的资源;乡村中还有着独特的植物,这些植物也成为学生课间 15 分钟活动的资源。
课程学习到“寒露”节气时,会让学生去风采园欣赏菊花并进行采摘。在苹果丰收的季节,劳动老师会带领孩子们把苹果清洗、切割,为全校师生制作止咳茶饮。该校三年级班主任陈则安表示。
北京市各个中小学为了让孩子们拥有更良好的课间活动体验感,都根据本地情况和本校实际使出了各种办法。场地充足的学校在户外活动选择方面提供的内容丰富多样,场地局限性较大的学校则发挥自身特色,在细节处下功夫。近 700 年历史的府学胡同小学,其特点是庙学合一。学校完整地保留了校园内庙、堂、阁、祠四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建筑。学校借此打造了“活”的教育博物馆,使得孩子们在课间能够走进不同的博物馆,从而了解文化并丰富知识面。并且有学生在课间担任起了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为同学进行讲解。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等多所学校在课间楼道开辟了植物角和演讲角等活动角,这样学生们就能就近开展活动了。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等多所学校于课间楼道开辟了活动角,其中有植物角和演讲角等,以便学生们能在近处开展活动。 北京市密云区第四小学等多所学校在课间楼道开辟的活动角包括植物角和演讲角等,目的是让学生们可以就近进行活动。
然而,保障安全是让学生“玩充分”的潜在前提。据悉,北京市的多所中小学采取了召开紧急救治教育班会以及定期安排安全督导员等措施,以此来确保孩子们课间的安全。记者在北外附校看到,每当大课间来临,该校的校医就会在操场旁边静静地守候着,以保证在出现意外情况时学生能够及时获得救治。张文超表示:“校医每天都在,从未缺席。”
让孩子玩出健康破解“小眼镜”“小胖墩”等问题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越来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去年年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关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的提问时表示,当前中小学生存在“小眼镜”问题较为突出,存在“小胖墩”问题较为突出,存在脊柱侧弯问题较为突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等情况,需要学校、家庭、社会朝着相同的方向前行,共同发力,为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成长营造有利的条件。

2024 年 11 月 4 日,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的学生正在课间进行跳绳活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羽璋拍摄了这一场景。
课间时长“扩容”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走出教室的时候,一些改变出现了。
北外附校小学二年级的谢天皓在别人眼中是个“小胖墩”。
谢天皓起初在大课间的阳光乐跑中总是掉队,原因是他体重偏高且体能偏差。班主任邓招菊说:“那时候,他每天问我最多的一句话便是‘老师,今天是室内操还是室外操’。”
邓老师陪着谢天皓一起跑。起初,他落后同学 3 圈;之后,变成落后两圈;而现在,几乎能并肩前行了。
国外一项研究表明,即便在课间开展轻微的活动,也对降低儿童肥胖的风险有帮助。
室外活动在减轻青少年近视的产生方面有着关键的作用。
现在三年级的吴若溪,一年级就戴上了眼镜,度数为 150 度。二年级时度数增加到 230 度。进入三年级后,课间时长有了调整,她每天有更多时间在户外玩耍,还参加学校每天组织的课间活动以及大课间的阳光乐跑。这些使她的眼睛得到了有效放松,去年年底复查时,眼镜度数未再增加。
与其他明显的变化相比,孩子们心理上的那些细微变化不太容易被察觉到。然而,在冲破障碍、跨越阻碍的那一瞬间,常常会展现出像破茧成蝶般的蜕变。
怀柔区九渡河小学一年级班主任王学荣讲述道,班里有一个孤独症孩子是随班就读的。这个孩子不习惯与别人进行交流,并且在做游戏的时候,常常只是胆怯地在一旁观望。
在一次迎面接力中,王学荣主动成为他的队友,和他一起参与。其他孩子看到他们两个人一起跑时,都在赛场边上高兴地又跳又喊。在一次次的游戏里,他慢慢打开了自己,从原本等着“被选择”转变为主动参与。他一来就会说:“豌豆妈妈(王学荣的班也称为豌豆班——记者注),今天我们玩什么?”
王学荣对他的变化感到欣慰。现在,这个孩子不仅会和王学荣一起,还会加入到别人的游戏中。即便不与别人玩耍,他自己也会主动去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花园小学的楼道里摆放着一架钢琴,课间时常有学生经过时随意弹奏几下。五年级二班的班主任是张蓓,她班里有个说话不太流利的小男孩,他缺乏与他人交流的信心。然而这一学期,他常常在课间弹奏钢琴,那指尖跳跃的旋律引得老师和同学们频频称赞。渐渐地,他在与琴键“对话”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音乐成为他表达自我、克服自卑的新语言。
从心理健康方面来讲,学生能够集中 40 分钟的注意力,尤其在小学阶段,做到不说话且认真听讲,所付出的体力以及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小学一到三年级学生的近视率环比增长的幅度是最大的。
王攀表示,我们的工作是有侧重的。并且强调,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要更加重视,要把课间时间留足,还要提升课间活动的质量。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体育教研室为了解北京市各中小学课间 15 分钟学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采用了网络问卷的形式。对全市的中小学体育老师进行了调研。这些老师有几千名。
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以上的学校制订了具体的活动计划,同时提供了特定的活动区域和设施,学生能够自主且有弹性地选择活动内容,并且有专人负责安全以及组织等相关事项;三成的学校借助人工智能来助力学生的课间活动;接近九成的学校都设置了预备铃;七成以上的教师参与了学生的课间活动。学生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室外。他们最喜欢的内容依次为:“室外运动类”;“自由玩耍”;“益智类”;“室内运动类”;“看课外书或绘画”;“同伴交往聊天”;“预习或复习”。其中,体育类活动是学生课间的首选。
让孩子爱上运动“我的课间我做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入北外附校的那一天,碰到了几名学生。这些学生正和美术老师一起,在教学楼外的玻璃上进行“玻璃彩绘”创作。
在府学胡同小学的课间,一间活动室内,有两个“竹节人”,一个名为“李二棍”,另一个名为“无敌大将军”,它们正在课桌上进行一场激烈的大比拼。匡泳介是该校六年级学生,他说:“这是我课间最喜欢玩的游戏。”并且这个课间玩具的设计想法,是源自语文课上的一篇课文《竹节人》。
竹节人是北京的传统游戏。在老师的启发下,孩子们开始行动。在老师的带动下,孩子们开始自己制作这种竹节小人。李响这样说道。
让孩子们动起来。这不仅是为了防止肥胖和预防近视。更是为了让孩子们逐渐喜爱在操场上尽情奔跑的感觉,喜爱挥洒汗水的感觉。进而热爱运动,养成运动的习惯。让校内每个课间增加的 5 分钟,能够变成校外自觉自愿增加的 50 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一场名为“我的课间我做主”的创意课间设计在北京的各个中小学展开,其目的是让学生真正爱上课间的活动,目前已经征集到了几千个创意设计。
北外附校在学期初刚开学之时给家长发送了一封信。该校期望家长能够与孩子一同设计课间活动,以此来调动孩子在课间活动中的积极性。张文超校长表明:“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想象力,并且能够解决动力源方面的问题,促使学生愿意进行玩耍。”
不少接受采访的老师表示,会引领学生设计具有独特性的课间游戏。当下,北外附校二年级八班的邓招菊老师正在带领孩子们设计超级大富翁的游戏。孩子们把快递纸箱板当作材料,接着在上面设计一些图案,或是一些语数英的简易题型。他们就是希望让孩子们在活动中能够获得一个学习的契机,做到在学习中玩耍,在玩耍中学习。
当然,更多的课间游戏来自孩子们的突发奇想或奇思妙想。

2024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市第八中学西便门东里校区的师生在课间进行踢足球的活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羽璋进行了拍摄。
在九渡河小学,四年级的张恩赐有设计“大家没见过的”的想法,他发明了需要发挥团体意识的集体性活动。五年级一班的李佳静和同学开发了“山楂树下”的演唱平台。府学胡同小学的同学为了课间能放松眼睛,发明了游戏“闭眼画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调查和采访过程中发现,为了进一步填补那 5 分钟的“空白”,北京市的多所中小学增添了诸多体育类、艺术类、益智类等不同类型的游戏,并且还增设了相关的场所,从而让原本单调乏味的课间生活实现了“华丽的转变”。
教师“转身”5分钟“扩容”带来的是教学结构的调整与变革
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
有人说,课间时长能否真正扩容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教师。近些年,“课间圈养”问题越发突出,这与部分教师不科学的教学观有联系。在一些教师心中,课堂比课间更重要,学知识比玩更重要,数学语文比体育更重要。所以,有些教师会随意拖堂,还有些地方出现大课间被学科教师占用去讲课的情况。
王攀称,课间 15 分钟政策实施有两重困难。其一为客观方面的“卡点”和“堵点”,像空间不足、人员众多等情况。其二是内在的“卡点”和“堵点”,“主要在于我们教育工作者对课间的认识有待进一步全面深化,需像尊重课堂那样尊重课间”。
北京市教委基教一处处长周凯在去年 11 月的一次市级专题培训中表明,应当开展培训活动。
北京市开展了各种类型的培训,从市级开始,到区级,再到校级,目的是让教师从观念上真正重视课间的育人功能。北京教育学院开发出了几十个课间微运动,这些课间微运动既容易教又容易学。只要学生想动想玩,就可以利用学校走廊、操场空地随时动起来。
对教师来说,转变是从身份的调整开始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抵达府学胡同小学时,恰好赶上课间。在那面积不大的操场上,一群学生正在和男老师王云龙一同打篮球。

2024 年 12 月 12 日,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学生在课间进行篮球活动。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聂思媛进行了拍摄。
王云龙是一名语文老师,同时还是班主任。看不出来吧,自从改革之后,他每天都会来打篮球,身边总是有学生围着他,一个学期了,几乎每个课间都没落下。李响说道。
王云龙告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改革之前,他的课间主要用于休息。他会利用课间改作业,还会“转场”。并且他当时还主动担任着“厕所所长”的工作,他认为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和小姑娘就应该多出来玩会儿,要把逗留在厕所的孩子们叫出来。
课间时长改变后,他决定不再跟在学生后面。接着,他开始吆喝学生,让他们一起走出教室去打篮球。他还主动加入女生的队伍,与男生展开对阵。如今,每个课间他的身边都围着一群正在打球的孩子,这些孩子中既有他自己班的学生,也有其他班的学生参与其中。
从在孩子身后“管”着他们,到走到孩子身前“带”着他们,一个“转身”对于教师而言是身份的转变。教师从原来课间的“管理者”,变成了课间的“参与者”和“设计者”。而对于孩子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寻找到了身边的榜样。
王学荣说,她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也必须做到。她班上的孩子刚从幼儿园升上来,她不仅要带孩子们玩一些幼儿园玩过的传统游戏,做好幼小衔接,还要鼓励孩子们学会更多更有挑战性的运动。她要求孩子跳多少,自己就跳多少,她一个月跳绳量能达到 5 万个。
那么,课间的释放会不会影响上课?

起初,王云龙会担忧长时间玩耍会致使孩子们上课难以集中注意力。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察觉到孩子们在语文课堂上思考和发言变得更为主动了,其表达欲有了显著的提升。
在学生一张一弛的变化中,教师不仅转变了身份,也转变了观念。
教师们为了能更好地发挥课间的育人作用,开始在课堂上发力,思考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并在这方面做文章。同时,教师也有意识地进行课堂与课间的联通。在课堂结构方面,借助课堂尾部的 3 至 5 分钟来开展学生研讨和师生互动,创造出柔性空间,以确保能够准时下课。
现在的情况表明,拖堂问题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王攀称,自 2024 年 10 月起,北京市的责任督学在每所学校会随机巡查至少 5 个班级,并且累计访谈了涵盖小、初、高各年级的超过 2.5 万名学生。绝大多数学生反馈,老师尊重学生课间的自主权,不存在拖堂、提前上课以及限制学生出教室的情况。仅有 34 名学生(0.13%)称出现过老师从预备铃响就开始上课的状况。只有 2 名学生表示有老师在课间讲题且限制学生出教室的情况。
“小切口”背后的持续性变革
课间时长扩容至 5 分钟,改变的不只是学校课内课间结构的变化,还让孩子能够奔跑出汗。王攀说:“核心在于把学生当作完整的人、鲜活的生命来对待,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而非仅仅关注学科知识教了多少以及掌握了多少。”
寒假前,中青报·中青网的记者抵达了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此时,孩子们正在上一堂别具特色的科学课。
几分钟后,随着老师“三、二、一!”的指令,又一个塑料袋升了起来。
这一节课的内容源自科学课本上的“空气”。课间时长增加后,这节课不再仅仅是老师进行原理讲解和实验展示,而是被调整为“我和空气做游戏”,这样能帮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理解热气球起飞的原理。该校科学教师张懿介绍,在“我和空气做游戏”这方面,无论是内容的设置,还是文本的引导,都在努力展现课堂教学与课间游戏的关联。孩子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或者做过的实验,能够在课间继续进行尝试。同时,孩子们在课间游戏时碰到的科学问题,也可以成为课堂上的讲授内容。
至此,知识变得鲜活起来了。新课标所提出的目标都具象化了,这些目标包括“跨学科”“综合性”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等。
张文超认为:我们要持续摒弃唯分数论、唯知识论这类理念。学生的学习,一方面是在课堂上学,另一方面能延伸到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体验中学。这样能让学生把课堂教学与课间活动以及其他校外活动相串联,从而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课堂内容延续至课间,课间开始对课内产生影响,既有延伸的部分,又有反哺的情况,这便是课间课内一体化,同时也是未来“课间一刻钟”改革探索的新方向。
其四,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新场景中发挥作用,为学生创设更为丰富的课间活动环境。
课间时长为 5 分钟发生了变化,这成为一个小的切入点。通过这个切入点,教育改革能够从离孩子最近的地方开始推进。并且,教育改革能够聚焦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全面发展。这样一来,就为破解人才培育的难题提供了具体的路径和可能。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樊星记者樊未晨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5年02月24日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