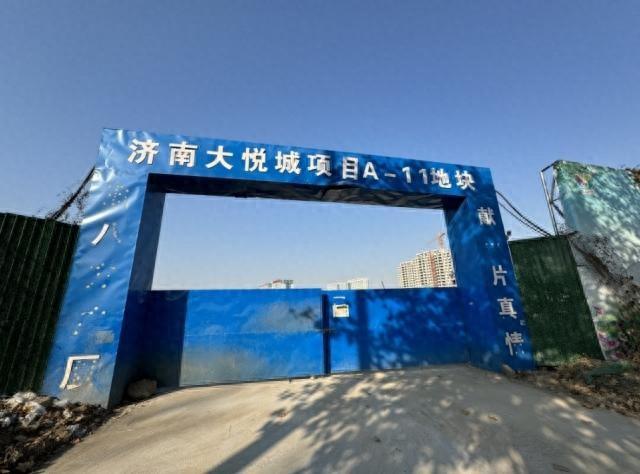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分别是“赋”“比”“兴”。“赋”这种表现手段是直接陈述事情,直接抒发情感,有什么就说什么。它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方法。然而,诗歌不能如同日常语言那样仅仅满足于说清楚,还需要注重说得有韵味,要给读者留下涵咏玩味的空间。正因如此,诗歌往往不直接表达,而是采用“比兴”的方式。明朝文学家李东阳称:所谓比与兴,都是通过寄托事物来表达情感的。因为正言直述的话,容易把意思说尽,却难以引发情感;只有有所寄托,进行形容描摹,反复吟咏,等待人们自己去领会。话语有尽头而意韵却无穷,这样就会精神爽朗、意气飞扬,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比”“兴”和“正言直述”的“赋”相比,更具有表达的能力。

具体而言,“比”和“兴”属于两种手段。其中,“比”包含单个的比喻以及成套的比喻(博喻),还涵盖涉及全篇的所谓“比体”。例如《诗经·魏风·硕鼠》,此诗全篇都在对老鼠进行斥责,实际上是在强烈地痛斥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像这样全篇都在运用“比”的手法的诗就是“比体”。

“兴”是所谓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诗集传》卷一)。这个“他物”与“所咏之词”也就是本意之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关系。有些“他物”仅仅是起到一个押韵的作用。有些“他物”能够起到烘托气氛、引起联想的作用。兴词与本意之间还有近于比喻关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比”和“兴”往往难以区分。
宋朝人李仲蒙称:“用索求之物来寄托情感的叫做‘比’,这是情感依附于物;通过接触外物而引发情感的叫做‘兴’,这是物触动情感。”(见于胡寅《斐然集》卷十《致李叔易》)如此从思维过程的角度来阐述“比”和“兴”的差异,是很能抓住要点的。“索物以托情”意味着先有本意,接着去寻找一个或一组物象进行比喻、寄托,此为从内心到外物,所指较为单一,也可以说是主题先行的情况。由物及心即为“触物以起情”,诗人从物象中有所感悟,所抒发的感情通常比较复杂含蓄,还能引发更丰富的联想。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创作了一首五绝《乐游原》,其中写道:“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出游而见到夕阳,从而引发了他叹老伤时、爱惜光景的情感,这种情感苍茫辽阔且无限感伤,最终成就了千古名篇。

“比”是从心到物,从一般迈向具体;“兴”则与之相反,是从物到心,从具体走向一般。它们的根基都是联想,不过路径存在差异,也可以说是恰好相反。歌德曾明确把艺术思维中的联想划分成两类:“诗人或者从普遍概念起始,接着去寻找合适的细节;或者从细节中察觉到他的普遍概念。这二者有着极大的差别。”前一个方法造就了寓言,寓言中的细节仅能充当示例,仅能充当普遍概念的典范。相比之下,是后一个方法体现了诗的本质。此方法在描绘细节时,并非单独地去思索或提及典型,然而它把握住了细节的生动性,在无形中也将典型一并抓住了。《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提到,歌德所说的这两种方法,大致上正好和中国古人常常说的“比”以及“兴”是相当的。
“比”是“索物以托情”,即找些可作比喻的例子来表达主观的东西,因此它往往是封闭的,主题明朗且单一;“兴”是开放的,内涵丰富,具有多义性,往往更耐读。所以歌德说,艺术的难关在于“对个别事物的掌握。需费大力挣扎,让自己从观念中解脱出来”(《歌德谈话录》)。中国古典文论向来认为“兴”比“比”更高级,“比”较为明显而“兴”较为隐晦(如《文心雕龙·比兴》中所述);“有了兴,诗的神理就全部具备了”(像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说》中所说);“必定有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道理,无法讲述的事情,在默默领会的意象之外遇到它们,而道理和事情在眼前都鲜明地呈现出来”(如同叶燮在《原诗》中所讲)。表述虽各不相同,但其中的深意与歌德的看法可谓是彼此心领神会,心意相通。

清朝诗论家沈德潜曾言:事情难以直白陈述,道理难以详尽言说,常常借助事物进行类比来体现。郁积的情感想要抒发,自然的机趣随之融合,常常凭借事物引发情怀来抒发。比兴相互陈述,反复吟唱叹息,而其中蕴含的欢乐悲戚之情,隐约跃动想要传达,其言辞浅显,但其情感深厚。倘若只是质朴直接地铺陈,完全没有含蓄蕴藉,用没有情感的话语却想要打动他人的情感,是困难的。从表现力方面来看,比兴的表现力比赋要高,兴的表现力又比比要高。这是因为“借物引怀”这种方式所包含的内容更加丰富生动,而“托物连类”这种方式所指向的较为分明,弹性较小,难以达到杜甫所说的“篇终接混茫”的最佳效果。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表明,“写物以附意”这种情况被称作“比”,同时“起情,故兴体以立”。这一说法为后来李仲蒙的著名界定提前开启了先河。刘勰还指出,汉代辞赋十分兴盛,然而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的现象,正因如此,汉赋的艺术感染力比不上诗,这就是根本原因所在。刘勰的这些意见,其方向与歌德重视从生活本身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的诗学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中国古代的理论家在见道方面总是会更早一些。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3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