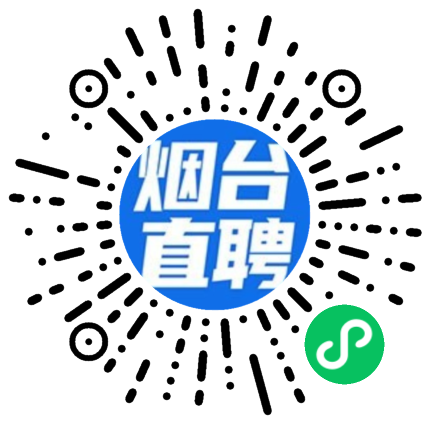随着《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等电视剧的热播,东北正成为大量观众关注的焦点,此前,双雪涛、班宇、郑直、杨志涵等东北作家已掀起一股写作风潮,让这片土地在读者心目中被视为“文学温床”。近年来,东北作家的作品多次被改编,包括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刺杀小说家》,班宇的《逍遥游》,郑直的《胜屯》……

刚刚过去的暑期档电影院,郑直的短篇小说《仙综合征》被改编成电影,电影由顾长卫执导,葛优、王俊凯主演,片名改为《刺猬》,《刺猬》就是原著小说和电影里的故事开篇——在一条交通拥堵的街道上,舅舅王占团正在指挥一只刺猬过马路,而这一幕恰好被一个叫周正的“我”看到了。

从他指挥刺猬过马路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占团是一个有些特殊的人物。王占团出生于1947年,19岁参军,因为一场运动,他变得不正常,先是离开了部队,然后早早地从工厂退休,不用上班,也没人理他。小说中对他生活状态的描述是,“大部分时间,他每天在家里闲逛,用姑姑上班前给他的零花钱买两瓶啤酒,最多够买一包鱼皮豆腐。中午就会回家把剩饭热一下,等姑姑下班吃饭。”
王占团的“不正常”很有限,只是什么都不做,偶尔举止怪异,但这足以让他成为别人眼中的异类,他被周正妈妈视为疯子,必须时刻和周正保持距离,他是周正奶奶说的负担,是周正姑姑家的负担,应该送进精神病院。在姑姑看来,王占团一定不能送进医院,承认他有病,就等于承认这个家有污点。为了解决问题,因为王占团不正常,大姑姑请了算命先生,给他喂安眠药,最后无奈之下,只能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故事展现了一个稍微偏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人,是如何被周围人以各种方式批评、拉回来的,因为不被当做是一个健康的人,失去了基本的权利和尊严。故事中,似乎唯一能和王占团相处的周正,也是别人眼中的不正常者,因为从小口吃,周正被同学歧视,被父母拉着去尝试各种方法,“在一家小小的诊所里,舌根被电钳烫伤,喝了用蝼蛄皮熬成的开水熬成的偏方,嘴里含着碎石读拼音表,吐了好几碗黑血,我的口吃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让周正成绩下降,还被留级了好几次。”
在原著中,郑直并没有刻意强化王占团和周正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刻意营造出一对边缘人靠拥抱取暖对抗外界的励志情怀。在周正视角的这段叙事中,他对王占团有了更深更深刻的理解。复杂的感情,有如同其他亲人般的疏离感,也有基于共同“异常”的吸引。“我仿佛被一种熟悉的力量驱使着……独自去找王占团。”对父母所作所为的憎恨,或许也是周正与王占团站在一起的原因。这种对父母的憎恨,进而转化为对自己的憎恨。“我恨这个家,恨父母,也恨我自己。”周正矛盾的内心世界,在他对王占团的种种难以排解的情绪中展露无遗。他想要接受自己,却又时常陷入自我厌恶。

小说中,王占团用“卡住”二字形容自己的人生状态,“我卡在了关口,一切都是灰色的。”但相比于王占团应对他人操纵时的冷静,甚至有时装糊涂,周正似乎才是真正“卡住”的人。他更加愤怒,更加敏感,当挣脱的欲望更加强烈时,在“卡住”的位置上会更加痛苦。他不想被像王占团那样对待,但他又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这也是小说与电影最显著的一个区别。电影中,经常一起玩耍的周正和王占团成为互相扶持、对抗外界的联盟。当男孩面对另一个与自己长相相似的人时,内心深处的阴影便展露出来。被磨平后的他似乎没那么“卡”,也得到了电影中逆袭般的亮眼结局,成为了环游世界的水手。他不仅成为了一个正常人,也算是正常人中的“正常人”,一群“爬上顶峰”的人。
影片最后,刚从海上归来的海军士兵周正与母亲进行了一段对话,周正对母亲说:“我是王占团。”母亲问周正:“你能原谅我们吗?”周正说:“我不原谅。”成年后的周正接受了自己,也终于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态度。面对曾经受到伤害的周正,母亲那句求饶的话更是耐人寻味。无论是话语中透露出的悔恨还是屈服,都似乎建立在周正已经成为一个正常人的事实之上。如果眼前的周正还是她眼中那个结巴、留级、无所作为的王占团,她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个看似以周正的成功而完美收官的故事,并没有向所有像周正、王占团这样有缺陷的人许诺一个包容、尊重的“美好未来”,而是指明了这个群体必须走的路:成为这个正常社会绝大多数正常人要求你成为的人——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更优秀的人。
在原著小说中,郑直用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当王占团的女儿王海鸥爱上药店的同事李光远时,这个在众人眼中比王海鸥大八岁、离过婚、没有孩子、在舞厅混日子的男人,并不受欢迎,以至于大姑一度想杀了李光远。然而,这个“花花公子”在婚后生活中,渐渐显露出自己好的一面,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光远,我明白了,你不是坏人。”李光远在别人眼中形象的改变,戳破了人们对这些“不正常的人”的各种偏见,无法决定人们该如何对待?正是因为李光远的存在,王占团的悲剧才更加凸显。作为一个被偏见束缚的人,王占团至死也没有摆脱疯子、负担、污点的骂名,在精神病院去世。“早上护士给他端粥的时候,他就转过身,头靠在窗台上,像是在打瞌睡。”

王占团、李光远、周政等边缘人物在郑治等东北作家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在首部小说《生吞活剥》中,郑治塑造了失去双亲、性格孤僻但智商超高的少年秦立。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饱受歧视和暴力,甚至在友情上也遭遇不公平对待。秦立最终成了和卡西莫多一样的聋哑人。唯一能与秦立感同身受的同伴黄姝与他有着同样的感受,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却在快成年时因意外受伤而选择自杀。最纯真的心灵似乎总是在作者笔下遭遇最残酷的折磨。在坠落天台之前,对黄姝的复仇已经完成。聋哑男子怒吼道,“那声吼叫,或者说哀嚎,本该尖锐到刺破夜空,但却弱小得如同垂死的生命,没有丝毫回音,一瞬间就被黑暗活活吞噬。”
郑志的《生吃》以两个年轻人对命运的无奈愤慨收尾,其实故事结尾处消失在夜色中的回音,传达的正是一代人的失落。短篇小说《蒙特卡罗食人族》中,郑志写到一位下岗的父亲,整天在集市上四处游荡找零工,“头戴土匪帽,拉下来遮住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短篇小说《林中林》中,机场驱鸟工吕新凯和盲妻连洁几乎可以视为秦力和黄姝的化身。《先正的病》中,周正的父母双双下岗后,开了一家面馆,这个细节改编自郑志父亲的亲身经历。
在以《闲情症候群》夺得匿名文学大赛一等奖后,以黑马身份出现在文坛的郑直,曾在演讲中提到过这个群体。在沈阳一家名为“穷鬼乐园”的啤酒屋里,很多东北人会整天坐着,醉到不省人事,“他们当然是最失意、最悲惨的人,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生计和家庭,甚至被亲人和子女鄙视,或者干脆孤独了半生,最绝望的人”。或许,对于郑直和东北作家来说,文学的意义不仅仅是用虚构的方式记录下这些消失的人和事,更呼吁我们对身边的世界保持敏感和共情。它警示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