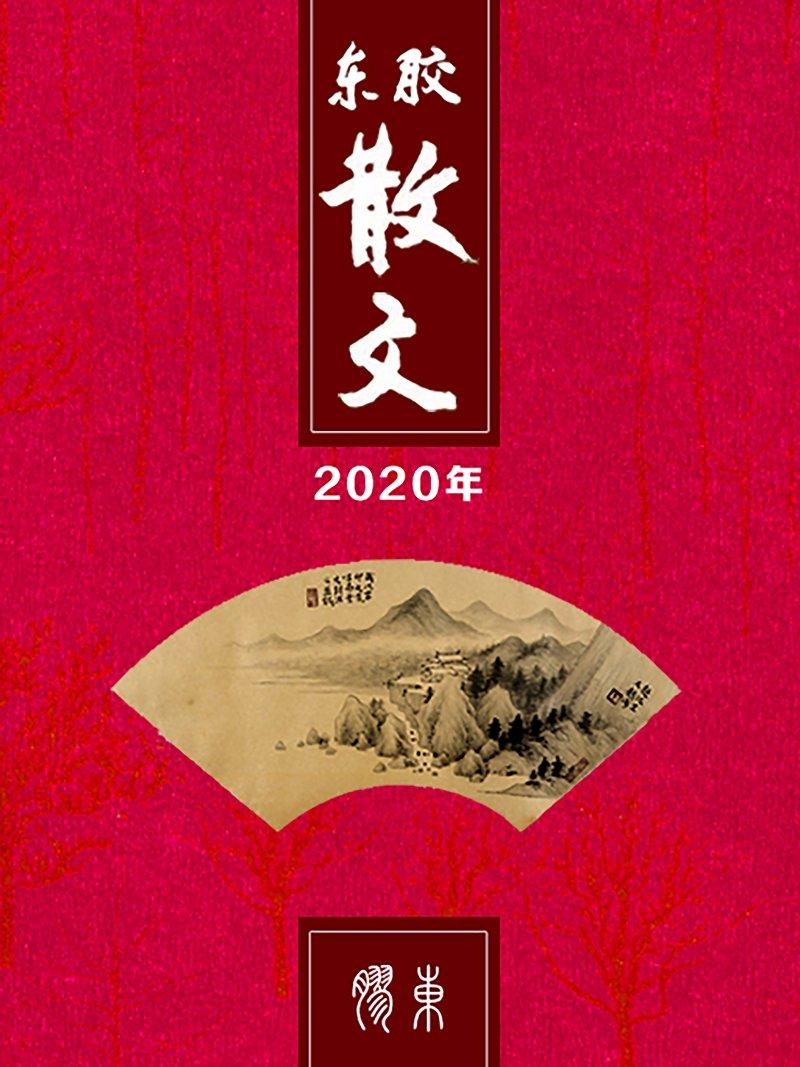清晨起床练习书法,完成后,一叠厚重的宣纸被整齐地放进了书架。不经意间,目光扫过,发现一个深褐色的檀木盒子静静地躺在旧纸堆里,上面覆盖着灰尘。轻轻拂去灰尘,打开盒子,只见半只青玉镯子躺在盒底,那是去年摘花时不慎摔落断裂的,断裂处棱角分明,幽幽的光泽如同解冻的冰河,仿佛有鲛人泪水凝结其中。当时捡起两片残缺的月亮,心中犹豫不决,不知是应该埋葬花朵还是埋葬玉石。
回首往昔,镯子宛如圆满的月亮环绕在腕上;而如今,寒霜渗透骨髓,暗自伤怀。取出一块断裂的玉石,置于西窗之下,日夜相对,日思夜梦,被困在这两片冷月之中无法自拔。《周礼》中记载:“用玉石制作六种器物,用以祭祀天地四方,用苍色的玉璧祭祀天,用黄色的玉琮祭祀地……用黑色的玉璜祭祀北方。”然而,谁又能知晓天地四方原本并无固定的模式呢?就在那一天,手持断裂的镯子仔细观察其光泽,观察断裂之处,似乎有所领悟。

复持断镯,寻巧匠,欲化镯为璜,皆笑异想天开,婉拒之。
再次审视《周礼》,我深感惊奇:璜,乃祭祀天地之神器,其形如半璧,便能沟通天地,若是运用残缺之美,即使是断裂的镯子,也能雕刻成穹庐之形!

置残镯于窗前案几,胸有成竹,对月摹画,线稿一气呵成。
那晚,蔷薇花瓣半开,幽香在空气中飘荡,残月孤悬在西窗之上。案几角落,鎏金的香炉轻吐檀香,手持银刀在画稿上刻画。麂皮包裹着残破的镯子,银刀划过的声音清脆悦耳,不久,锋利的刀刃便如同流星般断裂。刀锋变得滞涩,连续三昼夜,食不知味、睡不安稳,思索着如何破解困境。那天傍晚,细雨随着风飘洒,在窗棂间舞动,水渍如同远山轮廓的倒影,颇有良渚玉工“随形就势”的技艺。顿悟之际,我小心翼翼地滴下一滴水,那水滴在锋利的刀刃上,溅起细小的青灰色镯屑,它们遇到水后,便化作了遥远山峦的雾气。璜形的轮廓逐渐显现,我屏住呼吸,生怕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
春雨绵绵洒落室外,室内则玉屑纷飞。在禅意的旋律中,雕刻者挥刀如弹琴,刀法深浅轻重,皆依循玉石的纹理。不久,破碎的镯子便渐渐变成了精美的玉璜,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喜悦。磨砺玉璜的过程,更是考验雕刻者心性的时刻,需不急不躁,如同行走于薄冰之上,面对强敌般谨慎。待到薄片透出光芒,流转着彩虹般的光泽,玉璜才初见雏形。

最是薄如蝉翼的玉片断裂之处,如何才能巧妙地雕琢?辗转反侧,我在庭院中徘徊,随意翻阅书籍,忽然想起了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那里出土的素面玉璜,其光素之美远胜于繁复的纹饰,这才领悟到极致的技艺,原来是顺应自然、巧妙利用自然之力。于是,我依照青玉的本色,雕刻出了卷草纹样。第二天,观察断裂处,仿佛藤蔓在蔓延,我的信心顿时大增。我拿起玉璜,放在案几上,运用浅浮雕的技艺,在轮廓上阴线雕刻出龙纹,细致入微,纹饰凸起,渐渐呈现出苍龙腾云驾雾的景象。
由是玉璜大成。
玉璜上孔洞,摒弃了世俗常用的金银扣饰工艺,受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诗句的启发,特意挑选了五彩丝线,将其交织于金色蕾丝之中,点缀以几颗玉珠,精心编织成一条绳索,佩戴于颈间。

次日茶聚,佩璜者翩然而至,众人不禁赞叹:“此玉璜之精美,实乃超越完璧!”听闻此言,全场皆为之震惊。
日落时分,我踏着归途,手指轻轻滑过璜的表面,一股凉意仿佛从古至今传递而来。往昔的祭祀仪式中,那些贵族刻意摔碎玉璧的身影,一幅幅浮现眼前。或许,我们的祖先早已领悟,真正的完整,往往需要先经历彻底的破碎。在暮色笼罩下,我久久地玩弄着璜,突然,一声清脆的玉镯落地声响起,那分明是岁月如裂帛的声音。